而今再读叶师长西席诗词,感触颇深。市价寒冬,更兼疫时,武汉公民、湖北公民、全国公民都同心协力,共抗疫情。只管很困难,只管有许多同胞因疫情严重而永久长眠,只管此恨无重数,但我们相信,任何困难都降服不了中华民族,任何风雪都粉饰不了东风。我们热烈地期盼春天,期盼东风吹散阴霾,期盼中国降服疫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诗,不仅仅是诗歌,更是民族的魂魄与脊梁。
“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这是困难时候,幸好,我们还有诗词征集活动中,来自广西的丁震寰师长西席推举的诗词。他在推举语中写下了顾随、叶嘉莹师徒的一段往事。全词如下:
用羡季师句,试勉学其作风,苦未能似。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梦回何事萦怀抱。撇开烦恼即欢娱,众人偏道欢娱少。 软语打发,阶前细草。落梅花信今年早。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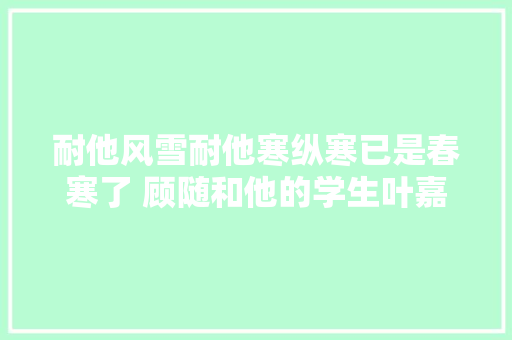
叶嘉莹师长西席是公认的顾随师长西席的传秘诀生。叶嘉莹师长西席说:“我最该感激的有两位长辈,一位是在我幼年时教我诵读唐诗的我的伯父狷卿公,另一位便是在我进入大学后,担当我们诗词曲诸科之讲授的我的老师顾羡季师长西席。伯父的引领,培养了我对诗词之读诵与写作的能力和兴趣;羡季师长西席的讲授则开拓和提高了我对诗词之评赏与剖析的眼力和境界。”
妙音迦陵
叶嘉莹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诲和熏陶。她的父母认为人在“童幼年时影象力好,该当多读些有久远代价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摧残浪费蹂躏韶光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因此请她的姨母做家庭西席教她读《论语》。其余,她的伯父有很好的诗词教化,耳濡目染,使她在学诗的兴趣和领悟方面得到很大的启示。
1942年秋,在顾随师长西席的“唐宋诗”课上,她的天赋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并且得到老师的讴歌:
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护持。勉之,勉之。
这是顾随师长西席对叶嘉莹大学之前几首习作的评语。而自“上过师长西席之课往后”,叶嘉莹自喻“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在叶嘉莹看来,顾随师长西席“对付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想熏染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师长西席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教化,以是师长西席之讲课每每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想熏染与启迪”。而她“既因聆听师长西席的讲授而对诗词的评赏有了较深的体认,更因师长西席不断的启示和鼓励,在创作方面也有了逐渐的进步和提高”。乃至于习作的风格,也受到顾随师长西席的影响。
1943年夏,顾随与国文系41级女生在辅仁大学女院垂花门前合影(后排右五为叶嘉莹)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大学二年级时的叶嘉莹已经有了若何的手笔。
小令《落梅风》:
寒灯烬,玉漏歇。点长空乱星残月。一天风送将冬至也。拥柴门半堆黄叶。
顾随师长西席评曰:“结二语逼真元人,未可以其看易而忽之。”与此同在一纸的还有两首小令,师长西席的总评是:“小令妙在自然;深刻之思力,健举之笔力,必要使人不觉。此作庶几近之。”
套数《般涉调耍孩儿》:
〔一煞〕见只见蜂蝶纷纭争嫩蕊,听只听杜宇声声啼断肠。春魂冉冉随风荡。今日个是踏青士女如云聚,嫡个我立马西风数雁行。事事堪惆怅。说什么吹箫击筑,访酒侣到高阳。
顾随师长西席旁批“立马七字好句”,并建议将末了一句中的“访”字和“到”字去掉。
叶嘉莹的辅仁大学奖证
《顾随与叶嘉莹》一书中收录了顾随师长西席批改叶嘉莹诗词曲习作五十七首,从中我们也能略窥为师的才思与敬业。《鹧鸪天》末句“几点流萤上树飞”,“上”字改为“绕”字,并注以“上字太猛,与萤不称,故易之”——这是一字之易。《春游杂咏》之七“年年空送夕阳归”句,“年年”改为“晚来”,并注以“年年字与夕阳字冲突”——这是一词之易。《寒假读诗偶得》“墨客原写世人情”一句,改为“面远景物世间情”——这是一句之易。有的改动可以看到是经由了反复的考虑,如《杨柳枝》之七“而本年夜似琅玡木,谁抚长条为泫然”二句,先说:“木字改树字何如?”后又建议:“末二句拟改作‘而今谁上琅玡道,为抚长条一泫然’。”
顾随批改叶嘉莹习作
叶嘉莹言及老师为她批改作业的环境时说:“一样平常说来,师长西席对我之习作改动的地方并不多,但虽然纵然只是一二字的更易,却每每可以给我极大的启示。师长西席对遣辞用字的感想熏染之敏锐,辨析之精微,可以说是对付学习任何文学体式之写作的人,都有极大的助益。”
除了推敲文句之外,顾随师长西席更对弟子的诗心细加呵护。如对套曲《仙吕赏花时》总评曰:“稳妥,有似明人之作。欠当行者,以少生辣之味耳。”对《临江仙·连日不乐夜读〈秋明集〉有作》词评曰:“是用意之作,但少清闲之致耳。”对《杨柳枝》八首之总评曰:“近作诗极见思致,但音节中稍欠和谐生动,不知作者以为何如耳?”对《初夏杂咏》四首之总评曰:“锤字坚实,想见工夫。但此更希望保存元气也。”对《忆萝月》词评曰:“太凄苦,青年人不宜如此。”如此等等,足见顾随师长西席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弟子欣赏之至、呵护有加。
有时,师生之间还相互唱和。1944年秋,叶嘉莹写了六首七言律诗,顾随师长西席发回时不仅一字未改,还附以六首和诗;叶嘉莹叠韵再和,顾随师长西席复作长句六章。
顾随致叶嘉莹书(1946年7月18日)
多年往后,叶嘉莹在文章中写道:“师长西席对我的师恩深厚,但因我年轻时的性情拘谨羞涩,很少独自去拜会师长西席,总是与同学一同去。见到师长西席后,也总是静聆教诲,很少发言,我对师长西席的仰慕,只是有时会写在诗词的作品中。”五古《题季师手写诗稿册子》所叙写的便是叶嘉莹对顾随师长西席的诗与字的各类感想熏染和内心诚挚的仰慕:
自得手佳编,吟诵忘朝夕。吾师重熬炼,辞句诚精密。想见酝酿时,经营非苟率。旧瓶入新酒,出语雄且杰。以此战诗坛,何止黄陈敌。小楷更工妙,直与晋唐接。气溢乌丝阑,卓荦见风骨。人向字中看,诗从心底出。淡宕风中兰,清严雪中柏。挥洒既多姿,盘旋尤有力。小语近人情,端厚如彭泽。诲人亦谆谆,虽劳无倦色。弟子愧凡夫,三年面墙壁。仰此高山高,可瞻不可及。
叶嘉莹听顾随师长西席讲课,自1942年后即未间断,包括毕业往后已在中学任教之时。那时顾随师长西席除了在辅仁大学担当唐宋诗的课程以外,还在中国大学教授词选和曲选,叶嘉莹常常骑车赶去两校旁听。
叶嘉莹条记
1947年初,弟子们要为老师五十周岁生日举行一场庆祝宴会,叶嘉莹受推撰写祝寿预备会的通启:
盖闻春回阆苑,庆南极之辉;诗咏閟宫,颂鲁侯之燕喜。以故麦丘之祝,既载齐庭;寿人之章,亦播乐府。诚以嘉时共乐,寿考同希。此在凡人,犹申祝典,况德业文章如我役夫羡季师长西席者乎。师长西席存树人之志,任秉木之劳。卅年讲学,教布幽燕。众口弦歌,风传洙泗。极精微之义理,赅中外之文章。偶言禅偈,语妙通玄。时写新词,霞真散绮。寒而毓翠,秀冬岭之孤松;望在出蓝,惠东风于细草。今岁仲春二日即阴历丁亥年正月十二日,为我役夫五旬晋一生日,而师母又值四旬晋九之岁,喜逢双寿,并在百龄。乐嘉耦之齐眉,颂君子之偕老。花开设帨,随淑气以俱欣;鸟解依人,感东风而益恋。凡我同门,并沐菁莪之化,常存桃李之情,固应跻堂晋拜,侑爵称觞。欲祝嘏之千秋,愿联欢于一日。尚望及门诸彦,共襄斯举,或抒怀抱,或贡词华。但使德教之昌期,应是同门之光彩。日之近矣,跂予望之。
叶嘉莹的才华在同学辈中是公认的,而这一篇富丽的笔墨,也当是献给老师最好的贺礼了。
起先,顾随师长西席欲将叶嘉莹的作品交给报刊揭橥,曾在教室上问她有没有笔名或者别号,叶嘉莹说没有,师长西席要她想一个,她想起佛经上提到的一个鸟名——迦陵,发音并与“嘉莹”附近,遂以为号。“迦陵”,系音译“迦陵频伽”的简称。《翻译名义集》卷六:“迦陵频伽,此云妙声鸟。”并引《正法念经》:“山谷旷野,个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所及者。”
传秘诀生
顾随师长西席常用禅宗古德的话“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勉励学生,希望他们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46年7月13日,顾随师长西席在信中表达了对叶嘉莹莫大的期许: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肯望足下能为苦水传秘诀生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拓,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南岳”指的是唐代高僧怀让,马祖道一随怀让学禅十年,嗣后开宗门、建丛林,对禅宗乃至中国佛教做出重大贡献。顾随师长西席以马祖为喻,告诫弟子不要马首是瞻为老师所局限,而应勇于打破首创属于自己的天地。至于如何能够“达到此目的”,信中说道:“除取径于蟹行笔墨外,无他途也。”所谓“蟹行笔墨”,指的是横向书写之字母笔墨。信中还说:“至少亦须通一两种外国文,能直接看‘洋鬼子’书,方能开扩心胸。”顾随师长西席此语,既是因材施教,又是履历之谈。“师长西席幼承家学,对古典早有深厚之教化,其后又毕业于北大之英文系,在为学方面能融古今中外为一体”,“这正是何以师长西席在论诗谈艺之际,能随时有高论妙悟的一个紧张缘故原由”。
1948年春,叶嘉莹要去南京结婚。顾随师长西席为赋《送嘉莹南下》一首相送,中间有句:“十载不雅观生非梦幻,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哀朽敢言吾道南。”“鹏起北”,由于叶嘉莹当时要离开北平去南方;“吾道南”,用的是禅宗典故,禅宗五祖弘忍传衣钵与六祖慧能时说“吾道南矣”。诗的意思是说,自己教了这么多年书,希望能够后继有人,而他的希望就寄托在叶嘉莹身上。
顾随致叶嘉莹书(1947年8月2日)
1948年11月,叶嘉莹随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丈夫赵东荪去了台湾。在《怀旧忆往——吊唁台大的几位师友》一文中,叶嘉莹说:老师“在信中殷殷向我先容了在台湾任教的他的几位朋侪,那便是当日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师长西席、郑骞师长西席,还有一位李霁野师长西席。顾师长西席在信中还附下了几张先容的名片,嘱我抵台后去拜会他们”。
叶嘉莹赴台之初,师生之间尚有通信联结。1948年12月4日,顾随师长西席在日记中写道:“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煮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此后不久,叶嘉莹与同在台湾的师长西席二女之英,便都失落去了音讯。1949年7月25日,师长西席在致弟子刘在昭的信中流露出内心的焦虑:“嘉莹与之英遂不得,彼两人其亦长长相见耶?”刘在昭是叶嘉莹最要好的朋友,师长西席此问,或许不无试探的存心吧。
事实远比顾随师长西席理解和想象的严重。1949年12月,叶嘉莹的丈夫因“白色胆怯”被捕。次年夏,她带着吃奶的女儿也被关了起来,虽在其后不久获释,但却失落去了教职和宿舍,无奈托身丈夫的一个亲戚家。而她的丈夫则连续羁押在左营军区附近的一个山区,三年之后才重获自由。至于顾随师长西席为叶嘉莹所写的那封荐书,在她的丈夫被捕之时即被搜没,尚且未到台北送呈台静农等。然而,时隔六十余年,令叶嘉莹激动欣喜的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创造那封信竟然一贯殽杂在当年发回的物品中,意外地“失落”而复得了。
顾随致台静农书(1948年12月10日)
1956年,已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叶嘉莹先后撰写揭橥了两篇评赏文章。一次,郑骞见到叶嘉莹,说“你所走的是顾羡季师长西席的路子”,只管郑骞认为这条路子并不好走,由于“作者要想做到自己能对诗歌不仅有精确而深刻的感想熏染,而且还能透过自己的感想熏染,传达和表明一种属于诗歌的既普遍又真实的感发之实质,这实在不是一件随意马虎的事”,但他仍对叶嘉莹十分讴歌:“你可以说是传了顾师长西席的衣钵,得其神髓了。”
从“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而至“为他人的对传承之任务的反思”,是叶嘉莹诗词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并由此转入理论研究的新阶段。在多年传授教化、研究的实践中,叶嘉莹对老师当年关于取径西方文化的叮嘱亦逐渐有了自觉和深刻的认识。在《我的诗词道路》序言中,她说:
一样平常说来,由于我自幼所接管的乃是传统教诲,因此我对付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原有一种偏爱。但多年来在外洋传授教化的结果,却使我深感到此种妙悟心通式的评说之难于使西方的学生接管和理解。这些年来,随着我英语阅读能力之逐渐进步,有时阅读一些西方批评理论的著作,竟然时时创造他们的理论,原来也与中国的传统文论有不少暗合之处。这种创造常使我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借用他们的理论能使中国传统中一些心通妙悟的体会,由此而得到思辨式的剖析息争释,对我而言,当然更是一种极大的欣愉。直到现在,我仍旧在这条路子上不断地探索着。
……我个人干事原有一个态度,那便是欲望与尽力在我,而成功却不必在我。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庶几不辜负当年我的尊亲和师长们对我的一片教诲和期望的心意。
(文章节选自《顾随和他的弟子》,2017年出版)
《顾随和他的弟子》
赵林涛 著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23654
45.00元
当代学术大师顾随师长西席(1897—1960)是名副实在的通家,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诲家。他的多位弟子,如周汝昌、叶嘉莹、郭预衡、吴小如等,或承其衣钵,或受其影响,造诣卓越,名满天下。他的许多教诲传授教化理念和教室讲授艺术,至今闪耀着聪慧的光芒,值得我们探寻、学习和借鉴。从1929年初登大学讲堂到50年代初,是顾随师长西席传授教化生涯的一个主要期间。本书述及的顾随师长西席的几位弟子,紧张是在40年代从师受教,顾随师长西席思想之精华,在与这几位高足的传授教化、交往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示。本书既展现了前辈学人朴拙的师生情意,又为读者深入理解顾随师长西席的平生业绩、德业文章供应了更多资料。
《迦陵说诗》
可听、可看的叶嘉莹古典诗词课
叶嘉莹师长西席倾毕生之功的古典诗歌国民读物,
进入中华书局官网,
收听音频版,
体悟古典诗歌的感发力量。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