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夜泊》是一首在唐诗中具有一定地位的绝句,古今有很多文学大家将其列为唐宋第一绝句,乃至有文人称作者张继的失落眠为不朽的失落眠。
那么我们如何来感想熏染和欣赏这首诗呢?要知道在中国,能够传世的诗词均是经由千淘万漉,经得起韶光考验的,张继的《枫桥夜泊》能够在诸多传世诗词里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确实有他出色的地方。
首先《枫桥夜泊》一诗在场景构建上很生动,乌啼、渔火、夜半钟声等词语的利用,能够让人看到诗句直接在脑中刻画出场景。场景构建对付言简意赅的绝句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在四句话里要能刻画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有时候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引起读者的共鸣”,所谓“读者的共鸣”我们可以大略地理解为感同身受。好的作品能构建出让人身临其境的场景,当你看到乌啼、渔火、夜半钟声并在脑中构建这一系列映像时,你仿佛就坐在那个扭捏的小江船里,那一刻你便是那个落榜的诗人。可以说精良的绝句差不多都有着同样精良的场景构建,像杜牧的《清明》,就构建了一个清明时节在小雨中赶路的行人问路的场景。像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构建的是“林中松下,墨客问小孩子:你屋里师傅呢?”的场景。常日情形了局景中有互动的不同主体时,场景构建要大略,也较为常见。像《枫桥夜泊》这样的场景构建,诗中主体在行为上一没有与其他人互动,二不与周围物什环境互动,却刻画出了一个让人身临其境的场景,实在是较为出众。
《枫桥夜泊》一诗的场景描写细致而又色彩光鲜,诗中并没有利用描述色彩的词,但是我们作为读者明明是知道的,白色的是“霜”,赤色的是“枫”。通过“霜”、“枫”这种有着显著色彩特色的词又使人感想熏染到了光鲜的色彩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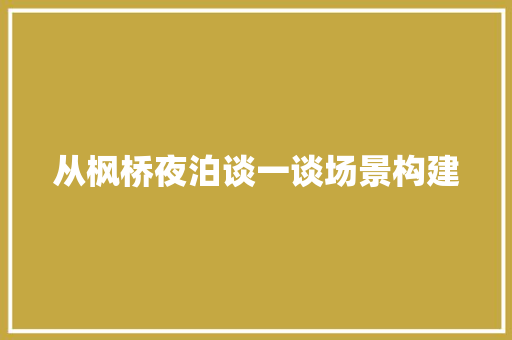
《枫桥夜泊》一诗的场景中动静比拟也是非常明显,动的是什么,是月、是乌鸦、是渔火、是船、是浪、是钟声,看起来场景里所有东西都在动。不动的是什么?是船舱里愁眠的作者。在中国古诗中,动静结合的手腕是较为常见的,像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中“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明明是“独坐”却坐出了“两不厌”,像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东风不度玉门关。”一个“怨”字盘活全场。而在《枫桥夜泊》一诗中,作者并没有靠某一个诗眼来带动全场感情,而是用作者愁眠的状态使作者看起来与动态环境扞格难入的静默具有了合理性,终极寒山寺那夜半钟声的锤击,将原来静默着的作者情绪宣泄得淋漓尽致。
《枫桥夜泊》一诗中这种匪夷所思的动静结合术,带来了非常充足的情绪冲击力,这种手腕,我后来在鲁迅师长西席的《而已集·小杂感》里也曾见过一次——“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去世,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去世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以为他们吵闹。”场景跃然纸上,情绪迎面而来。
在我们的生活和事情中,尤其是从事文宣信息类事情的同道,有时候会由于自己写出来的材料或者宣布中描述的人物形象不足丰满生动而苦恼,在这时就可以利用到类似的场景构建的技巧。比方说我们通过笔墨描述一个工人热爱劳动,我们有时候会说他由于常年劳作,手上皮肤皴裂,但是这种形容就不如描述一只握着工具的手,因感化着汗渍与机油而黝黑的工具与像老树皮一样手,且远比反复强调搬了多少砖、修了多少机器有画面感。同样当我们描述一个人物伏案事情较多时,一样平常会写人物从事事情后写了大量的笔墨,而这种描述就不如凌晨的灯光、撞着窗纱的飞虫、磨坏的袖口、房间角落里放着的“笔冢”,当这样的几个映像组合起来,读者更随意马虎产生现场感。
构建合理的场景使读者身临其境,从而引起共鸣,是通过笔墨触摸民气的一个最为常见也非常有效的手段,《枫桥夜泊》作为个中俊彦,不仅在文学创作中,包括平时事情中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