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为社会教诲之一种,其动听也深,入人也切,尤能匆匆进智识,移易脾气,魔力之伟大几于不可思议。故有识者认为极有研究之代价,不得以平凡游戏目之。近代戏剧昌明,占艺术界主要之位置,良有以也。
戏剧所在多有,国异而省不同。试究其身分,则腔调各别,派别稍殊,精神上固无不同者,即就起目的结果而论,其以是谋社会进步,与社会之以是藉以兴起不雅观感者,亦未始稍有不同之点焉。
就余磋商有得,当以戏剧二字为演译的名词,内含戏与剧两大部分。戏为一种引人入胜之工具,如猴戏、马戏、狗戏……侧重于做的方面者也;剧为一种现身说法之利器,如电影、苏滩、南词……侧重于唱的方面者也(电影演出故事,幕幕有解释,近年并有有声电影之发明)。
言慧珠在电影《同心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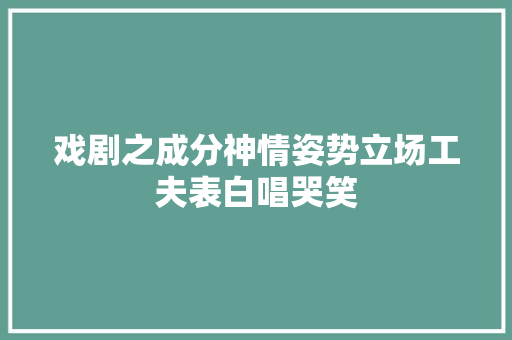
迨至戏与剧混而为一,添花锦上,相得益彰,而规模以备,适成现社会上所称为“戏”之戏剧。有现身说法处,亦有引人入胜处,故足补社会教诲之不及,而汉调、京调、徽调、浙调(浙调谓宁绍之乱弹)……均有十百年之历史,发明之人盖不知费去几何心血矣。彼普通人于戏与剧之差异,且未分清,无怪乎错认京调一门为戏剧之单独名词也。
吾之所谓戏剧之身分,系指戏剧演出者做唱之身分而言,腔无分东西南北,调无分汉京徽浙,而行头、布景、彩色、切末,更不在论列范围之内。是故不得不预先声明者也。矧戏剧为戏与剧两种组织而成,而戏与剧又各有其多少之身分,始得编排成戏,断非无意义、无经纬者所能组成此一定之理也。西方之舞蹈近于戏,唱歌近于剧,文明进化,舞与歌同冶于一炉,即现在最盛行之歌舞也。从可知歌舞云者,实即戏剧之缩影,兹就戏剧分别述之。
甲:戏
高档动物皆富于摹仿性,而以人类为尤甚,孩童至五六岁呱呱学语,即知结伴游戏,为家庭之组织,作迎送之程序(俗称办人家),旋以摹仿性扩大于游戏上,加以各类之规则,演为有程序之游戏,戏之起源实即来源于此。
考其完成,约分四部:
一、神色:神色有喜怒哀乐之分,演戏时须将戏中人喜怒哀乐之神色,移而置之,稍一不慎,即失落其摹仿之功能。既艺术上之代价,善恶忠奸,贞淫贵贱,又复各有其身份,各有其环境,且喜不止于笑,怒亦不止于骂、哀不止于哭,乐亦不止于舞。必须逐一谅解,曲曲传出方得谓为尽神色之能事。例如谭鑫培演《打棍出箱》俨然为一穷愁潦倒之疯秀才,金秀山演《逍遥津》,无异汉代曹操之复活……故知伶伦当以神色为戏之第一步功夫也。
金秀山之李克用
二、姿势:身体台步为姿势之根基,而化妆扮相(附勾脸及服装)之能否合式,尤为姿势之最大关键。至于技艺之灵敏活泼,脚步之稳健妥适,在在均须磋商,以求其胜任而愉快。大抵善演之者,自能入情入理,丝毫不苟。空中无楼阁,而楼阁毕现,台上无山水,而山水杂陈,是均有赖于演戏人之姿势。故小翠花《玉镯记》中之各类姿势,似真似幻,亦假亦真,能令人惦记无已。尝谓吾国戏剧之好处,全在于空中有实,自电光、布景东渐后,花样翻新,几于台金上均陈真品,而好处反而不彰,良可惜也。故姿势要当为演戏者第二步功夫。
三、态度:态度亦称工架,似与姿势相仿佛,然一经体会,大有分别。盖姿势者,千变万化,各有其妙,是为分拆的;态度则举止行动,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是为全体的。同一须生,伍子胥与老薛保完备不同;同一秦琼,卖马时与拜将时又复各别;至小生戏中,扮吕布要有英武气,饰宝玉洒脱气,儒雅风骚,穷酸华贵,又复各有其身份,各有其形状。旦角之端庄淫靡与悍泼刁奸,做法亦截然不同。各类态度,实故意想不到之神妙,倘能摹仿戏中人当时情中形,加以从容理会之功,自能恰到好处。近伶如梅兰芳之以是能负莫大之盛名,盖即于戏中人之态度,多有移而置之自身之特长,故虽一举足一动手之微,亦靡不尽心研究,惟妙惟肖,试本不雅观其西施与太真之不同,袭人与晴雯之迥异,诚令人叹为无从描写之实艺。他如尚小云之卓文君,前后判若数人,琴挑、私奔、当垆认父,各有各的态度,各善于各的胜场。此种摹仿功夫,曾不知其费几许思考推考而来,故演戏应以态度为第三步功夫。
梅兰芳、尚小云之《西厢记》
四、工夫:武行之踢扑跌打为戏中真实功夫,故哑吧子王益芳亦能负武行之盛誉。刀枪剑戟,各类花把之动作,虽为姿势技能之一部,要亦非加以实在工夫不可。例如穿山甲之飞鋿,盖叫天之玩圈,工夫均为不弱。文场中如《碰碑》之弃甲丢盔,《琼林宴》之出箱顶鞋,《探母》中见娘时之甩发,《秦良玉》中愤怒时之割袖。此外如旗带发须,虽在混战中,亦不得有丝毫之紊乱;衣袖彩羽,虽在激舞中,亦不得有些微之错杂,此皆非常时练习,有真实工夫不可。是应列为戏之第四步工夫。
乙:剧
有戏无剧,迹似无意识之动,且于审都雅感及传播故事之效验,亦极无着落处,故有智者从诗词之皮面上,思所以为雅俗共赏之创造,于是乎管弦杂陈,腔调百出。所谓剧也者,应运而生,终乃化合于戏,而成今日之戏剧。谈剧者,撇戏而言剧,于其身分上,有言之详尽者,兹亦大抵分为四部:
一、表:剧中多暗场,自非由演剧人加以解释为明晰之交代不可。一人说几人之事,一时讲几时之话,自为最难之事。如《坐宫》一场,不特通名报姓,又复说尽前后在番之历史,使不雅观众得以明白其究竟,诚属不易之技能。彼脑筋不敏之人,每每经表辞与白口混而为一,则愈表而愈不明白,岂非恨事?须知表为演剧人对付不雅观众之说白,字眼既贵响亮,抑扬尤宜合度,神色、姿势、态度间,虽有剧中人在,而尤须有演剧人之我在,庶乎其不远矣。抑又有不开口之表法,则全在于姿势与精神二者之流露,简称之曰表情。是又不可以不知也,此为演剧之第一步功夫。
时慧宝之《坐宫》
二、白:白为剧中人与剧中人说话之用语,例如“大嫂请了”“请了,军爷,敢是迷失落路途?”神色、姿势与态度之三要素,必须完备移置于剧中人身上,自然相对之时,入情入理,语句须清楚干脆,固不待言,且须弯曲婉转,使不雅观众如闻古人说话,庶几近之。又有似白非白,似表非表之词句,则为引子(例如“凤阁龙楼万古千秋”)与念歌(例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两种之差异。剧中人各占身份,务要念得清晰,方为适当。尝不雅观金少山与慈瑞全之《法门寺》,“大虫吃小虫,小虫吃毛虫”,阉官景况,跃然欲活,是故长于说白者矣。是应列为演剧之第二步功夫。
三、唱:唱为审都雅感所侧重,似为剧中中坚身分,实在不然。借使仅仅把稳于唱工,则毋宁清音坐唱,较为简便。留声机器费省而用久,更觉其有合于经济,又何多于戏剧乎?故唱也者,只得仍为剧中身分之一部,不得认为中坚。不雅观于近今之文明戏,个中无唱句,亦能引人人中入胜,当可憬然,其故,大抵唱合表白二者而成。换言之,即为有音韵之表白,剧中人与剧中人之对语用唱,例如“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我问他好来,他倒好”……演剧人对不雅观众表明剧情、韶光,亦用唱,例如“上前去说几句知心话看他知情不知情……”惟是唱之基本为嗓音,必须洪亮圆稳,抑扬合拍,方为无疵,故咬字贵乎准确,韵味贵乎浓厚,故唱应列为演剧之第三步功夫。
四、哭笑:在生理学与性理学,均以哭笑为同一之浸染,故剧中之哭笑,亦宜列为一事。有真哭真笑,有假哭假笑,有陪哭陪笑,有似哭似笑,有非哭非笑,又有忠臣之哭笑,奸庸之哭笑,情人之哭笑,恨人之哭笑,各类不同。在剧中人,固为一时情绪之冲动,而在演剧人,则身在事外,安得有如许之情绪乎?故必当细心摩拟,用力推考,方得探悉其大概。其于戏中之四大身分,关系密切,尤须加以研究照顾之功,来能逼于真,始得谓有剧情上脸之艺术。故哭与笑亦剧中之一主要身分也,尝谓脸上有剧情,方可称为得演剧之神髓。如谭鑫培之得力处,即全在于一脸都是戏。盖于哭笑间具有湛深之研究,而于哭笑之外,若笑尾哭前神色,亦有相称之演出,学者更不可以不察。此为剧中之第四步功夫。
谭鑫培之《探母》
由是言之,可知戏剧内包神色、姿势、态度、工夫、表、白、唱与哭笑八个身分,机括辐辏,互应顾及,演剧人果能八字全工,唱做兼善,自系上选名角;若偶得一二,但足以吸引社会之崇奉,亦不失落为中等人材,有配角之资格;至若一无所长,仅足与言跑龙套、背旗帜而已,抑亦有需于纯熟的与活泼之精神,方得尽过场之能事,否则竹头木屑,行尸走肉,又何贵乎有此赘瘤乎?
近今最时髦之谭派须生,首推余(岩)马(连良)二人,然细究其八大身分中,似于表、白二者均不免有嗓低字浮之病,亦微觉其有美中不敷之嫌。其它派别未明,如春间随尚小云南下之杨宝忠,唱工固亦未始无一二句可听处,然其对付极占主要地位之表白二身分,均属不之研究,几于无戏不学老谭之《卖马》与《碰碑》,神气沮丧,声在喉底,凡遇表、白处但见其口角开阖,卒未辨其道白云何(唱快板亦听不清)。吾甚望其猛加致力也。
我国自改造以还,日见伶伦之趋重艺术化,病榻彷徨,不免有改良戏剧之思潮,回旋于脑海中,有时书此,聊以遗兴,质之豁公,以为何如。
(《戏剧月刊》第1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