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墙送过秋千影
——张先的“影”诗词赏析
川 雪
张先长于用“影”字描写景物,其词作中,除了“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
张先的《青门引》,触景伤怀,感时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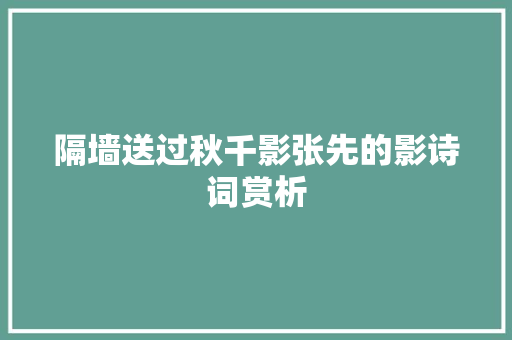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此词为春日怀人之作。词中所写韶光是寒食节近清明时,地点是词人独处的家中。全词抒写了词人感于自己生活孤独寂寞,因外景而引发的怀旧情怀和忧苦心境。
这首词构思新奇、风雅。用从景象的忽冷忽暖,风雨时至,陪衬词人的心绪不安;在残花中饮酒,展现词人的失落意感伤;不说酒意被角声所惊而渐醒,却说是被风吹醒;入夜月明人静,只见隔墙送来秋千之影,再现词人瞬间隐约之喜。全词蕴藉宛转,丽辞腻声,表现出张词的风格。
上片起首两句,写词人对春日里景象频繁变革的感想熏染。“乍暖”,见出是由春寒忽然变暖。“还”字一转,引出又一次变革:风雨忽来,轻冷袭人。轻寒的风雨,一贯到晚上才止住了。词人感触之敏锐,不但表示在对景象变革的频繁上,更表示在景象每次变革的精确上。天暖之感为“乍”,天冷之感为“轻”,风雨之定为“方”。遣词风雅确切,暗切奇妙人情。
人们对自然征象变换的感触,最随意马虎暗暗引起对人事沧桑的悲哀。“庭轩”一句,由景象转写现境,并点出清明这一景象变革多真个特定时节。至此,这“寂寞”之感就进而属于内心的感想熏染了。歇拍二句,层层逼出主题:春已迟暮,花已凋零,自然界的变迁,隐喻着人事的沧桑,美好事物的破灭,种下了心灵的病根。此病无药可治,唯有借酒浇愁而已。但醉了酒,失落去理性的低廉甜头,只会加重心头的愁绪。更使人感触的是这样的履历已不是头一遭。去年如此,今年也不例外,“又是去年病”点明词旨。
过片承醉酒之后而来。“楼头画角风吹醒”,兼写两种觉得。凄厉的角声,清冷的晚风,使酣醉的人复苏过来。这一个“醒”字,表现出角声晚风并至而醉人不得不清醒的一霎光阴反应,同时也暗示酒醉之深和愁绪之重。伤心人被迫醒来自是痛楚不堪,“入夜”一句,即以现境象征痛楚的心境。夜色降临,心情更加黯然,更加沉重。而重重深闭的院门更隐喻着不得开启的心扉。结句指出重门也阻隔不了触景伤怀,溶溶月光居然把隔墙的秋千影子送了过来。月光下的秋千影子是幽微的,描写这一感触,也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烦闷的心灵。“那堪”二字,着重揭示为秋千影所触动的情怀。
此词用景表情,寓情于景,“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尤其是词之末句“隔墙送过秋千影”,写人却言物,写物却只写物之影,影是人,人又如影之虚之无,令人忆及荡秋千的伊人倩影,确实写出了隽永的词味。总之,张先词艺术上的蕴藉和韵味,此词中得到了充分表示。
张先的《题西溪无相院》诗,写景细致,错落有致:
积水涵虚高下清,几家门静岸痕平。
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棹声。
入郭僧寻尘里去,过桥人似鉴中行。
已凭暂雨添秋色,莫放修芦碍月生。
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晏殊知永兴军,征请张先为通判赴陕。三年后张先又重游长安,其间到过华州。时张先已年过六十,然精力兴旺,诗兴不衰。这首诗便是作者在华州时一次游览后创作的。
这首诗写的是秋雨后无相寺前的景致,主景是水。首联写西溪及附近的湖泊,经由一场秋雨,水位上涨,远近一片浑茫澄澈,与秋空相接;水边的人家,彷佛浮在水上。“积水涵虚”四字,场面很大,仿佛唐代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的景况。孟浩然写洞庭湖水,描摹了湖的渺茫宽阔;张先在这里突出江南雨后河湖溪塘涨满水的情形,是小环境组合成的大环境,都很神似。“高下清”即孟浩然诗的“浑太清”,都写秋日天空晴朗,水光澄碧的景象。次句写水边人家,以“岸痕平”说水涨得高,与“几家门”成为一个平面,也活生生地画出雨后江南水乡的奇丽景致。
首联从远处、大处落笔,展示西溪的独特风貌。颔联笔触一转,从小处、近处着墨,使诗情飞动。出句描述微风吹来,满池的浮萍裂开了,露出了一段水面,水面上倒映出青山的影子;对句写一叶小舟归来,船帮与水中的葑草摩擦,发出沙沙的响声。“浮萍破”,这是一个极眇小而不易察觉的物象,是水上微风初起所致,被墨客捕捉住了。一个“破”字,寓动于静,体物入微。草声是极微弱的声响,为墨客听到,足见其静,此乃以动衬静的笔法,给以生趣。此联一见一听,一静一动,错落有致,妙趣横生。
颈联仍旧写景,但通过人这个主体来写,还是以水作背景。一句写入郭僧,照料题面“无相院”;一句写过桥人,点缀水乡,二句又相互呼应。僧到城里去,加以“尘里”二字,说城市鼓噪,反衬无相寺所在地的静寂清净;人过桥,以“鉴中行”形容,说出桥下水之清澈,回照首句,又以面前环境的清旷与上句的“尘里”为难刁难比,表达墨客自己对景致的欣赏。
尾联用逆挽虚收法。“已凭暂雨添秋色”一句,在篇束点出,确是巧设安排。一是突出了西溪之妙境,先绘景后叙其所由出;二是可以放开一步,宕出远神。“莫放修芦碍月生”,意谓秋雨之后,芦苇勃生,莫让它态意长高,使人领略不到深潭月影。以雨后芦苇长高作一虚设,便把白天所见的景致扩大到未见的溪月,拓出了另一番想象的天下,给人以回味。这一结余味悠然,又与首句“积水涵虚”相应。
张先善写“影”,人称“张三影”。他写影的本领,在此诗中也可见到。“浮萍破处见山影”是明写;“过桥人似鉴中行”,是暗写;“莫放修芦碍月生”,是虚写;为全诗增长了活气和情趣。全诗险些全是写景,纵然是尾联,也把情浸入景中,是一幅幽美的风景画。
张先的《木兰花 ·乙卯吴兴寒食》,书写了词人细腻的美感体验:
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芳洲拾翠暮望归,野秀踏青来不定。
行人去后遥山瞑,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张先词的蕴藉清丽在后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示,写此词时词人已是八十六岁的老人。看惯了潮起潮落,看淡了相思情愁。词艺更臻纯熟,意境更趋空灵。这首词,散发着清新的气息。描述了吴兴一代的风尚习气,书写词人细腻的美感体验。
这首词描述了江南寒食节的风尚。上片紧张是日间的描写,以动景为主。包括赛龙舟的男儿,荡秋千的女郎,在郊野踏青、探花,一贯游乐到夜晚才散去,表现欢快、爽朗的心境。句句写人,句句灵动,充分反响了活泼的活气。迟暮之年有此心境,足见词人晚年的超脱和达不雅观。
下片入夜,紧张描写静景。词人的视野由远方收回到池院,中庭月光,树下杨花,一派清明。此时,更多的是流露一种沉思和忧伤之情。白天的繁盛热闹繁荣到夜深的清寂,一动一静,一人一物,一情一景。在自然与人的交互中实现了内在与外在精神气质的平衡。此时的外界自然已经活了,它听懂了抒怀主人公的言语,词人与杨花、与飞影、与月光等自然景物脉脉相对,感情随着自然物景的转化而发生着奇妙的变革。“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勾勒出一种宁静清明的景象,得上片的衬托,以动衬静,更见深度。
张先创造的这个艺术境界既真实又虚幻,我们仿佛置身个中,似曾相识。但作者置笔的朦胧与虚幻又使我们产生了陌生感和一定的间隔。在这种或虚或实的氛围当中,读者的心里也存在着远近感想熏染的变革,在这种变革当中产生了美感,此种美感直接为心灵所感想熏染。他的
张先的《系腰裙 》,在朦胧与虚幻中感想熏染真实美景:
惜霜蟾照夜云天。朦胧影、画勾阑。人情纵似长情月,算一年年。又能得、几番圆。
欲寄西江题叶字,流不到、五亭前。东池始有荷新绿,尚小如钱。问何日藕、几时莲。
上片为空蒙之景,在景物上涉及到了“霜蟾”“娼寮影”“东池”“荷”,遐想到的景“叶字”“藕”“莲”,秋月当空,栏杆投影,东池一片幼荷初放,荷叶在月光下闪动着碧玉般的色彩`。整体觉得清新、自然、明净,意象空灵、玲珑。在这样的氛围下词人感叹“欲寄西江题叶字,流不到,玉亭前”。接着,由此景又产生“问何日藕,几时莲”,将人生有限与明月的阴晴圆缺相连,表达了词人期盼团圆的心情,也揭示了人生聚少离多的悲剧处境。
张先创造的这个艺术境界既真实又虚幻,我们仿佛置身个中,似曾相识。但词人置笔的朦胧与虚幻又使我们产生了陌生感和一定的间隔。在这种或虚或实的氛围当中,读者的心里也存在着远近感想熏染的变革,在这种变革当中产生了美感,此种美感直接为心灵所感想熏染。
张先用“影”字描述景物产生的朦胧美感,常在一些词中涌现。如《忆秦娥·参差竹》中的 “忆苕溪、寒影透清玉”, 《宴春台慢·仙吕宫》中的“犹有花上月,清影徘徊”等,我们在欣赏这些词句时,要利用遐想和想象,使朦胧的景物在头脑中清晰起来,从而更好的理解和把握词人创造的幽好意境,得到真实的美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