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墨客借诗言情,言“悲情”远远多于写“乐情”。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白居易《梦微之》)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离思五首·其四》)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纳兰性德《木兰词·拟古断交词柬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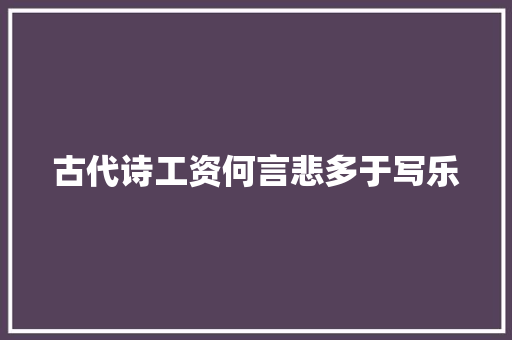
字字滴泪,句句含悲。
悲情的诗性魅力太大!
当然,写乐情的古诗也不少,但与言悲情的数量比较,便颇有些微不足道了。
为什么会涌现这一有趣的征象?
这又要从“悲”与“乐”情绪特性的差异以及古墨客的人生经历谈起了。
悲情比乐情更具艺术代价。
悲情,在于开释。
悲哀之情,好比是酒,好比是毒品,能最大限度调动人的情绪感想熏染力,延展情绪细胞的张力,使人的感情如潮水般蔓延、荡开,进而形成悲场。
悲场是人为制造的浪漫、戏剧化的气氛,使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乐情,在于内收。
快乐的意义重在享受,在于忘怀浩瀚烦恼,将情绪内收、集中在快乐的愉悦感上。随着韶光推移,快乐之情会逐渐淡薄,缩小,末了完备消逝,难以影象。
由此不雅观之,悲情的影响力、持久力远远超过乐情。
悲情,更易让人反思,匆匆人深刻。
悲,实在是人类又想躲避又不自觉沉沦的情绪。
当人生之境遭遇悲情,更能让我们静下心来专注思考。对自己的人生做一番回顾,翻检,反思,总结。人便会在这一系列思维活动中蜕变发展。
乐,更像享受美食,只在吃确当下有愉悦感,事后只余轻描淡写的袅烟。
乐情的享受性子,让人产生惰性,趋安逸性,自然难以深入思考。
以是,乐情只是感情一次性消费品,唯有悲情与诗意最靠近,最能催发诗情。
古代墨客,人生轨迹实在十分单调:读书,科举,做官(或归隐),辞归。
人生的大部分岁月都奉献给了官场,对仕途之路孜孜以求,对功名汲汲渴慕。
但皇权至上、等级森严的封建时期,仕途自古多艰险。
在做官的进程中,惊险,压抑,失落意常伴身侧,从现实来看,古墨客的生活不快意多于快意,悲事多于乐事。
这也是古诗常见悲情的另一个主要缘故原由。
悲情真是一剂毒药,让人避之不及,却又让人无限沉沦。也正由于如此,它才更具有诗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