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词的大意是:驿站的梅花已经凋零,溪桥旁的柳树也垂下又细又嫩的枝条。游子迎着东风、踏着芳草扬鞭远行。遥遥征途伴着无尽的离愁,就像那春江之水,迢迢不断。柔肠寸寸痛断,粉泪盈盈流淌。不要登楼凭栏了望。草地的尽头是春山,而游子却在那重重春山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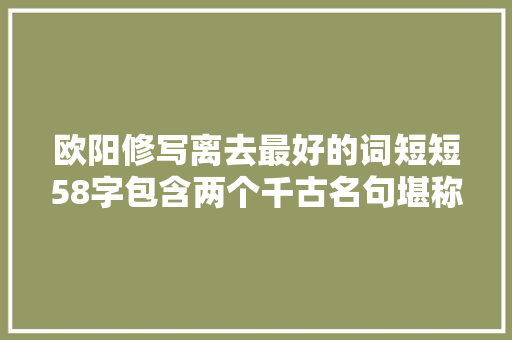
全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游子,下片写思妇。
上片是远行游子征途中的所见所感。开篇便是一幅明丽的春景图:驿馆旁的梅花已经零落,而溪桥边的春柳则发出了嫩绿的新枝,暖风吹拂着散发着芳香的青草,游子摇缰催马,行驶在美好的春光中。景致如此之好,但游子却无心欣赏,由于这芳草、这杨柳、这落梅无不触动他的离愁。这离愁随着相隔路程的越远,离去韶光的越久而越积越多,就像那春江之水,无穷无尽。
上片的前三句,词人选取了富有“离去”意象的梅、柳、草,既表现春天的景致,也寄寓了离人的伤怀,实景虚用,虚实结合,耐人寻味。后两句见景设喻,自然合理,形象生动,意境堪比李煜“问君能有多少很多多少愁,宛如彷佛一江春水向东流”,因而成了千古传颂的名句。
词的下片,词人抛开游子,变换角度,转写思妇。游子远行,思念着家里,而家里的思妇也同样思念着远人。她愁肠百结,寸寸欲断;泪水盈盈,流满双腮。但她再相思难过,也不能登高了望,由于倚楼凭阑,看到的只是那杂草繁茂的原野,原野的尽头才是那绵绵的青山,而她念着的人,还在更远的青山之外。思妇登高,目光为春山所阻,而思念却追随征人到海角天涯,目光有限,相思无限,情意深长而又哀婉欲绝。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这两句词广受后世好评。卓人月称“不厌百回读”;王世祯赞“此淡语之有情者也”。明代陈大声作《蝶恋花》,曾化用了这两句词,落句为“千里青山劳望远,行人更比青山远”,却被人诟病“面虽稍更,而意句仍昔。但是偷句之钝,何可避也”。
欧阳修的这首《踏莎行》以乐写愁,虚实相融,设喻奥妙,且从男、女两个角度写离思,这都是本词的艺术特色。而一首58字的小令,就有两大千古名句,足见文忠公的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