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话杜牧的《赠别》之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烛炬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虽然不是所有古诗词都有这种情形,不过粤语的确保留了唔少古汉语嘅发音,以是有些诗词用粤语读会更加押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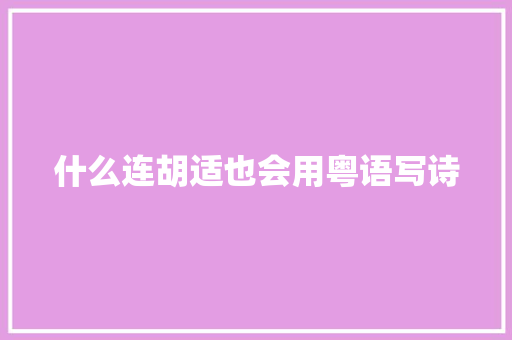
实在粤语不但可以用来朗读古诗词,还可以直接用来写诗!
有学者将用粤语写的诗歌叫做粤语方言诗,经历过民歌、新民歌(即粤讴,广东珠三角地区曲艺说唱之一)、旧体方言诗、自由体方言诗的演化。
▲《粤讴》内页,图片来源见水印
根据已有资料,在19世纪,岭南地区已经有人考试测验用粤语口语来写诗,由于粤语俚语、歇后语、典故非常多,形容词十分生动有趣,因此写入诗中不像一样平常诗歌那么文绉绉,反而令人以为诙谐盏鬼。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粤语诗盛极一时,不少岭南的文人雅士都用粤语入诗以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粤语诗一度与国语讽刺诗诗齐头并进。
但是对付大多数人来说,反而对这种市井气十足的粤语艺术感到陌生,乃至会以为:“啊?原来还有这种东西?”
今日就和大家先容这种,盏鬼又风趣的粤语诗,欣赏粤语入诗可以有多玄妙好玩!
何淡如
1820-1913
原学名文雄,后由于替人考试的事情被外扬开去,认为自己“人生再难出头”,于是将“文”字“砍头”,改为“又熊”。
说到粤语入诗的代表人物,绝对少不了以啜核无情对出名、被誉为“粤语入诗”祖师爷的何淡如啦!
你不要看佢帮老婆改名“人菊”就以为佢没文化啊(“人淡如菊”,问你服未?),淡如兄的绝技——无情对,真的有料又顶瘾:
开始仲以为佢乱说,连国家名、云吞都用来对对,负责一看才创造,无论是词性还是意思,每个字都对得刚刚好!
不过,文人始终是文人,淡如兄一旦负责起来,绝对反面你开玩笑:
注:沈展云认为“狡”应写作“姣”,即普通话中的“骚”。
大家不妨猜猜,这首诗说的是什么?
A:有人个老婆跟别人走了
B:有只母猪走失落了
C:红拂女、卓文君的风骚史
这首《代人访失落猪母赏帖七律》,措辞朴实大略,一眼就看出(实在看不出)是一首“寻猪缘由”啦,不选B,你说还可以选什么?!
用红拂女“发姣”、卓文君“跟佬走”比喻母猪走失落,完备没有考虑过红拂女同卓文君的感想熏染!
令人看完笑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去找猪,“何·啜核鬼才·淡·笔下无情·如”果真名不虚传!
廖恩焘
1865-1954
字凤舒,号忏庵,革命先烈廖仲恺之兄。
善于创作粤讴和广东俗话诗,著有《嬉笑集》。
民国期间,粤语诗的代表人物就有廖恩焘,以“珠海梦余生”为笔名,出了《嬉笑集》这本书,收录了他从前用粤语写的七言律诗,席卷不同题材,比如《自由女》,便是写当时的时尚女郎:
又有说历史人物的《范增》:
好似“掘尾龙”、“两头舂”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表达,如果不熟习粤语,又怎会感想熏染到它们在诗里面的魅力?
廖恩焘不但会用特色的粤语字词入诗,还兼顾了诗歌的对仗:“湿水马骝”对“烂泥菩萨”,负责贴切!
粤语诗“发热友”
除了何淡如、廖恩焘两位专家之外,余祖明的《广东历代诗钞》还记载了胡汉民、李蟠等粤语诗“业余”爱好者,同样有佳作。
胡汉民
1879-1936
字展堂,号不匮室主,广东番禺县人。
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曾为海珠桥题字。
胡汉民写过一首《韩信》:
他还有一首《垓下诗》:
“后生哥”、“行埋”、“唔慌”、“冇面”等都是粤语特有的用法。
看到诗之前,你有没想到原来可以这样用粤语来评价韩信同项羽?
李蟠
1893-1943
别号李根仙,广东中隐士。
而李蟠就有一首写于抗战期间的《闻捷》:
“氹氹”在粤语里面就见得多啦,至于叠字用的“棍棍”……
你有没有发觉这首粤语诗莫名多了几分可爱趣怪的觉得?
学写粤语诗的安徽人胡适
1891-1962
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铁儿等。
安徽绩溪上庄村落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
粤人写粤语诗不奇怪,原来以前连来自安徽的胡适也试过写粤语诗!
胡适1935年来广东旅游,闲时看到一本叫《粤讴》的书,一时兴起就用从书入面学到的广州话写了首《黄花岗》:
胡适后来提到,原来第三句他写的是“咪话火把唔够亮”,后来将“亮”改为“猛”,整首诗的粤语韵味才算完备表示出来!
黄霑
1941-2004
表字亦芹,另有笔名不文霑。
“喷鼻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著有《不文集》。
而说到离我们最近的粤语诗创作者,怎么少得了霑叔!
他最最最经典的粤语诗作品,同时也是大家最熟习、印象最深刻的——
(特殊约请演出高朋:唐伯虎)
这首诗由于某种你和我都明白的缘故原由,就不另作阐明啦。有些事情,只可融会,不可言传!
实在粤语入诗,不但极具意见意义性,还有一种隐蔽的“实用性”。
近代有位墨客曾经这样评价岭南:“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
他认为岭南的诗歌难与江南的相提并论,实际上反响出旧时大众对岭南“文教不盛”的片面印象。
而这些有写历史的粤语诗,令粤语的存在代价更加凸显,印证岭南文化不是千年不变的沙漠,纵然说不上是辉煌繁盛,但岭南文化能够流传、传承至今,绝对渊源有自。
可惜的是,就连粤语诗的个中一个承载体——粤语,都面临困境:越来越幼年朋友会主动利用粤语,乃至对粤语产生一种抗拒生理。
困境之下,本来就算是“冷门艺术”的粤语诗,又会有多少人乐意关注、重视,乃至是创作呢?
粤语诗会不会有后继无人的一日呢?
资料来源:
方宽烈《谈广东方言的格律诗》、胡文辉《粤语与旧诗》、维基百科等。
各位自己友
你们最心水哪首粤语诗?
你还知道哪些盏鬼粤语诗?
欢迎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