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汉书·艺文志·诗赋·序》云:“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云。”这段笔墨对研究汉代礼乐文化及乐府歌诗有主要意义,值得我们重视。然而,迄今学术界对此事的认识并未尽得其本意,乃至存在陈陈相袭的误解。尤其是对“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语的理解,古今以来多以为是说乐府歌诗反响了社会现实生活,歌咏了民生疾苦,亦即所谓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如斯。今则校阅阅兵载籍,揆以道理,对此别作新解,曰:《汉志》所谓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非说的是社会时势,而是本言汉武帝夜祭用乐,以表达敬拜时对神祇所特有的“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之意。但是《汉书·艺文志·诗赋》不但著录了敬拜乐歌,也有人间歌诗,故《序》又云“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则又兼及了礼乐的教养功能。
现对此新解申说如次,请学术界同仁批评见教。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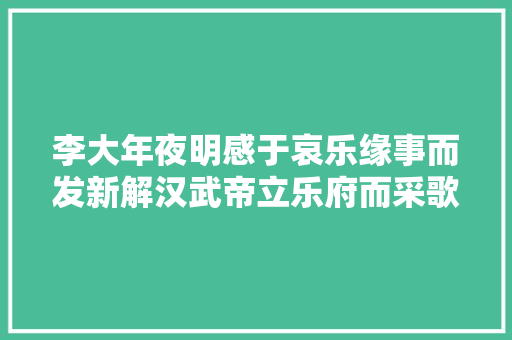
考汉武帝之始“立乐府而采歌谣”,后又造敬拜新歌之史事,其本意是为了夜祭时所用笙歌的须要。对此进行必要的谈论,是我们精确理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条件和根本。
首先要指出的是,《汉书》中关于武帝夜祭用乐的记载,《礼乐志》详于《艺文志》。而据《汉书·艺文志·序》,《艺文志》乃根据刘歆《七略》而“删其要”。又据《汉书·叙传下》,《礼乐志》在十《志》第二、《艺文志》在第十。今所读《汉书》,《艺文志》在卷三十,其对汉武帝夜祭用乐之事的记载,相称概括简单,故需检读其前《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的记载,还需检读《汉书》卷二十五《郊祀志》以及《艺文志》本身对礼乐歌诗文献的著录等,大义方明。刘歆《七略》原来,已不得见,而《汉书》如此行文,则盖其体例使然,所谓“详于前而略于后”也,需参互以见义,似不必视之为叙事疏略,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叙事上的特点,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确理解,故不可不辩。
武帝夜祭用乐之事,《史记·乐书》始有记载,而以《汉书·礼乐志》言之尤详。《史记·乐书》云:“至今上登基,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汉书·礼乐志》则云:“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歌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
将上述《史记》《汉书》的记载与有关文籍综合剖析,有可议者二,以补《艺文志》叙事之简单。
其一,关于武帝夜祭用民间乐。
《艺文志》云“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但未言武帝“立乐府”乃是为了“定郊祀之礼”用乐的须要,而其用乐,即《礼乐志》所谓“采诗夜诵”的“赵、代、秦、楚之讴”。曰“采诗”,当然是为了“郊祀”时“夜诵”之用。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此事亦见《汉书·郊祀志上》。其时尚未由李延年等人造朝廷敬拜新歌,故采“民间祠”所用“鼓舞乐”的“歌谣”即“赵、代、秦、楚之讴”(变言则曰“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以为“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的“歌谣”。拙文《〈九歌〉夜祭考》尝考索赵、代、秦旧时祭歌的蛛丝马迹,又论所谓的“楚之讴”即指先楚夜祭乐歌《九歌》,拙著《汉楚辞学史》又引《史记·封禅书》记高祖置女巫有晋巫(包括有赵巫)、秦巫论此,本文下面对武帝夜祭始用《九歌》之事还有引述,可参。
所谓“夜诵”,是理解所用乐歌性子的关键。既然武帝是举行夜祭(前引《史记·乐书》云“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汉书·礼乐志》云“昏祠至明”),则所采乐歌本用于敬拜无疑。而颜师古注云:“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纳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落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但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武帝时并无“依古遒人徇路,采纳百姓讴谣”之事(说参后);纵然有,既然能“以知政教得失落”,又岂是“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师古之言,臆说而已,故与道理不合。但对“夜诵”之义,自颜氏而下,却历来误解纷纭,可略参范文澜师长西席《文心雕龙注·乐府第七》注释第一四条引钱大昭(谓“夜”通“掖”,“诵于宫掖之中”),周寿昌(谓“夜时寂静,循诵易娴”),以及范师长西席“夜诵即绎诵”,“抽绎以见意义,讽诵以协声律”之论,兹不细辩。又,张永鑫师长西席《汉乐府研究》引颜师古《汉书注》(见前引),何焯《义门读书记》(谓“先教之夜诵,以肄习学童”),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昭(见前引),周寿昌《思益堂日札》(见前引),范文澜师长西席《文心雕龙注》(见前引)等,云,“范说彷佛比较近于情理”。又解曰,“夜诵是指专门祀礼太一尊神的祭歌独奏者”。此解似比以前诸说都靠近“夜诵”原意,但仍有未安。由于据《汉书·礼乐志》,哀帝时罢乐府官,属于不可罢之列的有“夜诵员五人”,当指“夜诵”的乐工,说其“独奏”,于史无征;而如前所引,李延年等人造夜祭新歌后,“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这七十人当是祭歌的演唱者,而乐府“夜诵员”之设,又当在其后也。
其二,关于李延年等人造敬拜新歌。
《艺文志·序》未言李延年、司马相如等人造敬拜新歌之事,但《史记·乐书》和《汉书·礼乐志》对此言之甚明;而曰“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则是“采歌谣”而“夜诵”往后之事,《史记》《汉书》所记亦甚明。又曰“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是说李延年对《郊祀歌十九章》“次序其声”。故《史记·佞幸列传》云:“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司马贞《索隐》云:“初诗,即所新造乐章。”《汉书·佞幸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以《史》、《汉》对读,知司马贞的阐明是精确的。
又,检《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十九章》,第八章《天地》有云:“天地并况,惟予有慕。……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展诗应律鋗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长。声气远条凤鸟鴹,神夕奄虞盖孔享。”从“天地并况,惟予有慕”和“合好效欢虞泰一”诸句可知,此歌乃为祭“三一”(天、地、泰一)所奏。而据《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上》,祭“三一”在武帝元朔间,而且这往后再也没有合祭“三一”。此歌曰“《九歌》毕奏斐然殊”,解释武帝夜祭所始用的“楚之讴”,正是先楚夜祭乐歌《九歌》,而代、赵、秦之讴可类知。又,其曰“展诗应律”,乃直用《九歌·东君》“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文辞。复曰“造兹新音永久长”,即言造《天地》之夜祭新歌;而曰“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商”,正言《天地》乃经由“略论律吕”,故“合八音之调”也。
以上仅举《天地》,而全体《郊祀歌十九章》的情形则比较繁芜。简言之,《十九章》中,《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四章,为四季乐,且特殊题名“邹子乐”,盖以别于武帝君臣所造乐歌。《汉书·礼乐志》载文帝时始有《四季舞》,且明言“《四季舞》者,孝文所作”,武帝时亦用。《宋书·乐志一》亦言文帝“自造《四季舞》”。《青阳》四章当为四季舞之乐章,亦由李延年“次序其声”,武帝夜祭亦用(前引《史记·乐书》先言作《十九章》,后又言夜祭用春、夏、秋、冬歌,则单举此四章,可参),后亦得编入《十九章》之中(第三、四、五、六章)。另,据《汉书·武帝纪》,武帝所作《白麟》、《宝鼎》、《天马》、《芝房》、《西极天马》、《朱雁》等,乃颂祥瑞之歌,且作时不同,也由李延年“次序其声”,夜祭亦用,后来亦编入了《十九章》之中。且《十九章》中其它祭歌之创作韶光,亦有先后。纵然《礼乐志》所谓的“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也应理解为举其诗,而非举其人(参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语),由于司马相如(还有朱买臣)卒于武帝定郊祀之礼的元鼎四年之前。此事的较详细引证,参拙著《汉楚辞学史》第二章《武帝君臣与楚辞》,兹不赘述。
又,据《汉书·礼乐志》,武帝命李延年对敬拜乐歌的“次序其声”,“为新变声”,在当时即被认为“非雅声”,由于“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腔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应劭《风尚通义·声音》亦云:“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乐官多所增饰,然非雅正。”《宋书·乐志一》云:“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敬拜见事及其祥瑞而已。”《文心雕龙·乐府》亦云:“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系统编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此亦论及《十九章》之事,且言及时人对武帝郊祀礼乐不合典则的批评。但《史记·乐书》有云:对李延年“次序其声”的《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关照其意多尔雅之文”。可见这些郊祀乐歌虽然在系统编制上大概不合古制,但文辞合乎敬拜之用,是一种新的雅乐。班固《两都赋序》亦云“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因此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这里并无批评。不雅观上引《汉书》《宋书》之语,紧张是批评《十九章》中没有享祖考的内容;刘勰之语,则批评的是个中歌祥瑞之作。但无论如何,李延年对全体十九章夜祭新乐进行了“次序其声”,“略论音律,以合八音之调”的事情,则可知也。
二
由以上论述可知,汉武帝“立乐府而采”“代、赵、秦、楚之讴”和使李延年等人造为新歌,皆是为了敬拜之用。由此再不雅观《汉志·序》所接着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语,其为本言敬拜生理之义甚明。
其一,关于“感于哀乐”。
哀乐之心,人之脾气,可泛言,可特称,而在敬拜时,固能表达对神祇乐迎哀送之意也。
《礼记·乐记》有云:“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郑玄注曰:“大事谓去世丧也。”又《礼记·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玄注曰:“迎来而乐,乐亲之将来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祭义》又曰:“祭之日,乐与哀半。享之必乐,已至必哀。”孔颖达疏曰:“孝子想神之歆享,故必乐;又想及享已至之后必分离,故必哀也。”以此释吾先民之郊庙敬拜(不但是丧祭和祭祖,也包括敬拜天地神祇)所怀乐迎哀送之生理,该当说最能探得其本真之意。今检诸史乘所载,如《汉书·艺文志》在《郊祀歌》后又著录“《送迎灵颂歌诗》三篇”,直以“送迎”标祭神歌诗之目,正是继续的《郊祀歌》传统(参后所引述)。又,《晋书·乐志上》记傅玄所作,就有《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祠庙迎送神歌》。又《宋书·乐志一》述刘宏议郊庙之礼,论迎送神之义甚明,曰:“立庙居灵,四季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恒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汉书·安世房中歌》曰:‘神来宴娱。’《诗》云:‘三后在天。’又《诗》云:‘神保遹归。’注云:‘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众臣则同议当奏迎神、送神诸歌。今检《宋书·乐志二》,即有颜延之所造的《天地郊迎送神歌》,且言所作迎神歌诗是“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汉郊祀送神,亦三言”。至于古代郊祀所奏迎送神歌,仅唐五代以前就数量极大,除傅玄、颜延之,如谢庄、谢超宗、谢朓、江淹、沈约、庾信、张说、褚亮、包佶、武后、于邵等,以及其他未署名者,皆有创制。其事诸史有载,又可略参郭茂倩编《乐府诗集·郊庙歌辞》所录及诸序所引,兹不繁引。
实在,武帝敬拜所始用的“楚之讴”《九歌》,就表达了对神祇的乐迎哀送之情,汉《郊祀歌十九章》亦如此。刘熙载《艺概·赋概》有云:“《楚辞·九歌》,两言以蔽之,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此言至确。验之《九歌》,其事神敬神之意确实是“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读《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小《司命》、《东君》、《河伯》等,及至送神曲《礼魂》皆然。如《九歌》首篇《东皇太一》始曰:“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末曰:“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云中君》开篇言迎云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而云神降临后拜别,故曰:“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纵然以借写人神恋爱,言不忍与对方相离,亦是表达敬礼神灵、“哀以送往”之情。二《湘》、二《司命》、《河伯》、《山鬼》诸篇即如此,不引。至于汉《郊祀歌十九章》,如《练时日》(第一章)极写迎神之乐,曰:“灵之来,神哉沛。……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师古注‘虞,乐也。亿,安也’)。牲茧栗,粢盛喷鼻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青黄,遍不雅观此,眺瑶堂。……侠嘉夜,茝兰芳,澹容与,献嘉觞。”又如《帝临》(第二章)言“帝临中坛,四方承宇”亦如此。他如《天地》(第八章)言“合好效欢虞泰一”,“神夕奄虞盖孔享”(前已引)。《华烨烨》(第十五章)言“神之徕,泛翊翊,甘露降,庆云集”。“神安坐,翔吉时,共翊翊,合所思”。《郊祀歌》之末《赤蛟》(第十九章)述神之去而欲留其不离,以永赐福祉的“哀以送往”之情有云:“赤蛟绥,黄华盖,露夜零,昼晻濭。百君礼,六龙位,勺椒浆,灵已醉。灵既享,锡吉祥,芒芒极,降嘉觞。灵殷殷,烂扬光,延寿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泽汪濊,辑万国。灵禗禗(孟康注‘不安欲去也’),象舆轙,票然逝,旗逶蛇。礼乐成,灵将归,托玄德,长无衰。”此歌末四句,与《九歌》之送神曲《礼魂》所谓“盛礼兮会鼓……长无绝兮终古”义同。
通过以上论述,“感于哀乐”之“哀乐”乃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的敬拜之意已明。当然,古文献言乐之“哀乐”,临文属辞,我们亦应随文释义。他书且不引,仅以《汉书》为例。如《礼乐志》云:“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赋其性而不能节也,贤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以是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此总言人情生理和礼乐之用,乃是合论礼乐的敬拜浸染和教养浸染(参后所论)。又曰:“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君子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落。”亦当如是不雅观。又如《艺文志·六艺·诗·序》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按《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则本谓祭乐之用。《汉志》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虽似是泛言,然必含敬拜与教养生理。总之,在详细的叙事语境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乃言敬拜用乐,以表达对神祇的“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之意,则无疑也。
其二,关于“缘事而发”。
所谓“缘事而发”,即前引《史记·乐书》所说的“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汉书·礼乐志》则言“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史迁言“祠”,班氏言“用事”,“用事”即“祠”,同谓举行敬拜之礼,而非泛言他事。类似的例子如《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十一月诏曰:“亲省边垂,用事所极,看见泰一,修天文禅”如斯。又如《史记·封禅书》记武帝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如斯,《史记·孝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上》同,而“用事泰山”即《封禅书》和《郊祀志上》所同言的“封禅祠”泰山,这与前引“祠太一甘泉”、“用事甘泉圜丘”行文办法完备相同。又如《史记·孝武本纪》言“上遂东巡海上,见礼祠八神”,《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上》同,而《汉书·武帝纪》载武帝诏书言此事则曰“用事八神”,故《孝武本纪》“见礼祠八神”句下司马贞《索隐》云“用事八神”,当是直用武帝诏书语作注,当矣。总之,《史》、《汉》对读,此义昌明(类似例子还有“用事西岳”、“用事介山”等,不复更引)。又《春秋繁露·郊祭》云:“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此言“事天地之礼”,亦言举行郊祭天地之礼。故《说文解字·示部》云:“礼,履也,以是事神致福也。”“事神”即祭神。又《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觋,能斋肃事神明也。”“事无形”、“事神明”亦皆言祭神。
又有可论者。“事”,泛言乃指职守,此即《说文解字·史部》所云:“事,职也。”事有职份,因事而异。如前引《礼记·乐记》言“先王有大事”,郑玄注曰“大事谓去世丧也”。又《礼记·王制》言“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郑玄注曰“事谓征伐”;《王制》又言“兴事任力”,郑玄注则曰“事谓筑邑庐宿市也”。郑君随文释义,故意无窒碍。至于“事”言敬拜之事,文籍更多有其例。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述大宗伯之职云,“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郑玄注曰:“事谓祀之、祭之、享之。”《周礼·天官·宫正》言“凡邦之事跸”,郑玄注曰:“事,祭事也。”又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八年》言“天子有事于泰山”,何休注曰:“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礼也。”检《左传》、《穀梁传》皆记是年有祭泰山之事,知何氏表明不误。总之,就事论事,《汉志》所谓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事”,确实本指敬拜之“事”,而非泛言他事,更非“劳者歌其事”的“事”明矣。
又,“发”,发声歌唱之谓也,即“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故书言笙歌之“发”,例至夥。如:《荀子·乐论》有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礼记·乐记》亦言“乐必发于声音”,《史记·乐书》亦言“乐必发诸声音”。又,《诗大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至于《汉书》,《礼乐志》言礼乐之用,曰“发之于诗歌咏言”;《艺文志·六艺·诗·序》录刘歆言又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又,《楚辞·招魂》云:“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此即言“发”《涉江》、《采菱》、《扬荷》等新歌,故王泗原来生《楚辞校释》解曰:“三名皆发的受语,以诗句须平均,发字在第二句。”《淮南子·人间》亦曰:“歌《采菱》,发《阳阿》。”汤炳正师长西席等《楚辞今注》引此以注《招魂》句,并云:“‘歌’与‘发’对文见义,谓发声歌唱。”又如,《文选·啸赋》李善注引刘歆《七略》云:“汉兴,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动梁上尘。”“发声”即言“发歌”。
综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确实本言武帝敬拜用乐,以表达对神祇的“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之情。而其它各类阐明,皆未探得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又造敬拜新歌礼敬神祇之本意也。
三
还应结合《汉志》所谓“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之语,以及对“歌诗之属”的著录和刘歆的礼乐不雅观等问题进行谈论剖析,则“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本意更明。
依古贤之见,礼乐之用,有两种紧张功能,一曰敬拜,二曰教养。对此,古文献言之多多,《汉书》于此亦有明确的论述,如前引《礼乐志》所谓“故象天地而制乐,以是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礼乐志》又云:“王者未作乐之时,因先王之乐以教养百姓,说乐其俗,然后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因此荐之郊庙则鬼神享,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故乐者,贤人之以是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而《艺文志·六艺·乐·序》录刘歆《七略》语,于此义尤为显著,其文曰:“《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长于礼;移风易俗,莫长于乐。’二者相与并行。”不雅观刘歆语,正是论述的礼乐的敬拜和教养两种功能,故先引《易·豫卦·象辞》,以明乐之敬拜功能。今检《易》辞,同于班氏《礼乐志》所引,孔疏所谓“用此殷盛之乐,荐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至于黄帝以下至三代乐,兹不繁引可也。刘氏又引《孝经》中孔子语,今见《广要道章》,然先言乐,后言礼。“二者相与并行”,则是说礼乐并行合用。《汉书·礼乐志》所谓“二者并行,合为一体”,乃直用刘歆语。
尤其要指出的是,校阅阅兵载籍,《汉书·艺文志》所谓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本为敬拜所用,由于其时并未仿古制而设置采人间风谣之官,故《汉志》接着说的“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本指为敬拜而“发”歌,非关人间风谣。但是武帝之后,乐府所采又有人间乐,故《汉志》又用“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之语,言礼乐的教养之用。此事之论证,一是涉及武帝以至西汉末礼乐制度的一些问题,二是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歌诗之属”需进行必要的解析,三是需稽核刘歆的礼乐文化不雅观。
请略论之。
其一,关于武帝时并无采人间风谣之事。
此事于史有征。《汉书·食货志上》言古时“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如斯,并未言及武帝时。《艺文志·六艺·诗·序》录刘歆语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是不雅观风尚、知得失落、自考正也”,也是仅言古事。又,《宋书·乐志一》云:“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推敲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势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敬拜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此则明言武帝时并无采人间讽谣之事。而检《史记》、《汉书》等有关记载,确实未见武帝及武帝前至汉初设采诗官之事。孙尚勇师长西席《乐府通论》引沈约《宋书·乐志一》“秦、汉阙采诗之官”一语,又引杜佑《通典·乐序》、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和《与元九书》、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指出:他们“都否定了汉代存在采诗制度”。
实在,武帝之后,尤其是元、成以至哀、平,对武帝敬拜制度不合古礼的批评不绝于耳,亦有不少官吏提出或谈论应规复古时采诗之制。如《汉书·郊祀志下》云:“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敬拜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成帝时,匡衡、张谭亦批评武帝郊祭“事与古制殊”。等等。与此相应,倡言用雅远郑之议兴起,如《汉书·礼乐志》记成帝时大夫博士平当赞河间献王“修兴雅乐以助化”。哀帝时更是下诏“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古代采诗之制的实施制定条约论渐多。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变动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大家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蔼亲爱销除怨咎之路”。《汉书·谷永传》载永于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对曰,“愿陛下……立春,遣青鸟使循行风尚,宣告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石”如斯。又,《刘歆与扬雄书》言“诏问三代周秦轩车青鸟使遒人青鸟使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据汤炳正师长西席《措辞之起源·汉代措辞笔墨学家扬雄年谱》,刘歆此信写于王莽天凤四年(17年)。
其二,关于《汉志》“歌诗之属”。
与以上所论干系,班固据刘歆《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诗赋》所著录的“歌诗之属”,当分别言之。
《汉志》著录歌诗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始“《高祖歌诗》二篇”(第一),及“《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十四篇”(第四)、“《出行巡狩及游歌诗》十篇”(第五)、“《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第六)、“《李夫人及幸朱紫歌诗》三篇”(第七)、“《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童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诗》四篇”(第八),各家或有主名,或以类编,皆非谣歌。第五家之作,也不用于祭礼,即《汉书·礼乐志》录《郊祀歌十九章》而后曰:“别的巡狩福应之事,不序郊庙,故弗论。”而第四家所谓“汉兴以来”,与其他诸家一样,断于武帝期间可知也。至于“《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第二)、“《宗庙歌诗》五篇”(第三),当即《郊祀歌十九章》。而从“《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第九)至“《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第十)、“《邯郸河间歌诗》四篇”(十一)、“《齐郑歌诗》四篇”(十二)、“《淮南歌诗》四篇”(十三),当为各地歌诗,惟韶光无法考定。依本文前论,当在武帝之后。又,“《左冯翊秦歌诗》三篇”(十四)、“《京兆尹秦歌诗》五篇”(十五)、“《河东蒲反歌诗》一篇”(十六)、“《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十七)、“《杂各有主名歌诗》十篇”(十八)、“《杂歌诗》九篇”(十九)、“《雒阳歌诗》四篇”(二十),当为各有主名、无主名歌诗的类编。据《艺文志·诸子·名家》著录:“《黄公》四篇。”旧注云:“名疵,为秦博士,作歌诗,在秦时歌诗中。”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认为,黄疵歌诗“在左冯翊、京兆尹两家八篇中也”。第十七家,是宫门倡俳车忠等人的歌诗。第十八家为“各有主名”,则第十九家为各无主名。别的无考。又,“《河南周歌诗》七篇”(二十一)、“《河南周歌声弯曲》七篇”(二十二)、“《周谣歌诗》七十五篇”(二十三)、“《周谣歌诗声弯曲》七十五篇”(二十四),姚振宗以为:《河南周歌诗》、《周谣歌诗》“两家皆有声律弯曲”,“《河南周歌诗》指东周人而言也,《周谣歌诗》则合东西两周,故篇数多于东周十倍有馀”。又,“《诸神歌诗》三篇”(二十五)、“《送迎灵颂歌诗》三篇”(二十六),亦为敬拜歌诗,效仿《郊祀歌》,又列于后者,当为晚出。“《周歌诗》二篇”(二十七)、“《南郡歌诗》五篇”(二十八),盖最为晚出。
以上可考无考者,总凡两类,一类可归之于敬拜乐歌,一类则人间歌诗。又据《汉书·礼乐志》,迄哀帝时,在乐府署的乐工达八百二十九人,亦有两类分工,如:不在罢之列的“郊祭乐职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郊祭员十三人”,“夜诵员五人”等;部分罢的“竽工员”、“《安世乐》鼓员”等;全罢的“沛吹鼓员”、“东海鼓员”、“蔡讴员”等。但无论如何,并不能确定武帝时设置了采诗之官,并采人间歌诗用于祭礼;而所著录的人间乐,在武帝之前后,但都不能确定为乐府设置了采诗之官进行采录。
其三,关于刘歆的礼乐不雅观。
刘歆言敬拜用乐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后,为何又接语曰“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这不但由于《诗赋》“歌诗之属”中著录了大量的各地歌诗,也非常可能与刘歆(也包括乃父刘向)对武帝敬拜的评价和他们的诗赋不雅观有很大的关系。
据《汉书·郊祀志下》,成帝时,针对武、宣之后对武帝敬拜的多种非媾和变动,刘向对成帝问有云:“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
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由此可以看出,刘向对武帝敬拜之制,乃是正面论说肯定,并不轻率批评。值得把稳的是,据《汉书·韦玄成传》,哀帝时刘歆曾与太卜王舜一起议不宜毁武帝庙,整篇议论实在便是刘向对文的重复、翻版和发挥,有些话还直抄刘向语,如曰“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如斯。又,刘歆撰《七略》,肯定“雅乐声律”,故《汉书·艺文志·六艺·乐·序》特意述武帝时河间献王作《乐记》和乃父刘向校《乐记》之事。这也是正面立论。至于《诗赋·序》,写得更是颇有深意。其对荀卿、屈原赋,肯定他们“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而对宋玉以下及于扬雄,则批评他们“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这因此“诗教”为标准来论说先秦至西汉朝辞赋的是非得失落,借用其《诸子·序》之语,这是为了“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也”。但对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诸事,则只是从正面论说礼乐的敬拜、教养两种功能,却并未从“雅乐声律”的角度进行论说,更没有轻率批评,显然,这与乃父的不雅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又,本文前面尝引司马迁说《郊祀歌十九章》“多尔雅之文”,则刘氏父子的不雅观点又与史迁相通矣。尤其值得把稳的是,据《汉书·王莽传上》,平帝元始五年(5年),王莽上书有“伏念圣德纯茂,承天当古,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等语,“制礼以治民,作乐以移风”正是用的《孝经·广要道》的话(见前引),刘歆《七略》论乐之用,亦用,这绝非有时。至于刘歆言祭乐之用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复又言“亦可以不雅观风尚,知薄厚”,当是兼顾了“歌诗之属”中不但著录有祭乐,也有大量的人间乐歌,且与《六艺·序》所谓“乐以和神”以及《六艺·诗·序》言古者采诗“以是不雅观风尚、知得失落、自考正”(前已引)相应。古人行文述事,参互错综每每如此,读者自当会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