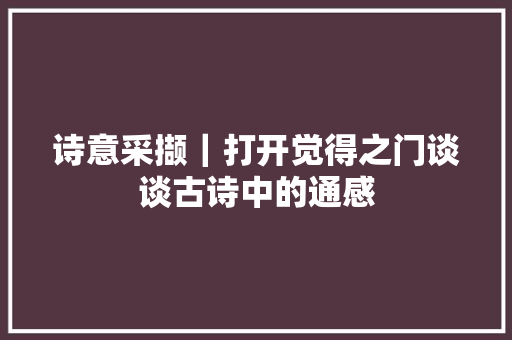听觉形象的通感。墨客进行艺术创造紧张靠视觉、听觉这两种审美感官,但这两种感官每每不足用,因而墨客们常常借助于别的感官进行艺术概括。如左辅《浪淘沙》中所写的“水软橹声柔,草绿芳洲,碧桃几处隐红楼”便是听觉与触觉的联姻。声音本来是无所谓硬度的,可作者居然说“橹声柔”,这是由于水不急,呈“软”态。如果是水浪翻滚,“卷起千堆雪”,那“橹声”就绝不可能“柔”了。李世熊《剑浦陆发次林守一》中的“月凉梦破鸡声白,枫霁烟醒鸟话红”则是听觉与视觉的结合。“鸡声白”是用视觉写听觉。这样写之以是能成立,是由于鸡啼声惊破黑夜,带明天将来间。“鸟话”之以是呈“红”色,是由于鸟生活在赤色的枫树林中。陆机《拟西北有高楼》:“佳人操琴瑟,纤手清且闲。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在这首诗中,声若兰花并带喷鼻香味,这是听觉与嗅觉的相通,是将声音比作兰花的一定结果。
视觉形象的通感。墨客们在“感物”时每每“联类无穷”,通过艺术想象和夸年夜将五官沟通,因而在视觉形象方面也就涌现了许多与其他感官遥相呼应的情形。大家所熟知的宋祁《玉楼春》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兼有视、听二觉的功能,用这个字既写出了杏之红,又描出了花之繁,亦红亦繁,如喧如闹,把事物的无声之态夸年夜为好似有声响,表示人们在视觉里仿佛得到春意繁盛热闹繁荣的听觉感想熏染,在听觉中又好似陈设出五颜六色的视觉风光,难怪王国维对此高度讴歌,认为这样写不但描绘出繁花似锦的光景,并富有鸟鹊满枝的曲意,由此境界全出。又如李白《菩萨蛮》中有“寒山一带伤心碧”之句。山之以是能给人寒冷的觉得,是通过碧色感想熏染到的,这与我们平时说的“绿得发冷”是一样的道理。而刘沧《秋夕山斋即事》中的“满山寒叶雨声来”,给叶以温度感,亦是视觉通触觉的例子。
嗅觉形象的通感。诗歌创作中的通感是墨客借助遐想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并不即是大自然的各种颜色、芳香、音响在客不雅观现实中真的可以相互呼应,但这种思维上的幻觉可以使作品取得奇警的效果,使读者得到新鲜奇特的感想熏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喷鼻香冷蝶难来”,这是黄巢《题菊花》中的诗句。他这里写喷鼻香味有温度感“冷”,是由于西风劲吹、凉气袭人的缘故。这是嗅觉通于触觉的例子。“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喷鼻香咚咚”,这是李贺在《神弦》中的诗句。他写喷鼻香气会发出叮咚的声响,乃是炭火燃烧时发生发火声响的移借。这是嗅觉通于听觉的例子。又如李白的诗句“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东风喷鼻香”,在这里墨客把“雪花”与“东风”联系在一块:他眼里的雪花,已像东风中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了。按照他的逻辑,花既然是喷鼻香的,雪花也是“花”的一种,自然也会有喷鼻香味。这是嗅觉与视觉的相通。
须要解释的是,通感常常通过比喻、拟人、夸年夜的手腕表现出来,但这些手腕本身不一定是通感。如大家所熟习的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关弦乐的描写“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密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就不是有人所讲的通感手腕的利用,这只是把各种事物所发出的声音——雨声、密语声、珠落玉盘声、间关鸟声、幽咽水声——来比方琵琶声,并不是那种觉得的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