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梅知道后,选择自尽后给我捐献眼角膜。
她留下一封遗书:
“这辈子不能和你在一起,就让晚棠代替我,陪你看这个天下。”
所有人都说是我害去世了小青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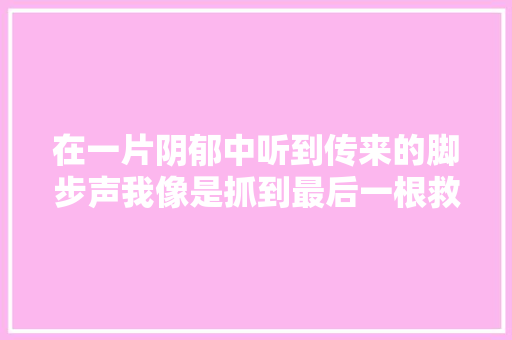
老公更是像疯了一样,把我关进了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不给吃喝。
声音比地下室的铁门更加冰凉:“你怎么配用她的眼睛看我!
如果没有你,她根本不会去世!
”
“既然她没办法再看到嫡的太阳,那你也永久待在阴郁里吧!
”
后来,小青梅回来了。
他疯了一样来找我,却不知道。
我早就去世在那个阴冷的地下室了。
不知道被关了多久,周围安静的只能听见自己无力的心跳和喘息声。
门外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努力转头望去。
宋知砚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你现在所体会的痛楚,根本比不上清函自尽时的绝望的十分之一!
”
我拖着麻木的双腿,爬到门边,伸开干涸撕裂的双唇。
有气无力的吐出两个字:“求你……”
放我出去。
我要疯了。
地下室小的不超过三平米,连身体都不能完备伸展开。
只能小范围的变换姿势,以减轻手脚的酸痛和麻木。
永劫光的五感尽失落,让我险些觉得不到我还是个活着的人。
起初,是饥饿脱力。
然后,便是恶心反胃,反复呕吐。
可空空的胃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吐的出来,只有酸苦的胃液和胆汁。
后来,连拉撒也在这小小的黑屋里。
最严重的时候,乃至产生癫狂和幻觉。
在一片阴郁中,听到传来的脚步声,我像是抓到末了一根救命稻草。
冲着门外的宋知砚求饶:“我快……去世……”
回应我的,是淡淡的嗤笑:“去世了最好,我只恨你为什么不早点去世。”
“还去祸害别人!
”
阴郁悄无声息的把我彻底吞噬。
我困难的想开口,却无法再操控这具身体。
沉默激怒了宋知砚:“看来这几天的禁闭并没有让你反省到自己的错,你给我连续呆在里面赎罪!
”
“别以为用去世能威胁我,人不吃不喝最少七天才会去世!
现在才第四天!
”
原来我已经在地下室关了四天了。
可是,宋知砚,你不知道,在五感皆失落,阴郁密闭的环境下,人乃至很难活过三天。
身体忽然轻了起来。
阴暗的灯光下,我忽然看到了宋知砚愤怒的脸。
我被放出来了么?
我抬起手,却触摸不到任何东西。
低头看了看自己透明的身体。
原来,我去世了。
宋知砚,如果你创造,沈清函根本不是我害去世的。
会后悔这样对我吗?
我和宋知砚是在爬雪山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在同一个旅行团,二十年来没看上过任何一个男人的我,却唯独对他一见钟情。
都喜好户外攀岩冒险,又同是年轻人,旅行团的成员很快打成一片。
一次出行遇见狂风雪,我们两个不幸和大部队走散,被困在白茫茫的雪山中。
他的护目镜坏了,眼睛被寒风吹的堕泪不止。
在他濒近奔溃的时候,是我摘下护目镜给他,又把他从雪山带了出来。
也是在那时,我患了雪盲症,眼角膜也受伤严重。
时常堕泪疼痛,后来连看东西也模糊不清。
宋母知道之后,强行逼他娶了我。
不只是由于宋家父母认可我的知书达理。
更是由于和我们两家门当户对,两家联姻,对他们的买卖非常有帮助。
我当时还傻傻地以为他是真的爱我,才会乐意向我求婚。
直到婚礼现场,沈清函涌现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宋知砚心里装着一个从小一起终年夜的小青梅。
新婚夜,他一夜未归。
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向我道歉:“对不起,清函心脏不好,昨天看我们结婚受了刺激,犯病了,我不能不管她。”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去世了。
可我不能任性离婚,这场婚姻,除了爱情,还有商业联姻。
我不能把连个家族的企业,都毁了。
这些年,我吵过,闹过,终极都淹没在他的冷暴力和沈清函的电话里。
直到前段韶光,我的眼睛险些完备看不清东西了。
年夜夫说,必须立时做角膜移植手术,他会帮我留神最近有没有人乐意主动捐献。
在医院的病床上,宋知砚溘然一巴掌扇到我的脸上,大声质问:“赵晚棠,是不是你逼迫清函给你捐献眼角膜?”
他按下手机,那边传来的,是沈清函临去世前的留言。
一向的温顺哀怨。
“知砚,在你听到这条的时候,我已经去世了。”
“这些年,我一贯活在痛楚和自责当中,我知道你爱我,可我不愿毁坏你和晚棠姐的婚姻,做一个人人谩骂的小三。”
“可我也无法眼睁睁的看着你跟别人在一起。”
“我知道晚棠姐眼睛不好,我已经签了赞许书,去世后志愿把角膜捐献给她。”
“这辈子不能和你在一起,就让晚棠代替我,陪你看这个天下吧。”
“我已经请了人帮我收尸。别找我,我想安静的离开。”
听完我愣住了。
他看到我手上扎着的针管,就天经地义的认为,我刚做完手术。
想要开口辩白,宋知砚却根本不给我机会。
他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我的话呜呜咽咽的堵在喉咙里,然后晕了过去。
醒来后,我已经被关在了别墅的地下室里。
耳边传来的,是铁门落锁的声音,以及他的那句:
“你这样毒辣的女人,不配用清函的眼睛。”
“你就好好待在阴郁中,后悔吧!
”
我终于再次看清了这个天下。
灵魂飘飘荡荡,跟在宋知砚的身边。
他在老屋子里喝的烂醉,那是和沈清函一起终年夜的大院。
无数的照片封在老旧的抽屉中。
他拿出来,一张一张的翻看。
我在一旁,被迫见证了他们的童年。
“清函,这是你三岁的时候,追着我要糖吃,那时候我还不懂让着妹妹,把你气哭了。”
“七岁的时候,你第一天上小学,姨妈让我牵着你,那时候我已经上二年级了。”
“初中你被同学陵暴,还是我帮你出头的呢。结果回到家里,我们两个都被父母大骂了一顿。”
“……”
宋知砚又哭又笑,从幼年细数到高中。
相册到毕业那天戛然而止。
他一毕业,就被宋家父母送出国了。
为了断了他和沈清函的联系。
由于两家家境相差太多,多年来,宋氏集团早就发展成上市公司,而沈家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后来两人横跨大洋,只能通过手机联系。
宋知砚的手机壁纸上,沈清函笑的残酷而清纯。
“清函,你怎么这么傻,我爱的只有你一个,赵晚棠怎么能代替你呢?”
“留下我独清闲这个天下上,让我怎么办。”
“是不是赵家用权势威胁你,才让你迫不得已签了捐献书?”
“你放心,我已经惩罚她了!
欠你的,我一定会让她还回来!
”
他翻看着这些年,他和沈清函的谈天记录。
沈清函是置顶。
而我被设了免打扰。
我不是去世了吗?为什么看到这些,心还是会痛呢。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他给助理打电话:“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给我找到清函!
”
“活要见人,去世要见尸。”
那边助理答应后,又小心翼翼的问:“那赵总……”
宋知砚冷笑了一声:“怎么,你是赵晚棠的助理还是我的助理?还敢给她说话了是吧!
”
“总是关在地下室,我怕出什么意外。”助理有些胆小。
“再敢让我听见你提她一句,立时把你开除!
”
宋知砚声音陡然提高,吓得助理一个抖动,立时应声:“是,是,沈小姐的事情,我立时去办。”
电话割断。
不到两分钟,手机又重新响起。
宋知砚火气蹭的窜起来,接起电话大吼:“有完没完!
能干干,不能干趁早滚蛋!
”
那边沉默了一瞬。
“宋师长西席,你是赵小姐的丈夫吗?”
听见是陌生的声音,宋知砚轻微复苏了一点。
他缓下声音,但由于听到了我的名字的缘故原由,还是十分不耐烦:“怎么了?赵晚棠那个女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电话那头传来哗啦啦翻纸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声:
“宋师长西席你好,我是A城私人医院的妇产科年夜夫。”
“赵小姐五日前在我们医院做了体检,胎儿情形不太乐不雅观。”
“我当时叮嘱她,每隔三日要来医院进行一次保胎。但是四天前,她第一次保胎后,就没有再来过医院了。”
“我联系不上她,紧急联系人那栏,填的是你的电话。”
“你们家属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如果不按时保胎,是极有可能小产的……”
“啪。”
手机从宋知砚的手中掉落,砸在地上。
碎裂的屏幕,还闪烁着那串陌生的电话号码。
“宋师长西席,宋师长西席?”
听不到回应,那边反复的叫着。
宋知砚回过神来,眼中是冰冷的怒意:“赵晚棠,你真是长本事了,收买医院的人一起骗我?”
“别以为用有身的情由就能逃脱惩罚,我可没那么随意马虎上当。”
他掐断电话,转头又给助理打了过去。
“我改变主张了,之前说让你给赵晚棠一天送一次饭,从现在开始,都不用送了。”
“可是本日送过去的饭,赵总根本没吃……”
“没吃?”宋知砚冷笑,“那就让她饿去世!
”
我冷眼看着宋知砚像小丑一样,一边对着沈清函深情,又一边对我发着脾气。
想起我未出世的孩子,我心中的恨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她才两个月,还没完备长出样子容貌。
乃至,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就这样被她的亲生父亲,亲手扼杀。
我根本没做过什么眼角膜手术。
那天宋知砚到医院质问的时候,我才做完体检,年夜夫见告我,我有身了。
就在我陷入巨大的惊喜时,年夜夫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赵小姐,由于你身体虚弱,并且长期的感情郁结,导致孩子长的并不是很强壮。”
“每个三日,都要来医院吊水保胎,最少坚持两个月。”
“等胎儿轻微终年夜一点,营养也补充上来了,就安全了。”
她给我吊上水,嘱咐我一定要平心静气,按时用饭,不可大喜大悲。
就在我抚摸着肚子,愉快的叫宝宝时,宋知砚闯了进来。
在听到沈清函的遗书时,我十分震荡。
可大怒之下的宋知砚,并没有讯问过我,也没有问过年夜夫。
更没有仔细看过我无法聚焦且没有任何手术痕迹的双眼。
就这样勒住我的脖子,把我揪入了地下室锁起来。
对付沈清函的话,他总是无条件的相信。
就像过去的几年一样。
一开始,我以为沈清函真的是恬淡而不食人间烟火的白月光。
直到那日,在我家用饭,她从菜里夹出一只虾。
没多久,便浑身红痒,呼吸困难,叫了120。
宋知砚见状对我怒骂:“你这个毒辣的女人!
我反复叮嘱过你,清函对海鲜过敏,你还偷偷加在菜里,是不是想害去世她?”
那是他第一次打我巴掌。
可是那天我根本没买虾,谁会在西红柿炒鸡蛋里放大虾?
我捂着脸,不可置信,一抬眼,是沈清函得逞而歧视的笑。
彷佛在说:你输了,你永久也比不过我。
她柔弱的倒在宋知砚的怀里,一张嘴便是娇滴滴:“知砚,不怪晚棠姐,大概她只是一时忙忘却了。”
“做这么大一桌子菜也不随意马虎,我没事的,只是有些难熬痛苦。”
她抚着胸口,彷佛在容忍极大的痛楚:“对女孩子可要温顺一点,我一贯教你的,你全忘了?”
“咳咳……”
宋知砚心疼的把她抱起来放在沙发上,匆忙找手机去打120。
还不忘骂我。
“赵晚棠这样的毒辣的女人也算女孩子?清函,你便是太善良,不是每个女孩子都像你一样纯挚干净。”
他嫌恶的看了我一眼:“平时你吵吵闹闹,我都以为你是被家里惯得大小姐脾气,我不跟你计较。可我本日才算知道,你原来手段这么下作,这么恶心!
”
我低头,看着被划破的手指,从层层纱布中渗出的血迹。
以往家里有保姆,我险些从不做饭。
可是赵晚棠在宋知砚面前无意提及,想吃我的烧的菜。
宋知砚就忙不迭的给我打电话,命令我晚上做好饭,等他们来吃。
又千打发万叮嘱,沈清函的喜好以及过敏原。
我一边应着,鼻头却微微酸涩。
结婚两年,在一起四年,宋知砚从来不记得,我喜好吃什么,讨厌什么。
乃至不知道,我根本不会做饭。
以是我切得手了。
那伤口深可见骨,眼泪掉进去,生疼。
我不知道自己哭,是手疼,还是心里疼。
我被他们丢在家里,宋知砚随着沈清函一起上了救护车。
那顿我用尽心血做的饭,乃至都还没吃上一口。
我默默的一盘又一盘倒进垃圾桶里。
连同对宋知砚的爱,也倒了进去。
就在我沉浸在自己的天下中时,一阵铃声又把我从回顾中拉了出来。
宋知砚不耐烦的按下接听键,却在听到那边的话时,猛地僵住,转而狂喜。
“什么?是真的吗?!
”
“是真的,宋总,我们找到沈小姐了。”
原来沈清函还在这座城市。
听说她手机关机,一贯流浪在街头。
宋知砚赶过去的时候,她正被保镖围着保护起来。
一看到宋知砚下车,就飞奔过来,扑到他怀里。
委曲大哭:“知砚——”
宋知砚激动的抱住她,像是抱着失落而复得的珍宝。
他抖动着问:“清函,你没事吧?”
“不许再离开我了,你知不知道,我都快被吓去世了!
”
他语气微微严厉,终极还是不忍心斥责她。
沈清函抽抽咽噎道:“对不起,知砚。”
“我那天买了一大堆安眠药,正准备吃下去。可是我想起你,我就舍不得。”
“我舍不得离开你,也舍不得再也见不到你。”
她仰起脸,眼睛红的像兔子,清瘦的脸上布满斑驳的泪痕。
“我太爱你了,知砚,我不放心把你交到别的女人手上,体谅我这点小小的私心。”
宋知砚心疼地把她抱起来,安置在车上。
听她诉说这几天流落在外的苦楚。
车子一启动,我就像是被无形的线拽着,强行绑在宋知砚身边。
我晃着身体,飘然跟上。
看着面前一副郎情妾意的景象,我忽然以为眼睛看不清楚也挺好的。
最少不会被这么膈应的画面恶心到。
回到别墅。
这是幢我从未见过的新居。
大概这便是宋知砚和沈清函的爱巢吧。
两年来没有回家的那些夜晚,大概都在这里和她缠绵着。
宋知砚忙前忙后,一边嘱咐着保姆烧菜,一边让佣人去备好沐浴水。
自己则亲自把沈清函抱到床上,盖好被子。
声音绸缪:“入秋了,天冷,你这几天冻坏了吧。”
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温顺。
我扭头望着表面,吹落的叶,和萧索的风。
冷吗?
纵然是五年前,拖着半去世不活的宋知砚,在雪窖冰天里走了五六个小时。
也不及地下室的可怖和阴冷。
喂沈清函吃过饭后,他开始给我打电话。
那头一贯是嘟嘟嘟的无法接通。
低声骂了一句,他才想起来,我被关在地下室,根本没带手机。
看着还躲在被窝里颤动的沈清函,他彻底没了耐心。
给助理打过去电话。
“把赵晚棠给我从地下室弄出来!
”
“清函回来了,还好她没事。让赵晚棠滚过来跪下给清函道歉,她威胁清函的事,我可以考虑体谅她!
”
助理罕见的没有立时答话。
沉默了少焉,才抖动着声音道:“宋总,赵总她,彷佛去世了……”
宋知砚带着沈清函急速赶到了我被关的那所别墅。
他进门就给了助理两个耳光。
他核阅了一圈低头丧脑的保姆和佣人,冷笑起来:“你们是宋家的人还是赵家的人?”
“和赵晚棠联合起来骗我是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你们卷铺盖滚蛋!
赵晚棠是什么东西,也敢违逆我的意思!
”
“关了几天就要去世要活的,大小姐便是娇气!
”
他随手指了几个人:“你,你,还有你,立时去地下室,把她给我拖出来!
”
被点中的几个人当心翼翼,对视了一眼,麻溜的去地下室找我了。
没一会,就划过几道凄厉的尖叫声。
在楼上的几个人听到动静,急忙赶了过来。
“嚎什么?!
一惊一乍!
”
他护着沈清函,站在地下室门口。
一股难闻的屎尿味顺着门缝飘出来。
一旁的佣人神色苍白,指着半开的铁门,几欲晕厥:“里面……赵总……尸、尸体。”
他不耐烦的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