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人生的多数韶光都在游历中度过,他的身上,有剑、有道、有诗。他怀揣着凌云之志,仗剑天涯,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他曾入仕出仕,在官场的风云变幻中历经沉浮,然而无论遭遇何种境遇,始终保持着一片小儿百姓之心。他不被世俗的功名利禄所蒙蔽,坚守着内心的纯粹与高洁。
他的诗歌都是抒怀诗,作为伟大的浪漫主义墨客,他和屈原一样,每每不是直接地抒写自己的感情,而是常常采取比兴、象征的手腕,借助于神仙、梦境、风雨、雷电、古人、美女等形象来寄寓自己的感想熏染,犹如残酷星辰,或情绪朴拙,或豪放洒脱,或婉约细腻,皆能触动人心,照亮了历史的长河。
千百年来,岁月流转,风云变幻,但人们记住的,一贯是——那个才情绝世、洒脱若仙的诗仙李白。他的名字,犹如不朽的传奇,永久镌刻在中华文学的辉煌篇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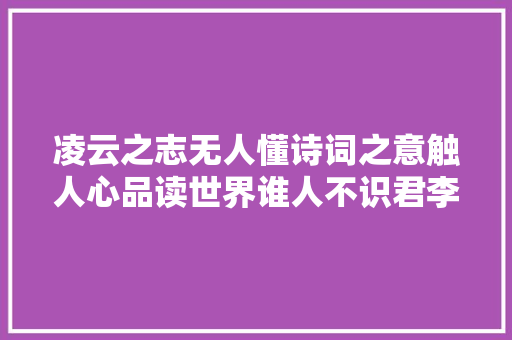
与李白同时期的著名选评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称他:“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可见他的生活办法和好尚是十分独异的。
而今人写李白,视野更宽广,吴斯宁的新作《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以诗立传,总结诗仙李白的脾气生平,由由然出世,愤愤然傲世,昂昂然超世,再次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理解那个既熟习又陌生的李白。透过作者富有诗意的笔墨,李白光鲜、洒脱背后不为人知的困窘与尴尬、失落意与沉重,重塑了我们对李白的认知。
《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从李白的出生与出身讲起,将青年、中年、老年的人生轨迹串联起来,将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的苦闷并联起来,从旷达、浪漫、明快的诗歌到权力官场下的百忧与万愤,直至无奈下的人生归去,留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的终极唏嘘。
李白生活在唐王朝的壮盛期间,即所谓“盛唐”。此时的唐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特殊是儒、释、道思想并存,各种思想十分生动。
正是在这样的时期背景下,学士秀士无不表示出飞扬蹈励、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对仕途充满抱负、产生激情、憧憬未来,都呈现出一种急于事功的生理状态和现实哀求。就连“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在从前也曾有过一定程度的功名希望。
李白也不例外, 生平大部分韶光对峙功立业的激情亲切是非常强烈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一句“仰天算夜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别内赴征》中一句“归时尚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样一时得志时的浮滑与浅薄,是其真实的内心写照。
不过,空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才华横溢的李白生平不得志,现实中的残酷一壁频频打击着他。
自诩“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人生追求始终短缺知音,两入长安失落败后陷入了“我本不弃世,众人自弃我”(《送蔡隐士》)痛楚。他的代价取向既不为权贵,也不为大多数士人理解。
李白的陷于重重困境,他的求仕之路不是科场及弟,也不是疆场建功,而是隐居、干渴这样一条当时所谓的“终南捷径”。天宝元年,在贺知章、玉真公主等人的推举下,李白终于以布衣之身应诏,进京供奉翰林,掌管为天子草诏之职,位居清要。
然而在唐玄宗李隆基的眼里,李白不过是一个点缓升平气候的宫廷御用文人,不会成为帝王师友,只能是其“奴才”。这对付“生平傲岸苦不谐”(《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的李白来讲,在热切追求功名的同时更为执著于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愉快颜”(《梦天姥吟留别》),终极地位难保长久,不得不“五噫出西京”(《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仕途不得意,家庭也不幸福。
开元十五年(727年),27岁的李白在安陆与故相许圉师的孙女许氏结为夫妻,以赘婿的身份居于妻家。仰人鼻息的李白功名不就,又常常纵酒狂饮玉山颓倒,渐为妻家族厌薄和奚落。长此以往,夫妻间的感情危急日益加深,许氏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后抛弃了李白。李白对为许氏所弃一事也是一贯铭心镂骨。
之后,李白先与鲁地一妇人同居,再娶故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宗氏不愿包袱照料李白与许氏所生子女的任务,李白也不便将子女接入宗府,只能连续由鲁地妇人照管。
李白去世之时,鲁地妇人、宗氏彷佛当时均不在其身边。李白始终未能组织起一个圆满的家庭,其儿女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受不到良好的教诲,高下两代始终未能沟通融洽,家庭生活极不正常,伦理关系无从建立,这也是李白的人生悲剧之一。
关于李白历史,误将传奇当史实的情形颇多,最令人津津乐道确当属三件事:唐玄宗命高力士脱其靴、李(白)、郭(子敬)互救、酒醉捉月溺死并骑鲸飞升。
力士脱靴、李郭互救虽不可信但已载入正史,酒醉捉月溺死并骑鲸飞升证明其溺死并葬于采石则有可能。三件事无论肯定或否定均无法加以确证,因此只能视为千古疑案。
晚年李白隐居在庐山屏风叠,即便故意思对现实失落望后暂时的退却,但其本性仍旧是“以待贾者也”。以是当永王李麟修书一邀,李白绝不犹豫地欣然而往,企盼着“熏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
在这点上,李白远远逊色于陶渊明。
陶渊明曾把官场比做“尘网”,把自己的为官生涯说成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官场的生活就好比是“羁鸟”、“池鱼”。
陶渊明的办理办法是放弃功名,归隐田园,能够以“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的彻底绝望与心去世,从而在自然山水田园中得到精神的超越与再生。
而李白的办理办法是功成身退,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殊不知,“功成”就必须放弃自我人格的独立精神,“功”不“成”又何谈“身退”呢?!
无法调和的抵牾使李白苦苦地挣扎,执着追求,李白是既绝望但心“未去世”,被判长流夜郎后,一遇赦就做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的好梦,直到临终前一年都还在期待着“申一割之用”的机会。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广弼率部出镇淮(今安徽省泗县)防御叛军南窜。已是61岁高龄的李白听到这个,不顾自己体衰年迈,毅然从军,但半路因病而折回。李白失落去了末了一次从军报国的机会,深感遗憾。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在安徽省当涂县因病去世,享年62岁。临终前,李白发出了末了的感言:“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 终极带着悲愤,带着遗憾,带着对人间间的眷恋,走完了生平。
后世的评论家,由于受各受才性、气质、秉斌、好恶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等成分的影响,对李白的评论褒贬不一,毁誉皆有。
品读《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它不仅是一部传记作品,更是一部富有诗意与哲理的文学佳作。
书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述,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李白这位传奇墨客的人生经历与内心天下,看到了他的豪情壮志、他的孤独失落意,以及他对自由和空想的不懈追求。
读罢《天下谁人不识君——李白传》, 三尺龙泉空在手,杯酒对影泻青魂,只能自醉寒宵,一个永久复苏又永久孤独的巨人在心头油然而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李白,李白的人生不可再复制,李白的诗不可再涌现,李白的天下我们永久读不懂。
在这个快节奏、物质化的时期里,或许我们可以从李白身上汲取一些精神力量与人生聪慧。
不论是任侠游仙、好纵横术,还是隐居学道、漫游寻友,李白的目的便是想参与政治,进仕辅君。虽受尽多少挫折和失落败,李白却仍济世之心耿耿,也从未真正隐退过,只不过时时发发牢骚而已,生平没有舍弃“愿为首相”“济苍生,安社稷”之宏愿,亦为之奋斗生平。
他那无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勇气,他对真善美的执着坚守,都能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更加武断与自傲,不被世俗的骚动所迷惑,年夜胆地去追寻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