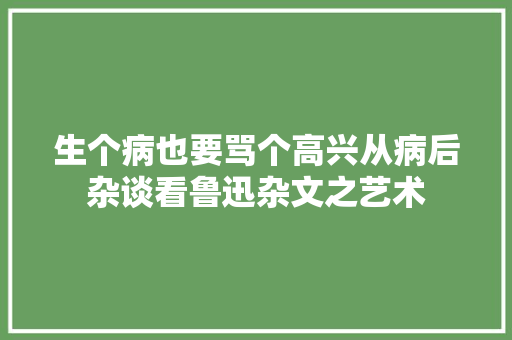杂文古已有之,但在当代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鲁迅功莫大焉。鲁迅的杂文,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好的熔于一炉,尤其让我们称道的,是他在杂文中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挥洒自如。鲁迅的杂文之以是吸引人,紧张是行文手腕非常灵巧,险些到了“运斤成风,十全十美”的绝妙境界。现以鲁迅的杂文《病后杂谈》为例,和大家聊一聊鲁迅杂文艺术特点。
一、开篇时暗藏笔锋, 在铺衬中打好根本
《病后杂谈》作于1934年12月,开篇从生病谈起。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泽。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去世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生病是每个人生平都要经历的事,鲁迅从自己的生病经历开始,在平淡的阐述中,为后面批驳那些“以病为美”病态文人埋下伏笔。这种选材,看似平淡无奇,但切入点却出人意料,在毫无征兆中引入正题,让你惊惶失措,却觉得过瘾无比。
果不其然,接下来作者把讽刺和批驳的笔锋,首先投向那些为封建专制者“帮闲”的文人们。在鲁迅的笔下,他们一种是“愿天下的人都去世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文人;另一种是秋日里吐半口血,病恹恹的去看海棠的文人。
从这里,我们看得出鲁迅师长西席不仅长于选材举例,又极善铺陈伏笔,寥寥数言,就如小刀慢割般戳穿出要么钟情风花雪月的风骚文人,要么具有病态的审都雅念,以羸弱博得众人怜爱的文人的可悲亲睦笑。
遐想到我们当今的社会,实在一些所谓的明星,也是用一种病态审美生理来吸引不雅观众的。比如现在的许多影视剧,阳刚之气消沉,而“娘娘腔却大行其道” ,男不男,女不女者比比皆是,然追随者却比比皆是,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审美代价不雅观。当然,或许是我不懂审美吧!
鲁迅与《病后杂谈》
本来我们以为他该狂风骤雨般批驳病态文人了,但他却又把笔锋回到了自己治病的经历上,从生病又开始谈“养病”,在反复酝酿中,为情绪的爆发奠定伏笔,这种一波三折的手腕,恰好表示了杂文行文的自由。
鲁迅的《春末闲谈》等作品,也有这样的特点。
二、论述时以奇为正,挥洒自如,不落窠臼
绕了半天,鲁迅师长西席终于说到了《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客不雅观说,《世说新语》是一部赞颂魏晋风姿的佳作,但鲁迅师长西席引出《世说新语》后,既没有歌颂它,也没有批驳它,而是把笔锋投向书中的传奇人物陶渊明。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我们想:他现在该是歌颂陶渊明的隐士风范,或者根据文章开始判断,该当批驳陶渊明的闲散和“矫情”了吧,可仍旧令我们大失落所望又颇为惊奇地是,作者以陶渊明作为彭泽县令时追求高雅的随意马虎和真正归隐后追求高雅的不已,转而反衬自己的“俗”。用穿越古今,比拟论证的方法,以陶渊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的困窘,进而藏锋般解释自己的论点:既然隐逸都不得,何不直面人生,年夜胆抗争?
归隐后躬耕自食的陶渊明
鲁迅师长西席论证的高妙,还在于他一旦捉住一个点,就用极其细腻的描述,把道理说得明明白白,绝不会轻描淡写。比如他写陶渊明如果归隐时开销的一段:
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便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即是一百五十九元六。比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由于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缺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用饭呢?要其余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三、高潮时直达中央,绝不客气,言必有中
鲁迅开篇时写出病态文人的表现,是为后面的批驳做伏笔,写陶渊明隐逸的随意马虎和不易,也是为后面的批驳做伏笔,一波三折的铺衬够了往后,他便真正切入正题,则其直入骨髓的讽刺和言必有中的批驳,就无遮无拦,如江河冲破堤坝而一泻千里,横扫万物了。
终于,我们在他的笔下看到了他要论述的野史小说《蜀龟鉴》和《安龙逸史》了。从鲁迅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蜀龟鉴》是一部记载张献忠在四川业绩的野史小说。但鲁迅师长西席既没有谈论张献忠的“劳苦功高”,也没有评论辩论明清更替的是是非非,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剥皮”之刑的胆怯。
“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去世。”
接下来,鲁迅从中国解剖学虽然不发达,但剥皮术却不仅种类多,而且极其细致的怪相,刀锋锐利地指出了封建统治者对待公民和反抗者的残暴。轻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封建时期便是靠着残酷的屠戮和君权神授的愚民思想维系统治的。为了让读者深入地感悟这种残酷,惜墨如金的鲁迅,详细的列举了明代剥皮的过程:
……应科匆匆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去世得快活,浑身清凉!
’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伯仲,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去世。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明代“剥皮”严刑
接着,鲁迅从剥皮之类刑法胆怯不已,却鲜见于正史的怪相,进而再次把笔锋指向封建统治者的帮凶——表面追求高雅,实则懦弱违心、或者宁愿为封建统治者粉饰太平的“帮闲文人”。正是由于他们的不作为和故意作为,以是朱棣残酷无比,却仍旧成为一代圣君,清朝的“笔墨狱”禁锢思想,却由于他们故意的忘怀和奥妙的掩蔽,乃至自欺欺人,因此才光明正大的。
鲁迅师长西席在关键之处,长于集中笔墨,一刀致命地戳穿和批驳,比如他详写朱棣对待景清和铁铉的一段:
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畅,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这真是“圆满收场”,令人如释重负,以为天皇毕竟圣明,年夜大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屈辱。……况且那时的教坊是若何的处所?犯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便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
以是,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实在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明代建文帝忠臣铁铉妻女造凌辱
是的,这些帮闲文人们,总是费尽心机为专制和残酷来一个圆满的、令人接管的解读,既不损毁自己道德君子的风范,又为统治者的恶毒找到一个下得了台的体面情由。这种两不延误,实在是精明至极,实在质,便是他们没有直面社会的勇气,以是用“温顺敦厚”的笔调,在自欺欺人的同时,连续替统治者愚蠢后人。细想之,封建统治之以是长久不衰,公民思想难以解放,“帮闲文人”们确有一份“功劳”。他们再不是鲁迅开篇时的可悲亲睦笑,而是可憎可恶了。
四、措辞上引经据典,却又奥妙杂糅;形如太极,却又泼辣有力
鲁迅的杂文之以是给力,紧张是他的措辞极富传染力和说服力,读来让你觉得有些不舒畅,但又不得叹服他笔墨的切中症结。这从开篇到结尾都能表示。
比如他写洋装的二十五六史,《四部备要》时只用了五个字——硬领而皮靴。极其精妙得表现了这种精装书的形状和沉重,可谓神来之笔。
再如用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进而写到上海时只能“悠然见洋房、悠然见烟囱”。“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一句话就将明代专制的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他关于清朝实施“笔墨狱”的论述: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该当惭愧的,但后来随处颂扬的虐政是笔墨狱。虽说笔墨狱,实在还含着许多繁芜的缘故原由,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管到流毒的,是他编削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清代“笔墨狱”
再如他结尾时的论述:由于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刑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切实其实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纵然有谁看了,于我去世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便是对付作者,实在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总的来说,鲁迅师长西席是口语文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为此他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口语小说《狂人日记》,但鲁迅师长西席的口语文,却是冷峻的,并不符合许多人一向的审美风味,然而在我看来,鲁迅师长西席的措辞真的好,一是既有文言文的简洁和真切,又有口语文的细致和明了;二是用典极其讲究,又灵巧自若,恰到好处;三是用词精确到位,不偏不斜正中症结;四是处处显示一种壮实、峭拔的风格,却又刚柔相济,不显生硬。
读《病后杂谈》和鲁迅其它的杂文,我们能深刻领略到鲁迅杂文的高超——看似散漫无序,实则褒贬清晰,不雅观点光鲜,论证透彻。读来如品烈酒、食辣酱,畅快淋漓,大呼过瘾。这种高超,既是对历代文学中讽刺和批驳艺术的集大成,又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一个作家之以是不朽,便是其作品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自成一格。
余秋雨在《废墟》中写道: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终极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感情的安慰,生理的知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涌现了一种真正深奥深厚的文学。
鲁迅的杂文、小说、诗歌等,都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时期废墟和悲哀的戳穿,这种雷霆万钧、绝不留情的戳穿,虽然不符合“温顺敦厚”的传统,却是一个有任务感的文人存心血造就的精神和艺术灯塔。它在当代文学史上放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这道光芒,不仅撕裂了封建统治思想的黑夜,而且为后人的文学创作,供应了可以借鉴的思想源泉和艺术源泉。以是,纵然鲁迅已远去,但绝不会离开人们的影象。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如鲁迅之伟岸、刚烈和诙谐者,世间能有几人?君若生活不易,烦闷萎靡时,可读读鲁迅之文,则精神振奋,闲愁尽消,可谓人间快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