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众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夸奖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善于,且有名作《桂枝喷鼻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众人共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东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以凭吊古迹、吟咏历史为题材的一类诗词谓之怀古诗词。怀古诗词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的里程碑。怀古诗词在历代皆有佳作,到唐代蔚为大不雅观,而怀古词则在唐、五代偶见端倪,但真正独立成体是在宋代,一样平常认为开怀古词风气之先的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桂枝喷鼻香·金陵怀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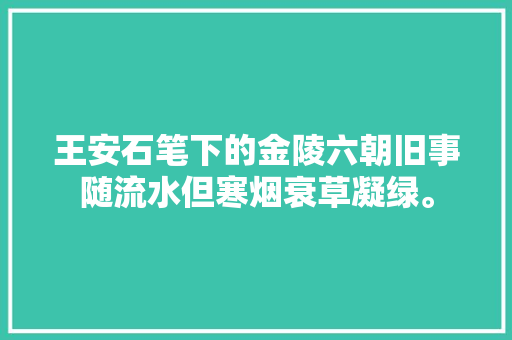
【赏析】此词为怀古讽今之作,作于王安石任江宁知府期间。全词勾勒了一派雄浑苍凉的深秋气候,借景抒怀,引发六朝兴亡感喟,寄托对国事的忧心。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为作者别创一格、非同凡响的精品。这首词通过对金陵景物的赞颂和历史兴亡的感喟,寄托了词人对当时朝政的担忧和对国家政治大事的关心。
词的上片写登临金陵故都之所见;下片写在金陵之所想,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把壮丽景致和历史内容和谐地领悟在一起,自成一格。此词意境开阔,立意高远,笔力遒劲,因景生情,情而兼景,借怀古而抒怀伤今,表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也表示了词人“一洗五代旧习”的文学主见。宋代杨湜《古今词话》云:“金陵怀古,诸公寄调于《桂枝喷鼻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周汝昌则云:“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其笔力之清遒,其境界之朗肃,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真不可及也!
”
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变法失落败、正退居金陵。意境凄清寥落,词意郁郁寡欢,短缺其壮岁时的犹豫满志。全词多处用典,采取虚实相间的手腕,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慨叹和为功名所误的追悔。明代李攀龙《草堂诗馀隽》赞曰:“不着一愁语,而寂寂景致,模糊在目,洵一幅秋光图,最堪把玩。”
王安石从前曾随父王益宦游金陵(今南京),王益去世后,百口就在金陵长期定居。晚年罢相后,又在金陵城外的钟山之麓卜筑隐居,除了《桂枝喷鼻香·金陵怀古》这首词,他还写过不少歌咏金陵的诗篇,《金陵怀古四首》便是他所作以金陵的兴亡历史为题材的一组七律诗。
(一)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怎知与祸双。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译文】凡是取得二江建都金陵的开国之君,大多是白手起身,好不容易取得天下,而其子孙每每轻易地把大好河山断送了。这些政权之以是相继败亡,紧张是继续者得到天下后,日趋奢靡淫乐。那金陵城中的东府城曾是东晋简文帝的丞相、荒淫的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府第所在,现在只剩下几间佛寺了。当年杜牧泊舟秦淮河上,听到商女唱着陈后主谱写的《王树后庭花》遗曲,便遐想到那淫靡之音终于使后主成为亡国之君,杜牧吊古伤今,写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句。如今这十里秦淮,依旧画舫不断,余唱未休。当年东周的大夫和殷朝的旧臣悯伤故国,眷怀旧都,因而作了《黍离》《麦秀》之歌,然而千百年来,兴亡更替,人们对此无能为力。那还是置之不论,统统付之羽觞,以免徒然感伤吧!
(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难双。留连落日频回顾,想像余墟独倚窗。却怪夏阳才一苇,汉家何事费罂缸。
【译文】宋太祖当年的神兵从采石矶架浮桥东渡,一举攻陷金陵,翦灭南唐。敌国的山川形势虽然险要,但在神武的君王面前,却起不了什么浸染,除了屈膝降服佩服别无选择。这统统使人日暮倚窗,遐想不已。当年韩信从夏阳(今陕西韩城)东渡黄河讨伐魏王豹,他在正面集中大批船只,故作疑兵,以吸引敌军主力,而在侧翼用罂缸装着士兵偷渡,一举生擒魏王豹。这里的长江比起“一苇可渡”的黄河来,当然要难渡得多,但宋兵连罂缸都不须要就顺利渡过去了。
(三)阵势东回万里江,云间天阙古来双。兵缠四海英雄得,圣出中原次第降。山水寂寥埋王气,风烟萧飒满僧窗。废陵坏冢空冠剑,谁复沾缨酹一缸。
【译文】万里东下的长江和高入云间的天阙山的双峰,一向都是据守金陵者的天然樊篱,但在五代十国的群雄竞赛中,胜利终于属于从中原南下的英武之主——赵匡胤。这时盘据者在金陵的“王气”黯然而收,只剩下萧飒的寒风吹拂着佛寺的僧窗了。人们有时还可以在那些小朝廷君王的陵墓里找到一些随葬的冠剑,但谁还会来为他们泪沾冠缨,以酒相奠呢?
(四)忆昨天兵下蜀江,将军谈笑士争降。黄旗已尽年三百,紫气空收剑一双。破堞自生新草木,废宫谁识旧轩窗。不须搔首寻遗事,且倒花前白玉缸。
【译文】当年那些盘据江东的小国,只因不修内政而进入日暮途穷的田地。因此当赵宋的王者之师挥戈南下、进军金陵的时候,便天佑人助,没有经由什么艰巨战斗就降服了敌国,好似摧枯拉朽。敌国君主的运数已尽,作为帝国仪仗的黄旗不复飘扬,所谓“三百年王气”黯然而终。如果这里的天上还有什么紫气的话,这不过是过去埋在地下的龙泉、太阿这类宝剑的剑气而已。但这些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现在残破的城楼上已是草木丛生,倾圮的宫殿中再也看不到昔日的门墙和轩窗了。不必再为这些往事搔首惆怅,还是开怀畅饮这玉杯中的美酒吧。
【赏析】在这组诗中,第一首可以说是主题歌,奠定了组诗的基调,这首诗表面上看是怀古叹今的太息,实际上隐含着更深的含义:历史上朝代的兴衰,都不是有时的,骄奢淫逸,是取败之道,该灭亡的就让他灭亡,又何必惋惜呢?这层意思贯穿着整首组诗,这就使得这首组诗不同于以往充满伤感情调的金陵怀古诸作,展示了比较明朗、达不雅观的思想色彩。别的三首诗实际上都是第一首诗的推衍演绎。如果说第一首诗是意在道古,那么别的三首诗则意在论今。这三首诗的前半部分都是对宋太祖攫取金陵统一全国的勋业的歌颂,后半首则多为寄托兴亡的感慨。这实际上是墨客对北宋朝政和士风的逐渐败坏已经有所警觉,因而借诗寓意,这就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内涵,深化了诗歌的主题,使得这组诗既包含着墨客的丰富感情和想象,也包含着思想家深刻的睿智和政治家匡时忧国的肚量胸襟。
用七律写组诗始于杜甫,但杜甫的组诗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每首诗都各有主题和意境,押韵也各诗不同。《金陵怀古》则是四首同韵,并且每首的主题与意境相仿,这是王安石的创新。这四首诗一气呵成,一唱三叹,每首各有特色又不显雷同,宛如一整套旋律和谐而又腔调多变的协奏曲。
除了《金陵怀古四首》,王安石还写过一首《南乡子·自古帝王州》,也是一首金陵怀古之作。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转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此诗亦为王安石晚年谪居金陵,任江宁知府时所作。在表面的表达昔盛今衰之感的同时,把自己非常繁芜的心境,也暗含于诗作之中。 这首词上片怀古,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览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词人以金陵为题来咏史述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全词情绪充足,情调凄凉,动听至深。
金陵是“六朝古都”,龙盘虎踞,形势险要,历来被认为有帝王之气。城里城外,曾经布满了帝王的宫殿苑囿,堪与长安比较。但如今王气消尽,宫苑荒漠消耗,山脉与扬州凭依相连,显得悲惨冷落。唯一可以证明当年的豪华,只有那些高大的帝王陵墓,却也早已被人盗挖,墓中的珠宝金银,常常被人拿到市场上贩卖。王安石行走于荒凉的堤坝间,听公鸡的啼鸣,在黎明的暗黑中催落残月,看春日的野鸡,在空阔的猎场中矫健飞行,看滚滚长江东流不息,他不禁深深感慨自然的永恒,与人间的短暂无常!
人生如梦,是非成败,转眼成空,历史的风云演化,究竟也不过是渔歌樵唱的消闲话题。更多的时候,王安石则因此一位政治家的深奥深厚忧患,总结历史教训、感慨朝代兴亡。#我的读书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