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唐代墨客崔护的七绝成名作——《题都城南庄》。提到这首诗的名字,很多人可能还不太熟习,但是提及“人面桃花”的故事,大家立时就会想到这首诗。
《题都在南庄》问世一千多年以来,在民间一贯传颂不衰。究其成功的原由,无非是表达了一种人类“共通的情绪”。
即描写与爱情擦肩而过的巨大遗憾,以及对过往美好事情的留恋与追忆。所谓“往事如梦不可追”,便是这样了。
然而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书写同类题材的诗词比比皆是,当中也有不少出名的佳作,比如唐人赵嘏《江楼书感》,“独上江楼思悄然……风景依稀似去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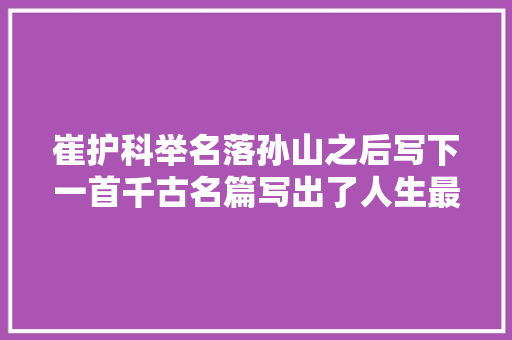
比如刘方平《春怨》,“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还有更出名的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宵》,“月上柳梢头,人约薄暮后”。
以上诗词,全部都是在书写类似于“人面桃花”中与“爱情擦肩”而过的巨大遗憾。但是如果不考虑创作者的名气,只论及诗歌本身取得的造诣时,没有一首超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那么,为什么会涌现这样的征象呢?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赵嘏的“风景依稀似去年”,表达得过于蕴藉。
欧阳修的“人约薄暮后”,又显得过于“直露”;刘方平的“梨花满地不开门”选取的意象,又和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太过于相似了。
《题都城南庄》赏析品味一首诗歌,恰如宋玉批驳“邻家子”:“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又如齐白石谈绘画,“学我者生,似我者去世”。以是千年以来,“人面桃花”的故事,专美于前。
崔护这首诗能够成为千古名篇,除了诗中情绪的尺度拿捏得十分到位以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缘故原由,是作者启动了源于《诗经》中的一个“文学秘码”。
由于这个文学密码的存在,作者就可以直接而轻易地挑动读者的神经,让整首诗显得妖而不艳,媚而不俗,达到孔子所说的“思天真”境界。
那么,这个“文学密码”是什么呢?实在它便是诗中暗含的“桃夭”意象。《诗经·周南·桃夭》是一首爱情诗,原文如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实在。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中的“桃之夭夭”是在借着对桃树、桃花的描写,歌颂新娘的边幅出众,身材丰腴。由于新娘生得好,盘儿靓条顺,以是嫁过去一定会替夫家开枝散叶——“宜室宜家”。
由于有这首诗的涌现,开启了以“桃花”喻美人的先河,后来又把“桃花”与男女的情缘联系到了一起。以是这一场“桃夭梦”,后来险些就成了“艳遇”的代名词。
这种“艳遇”是千百年来,普通人一贯抱负的“艳遇”,大家都想要有。以是写进崔护的诗中,俗人都能读得懂。
但是由于这个“桃夭梦”源于《诗经》,当饱读诗书的学士读到崔护这首诗的时候,并不会立时将它和庸俗的“偷情”遐想到一块儿。反而会想起孔子那个时候,年轻男女的“桑中之约”。
原来在先秦时期,男女们并不是像后世那样,绝对不能“自由恋爱”的。在某一些特定的日子里,先秦的年轻男女是可以在桑林中约会,选择与自己心仪之人在一起的。
在《诗经·鄘风·桑中》里面,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孔子认为,后代的人们应该客不雅观地看待过去存在的事实,承认食色性也。
从古至今,男欢女爱,本来便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一定要秉持“思天真”的态度,精确地去核阅它。
于是文人们读到崔护的这首诗后,第一韶光想起的便是《诗经·周南·桃夭》,并立时对崔护渴望追求真爱的动机,产生出了无限的同情与共鸣。
越是在守旧的时期,人们越是渴望冲破各类规矩的樊笼,以是读到这样的爱情诗篇,越随意马虎达到共鸣。
因此《题都城南庄》,成功地做到了“雅俗共赏”。其余,这首诗之以是成功,还和叙事上的技巧有关。
这首诗一共四句,二十八个字,前两句写过往,后两句写现实;前两句写“人面”与“桃花”是合为一体的,写桃花便是写心仪的美人;
后两句把“人面”与“桃花”分开来写,以“桃花依旧笑东风”来反衬“人面”的不见的巨大遗憾,造成一种落差。
在一合一分,一得一失落之间,自然地创造出了一种悲剧的美。让人为之心中一紧,而后感同身受。
人活一辈子,哪能不带点遗憾呢?不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一个人对付爱情的感想熏染,大多是大同小异的,以是总会有一些爱而不得的缺憾往事。
人总是在得到的时候不知珍惜,失落去的时候就追悔莫及。于是读到崔护的这首诗,便以为他代表自己讲出了心声,怎么能不为它叫一声好呢?
听说,崔护这首诗原来是被题写在“都城南庄”的一块门板上的,后来被经由赶考的诗人争相传抄,可见它也算是一首“老网红诗”了。
后来,由于人们太喜好《题都城南庄》,于是就不断把它改编成戏曲、小说,还编出了崔护和桃花女的一段惊世恋情。
不过这些故事里面讲到:桃花女由于崔护的拜别而自尽,崔护一年后回来她又复活了。这样的改编,虽然让结局看起来更完美,但是却失落去了原诗的意境了。
结语人们每每在人生的重大迁移转变点上,犹豫未定,等到做出一个选择,又后悔没有选择另一个选择。以是不管选了什么,末了始终会带着遗憾。
关于书写这种遗憾,这里还想向大家推举一首王维的古风《桃源行》。这首诗讲的还是《桃花源记》的旧故事,只不过更侧重对墨客的情绪描写。
墨客意外来到了桃花源里,见识了桃花源的美好,但是当居民们约请他留下来时,他却舍不得尘世的繁华。
及至墨客回到人间,又开始惦记桃花,于是又辞家再去寻桃花,结果:“自谓经由旧不迷,怎知峰壑今来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就这样,王维再也找不到他的桃花源了。崔护的《题都城南庄》,看似写的是南庄的“人面桃花”,但是实在也可以理解为写的是一个他空想中的“桃源圣地”。
当初崔护对桃花女故意,桃花女没有回应,可是他也没有坚持。离开一年往后,他才想起来重游旧地,等到他创造“人面不知所何去”时,他就再也找不到属于他的那一片“桃源圣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