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宋神宗时期,实施变法,朝廷的政治开始分解成两派,对文学创作一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宋朝面对的辽国和悍勇的西夏,没有汉唐的大气概,于是须要加强皇权专制中心集权,强调有一个利于稳定的舆论环境。
从苏东坡《明月几时有》的现实到宋江《西江月》的虚拟,都能够看到政治高压的影响在逐步加强。
一、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上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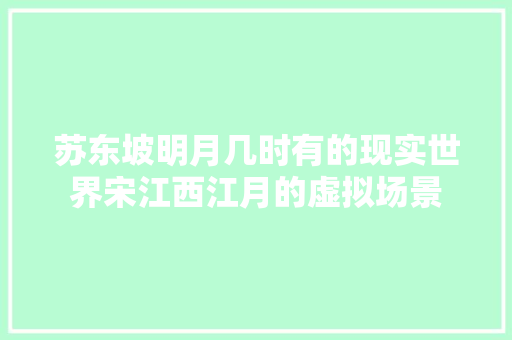
这首词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时所作。
对付北宋苏东坡这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历来都是推崇备至。南宋著名文学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此词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磋商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赏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诸多咏月的诗篇词作。比较之下,还是更喜好北宋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二、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时期背景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朝代,从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间,是一场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心集权利益的社会改革运动,其规模影响堪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紧张目的便是办理北宋建国后皇家中心集权与官僚集团地方地主之间的阶级抵牾,同时抑制地皮吞并,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改变全体北宋“积弱积贫”的社会格局,从而办理全体国家级政府的财政问题。终极达到富国强兵的终极目标。
从终极效果来看,王安石变法终极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国家确实富了,兵力确实强了。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触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守旧派与利益派的强烈反对,内因外祸终极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落败。宋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登基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王安石变法被全部废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王安石的变法是在强化中心集权、巩固皇家利益、践踏个体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落败但影响深远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国家主义者眼里是一次进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虽然政治态度不同,但并不是完备意义上的对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节。
三、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语文释义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苏轼上书评论辩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落。苏轼于是要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并辗转在各地为官。
他曾经哀求调任到离胞弟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差知密州。到密州后,这一欲望仍无法实现。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各处,词人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已七年未得团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引言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写《明月几时有》的初衷,苏轼紧张为表达对胞弟苏辙的怀念。他利用直景形象描述手腕,勾勒出一幅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图画。且把自己清高独立的意绪与神话传说融为一体,通过对玉轮阴晴圆缺的感叹思考,奥妙地对自然征象和社会现实一并抒发了自己的意见。
在词中,苏轼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高兴淋漓发挥。从天上的一轮明月、传说中的宫阙和琼楼玉宇;再到到人间间的亭台朱阁、绮户;再到人生的生离去世别、悲欢离合,都倾情作了表达。
四、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认为,虽然这首词是苏轼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表露出的寓意可见,他的心情并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却是他怀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弃追求的内心独白。
的确,当时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势依旧扑朔迷离,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这才发出了“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感叹。
他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再展宏图的渴望,“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
苏轼调任杭州又知密州,虽说是志愿,本色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田地。只管他于词中作了非常旷达的表白,却也难以掩蔽饰内心的郁愤。因而,还有人说,这首中秋词,也算是苏轼对宦途险恶体验的借景升华与倾诉。
故意思的是,苏轼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词作借题发挥进而陷害他。因此在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说白了便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这词是酒后的胡诌,而且内容是思念弟弟苏辙的私房话。不管再是谁,总不至于拿一个醉酒之人论事吧?
然而,“躲过十五,躲不过月朔“。苏轼的文笔还是给他带来了灾害。乌台诗案正在逼近。
五、苏东坡《湖州谢上表》与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落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发生在变法到改制的迁移转变关头即元丰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宁十年)四月年夜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实在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应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湖州谢上表》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公元1079年(元丰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便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生平的迁移转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去世地不可,接济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纭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公元1079年(元丰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台报告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形,个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笔墨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绅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去世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迟疑不决,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时与苏轼相互诗文唱和,引为心腹的守旧派大臣们,在苏轼入狱其间,一个给他求情的都没有,反而是那些被守旧派称之为“奸邪”、“小人”、“新进”的那些变法派大臣,纷纭上书为苏轼求情。危急来临时,方显本色,此真可谓是一览无余也。
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苏轼口中的对立派“新进”代表人物章惇,也积极的营救了苏轼,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
公元1079年(元丰三年)十仲春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函。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大失落所望。
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既有宋太祖赵匡胤时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又有有识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过小人的暗杀。
六、苏轼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书”
公元1080年(元丰三年)四月,苏轼撰诗并书《寒食帖》,别号《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因宋朝最大的笔墨狱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作了二首五言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宅兆在万里。也拟哭途穷,去世灰吹不起。”
此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
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情状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旷达,而无荒率之笔。
《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七、宋江《西江月》成反诗逼上梁山
历史记载,苏轼离世的18年后的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宋江聚众36人在梁山泊(梁山泺)叛逆。
《水浒传》中虚拟了宋江逼上梁山,源于他在浔阳楼上题写的《西江月》被断定成反诗有很大的关系。
宋江《西江月》反诗是出自《水浒传》的第三十九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那天,宋江来到苏东坡题字的“浔阳楼“。独自一人,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乘着酒兴,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也借得笔砚来,题在粉壁之上。“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略。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痛恨,血染浔阳江口!
”
写完之后,意犹未尽,又在《西江月》后,题下四句诗:心在山东身在吴,秋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题毕留款:“郓城宋江作”。
这是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写的反诗。也正是这一事宜,迫使宋江放弃抱负,终极走上梁山。
若说宋江的诗是反诗,紧张是表示在“血染浔阳江口”和“敢笑黄巢不丈夫”上。实在,我们都很清楚,具有强烈“忠君思想”的宋江,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推翻朝廷的想法。
如果写这首诗的人后来成为了反贼,那这诗就不难懂,可宋江末了成为了忠臣,这就难懂了。宋江究竟何意呢?实在便是借酒抒发内心的真实想法。
《西江月》之以是离经叛道,很可能是一个自大青年郁郁不得志而借酒消愁的一时诳语,并不见得二心坎真的有如此的打算和计较。
《西江月》,绝不是什么反诗,而是宋江期望入朝为官的内心独白,只反贪官不反天子的封建忠君思想。这便是宋江的本意,《西江月》终极所表达的意思。
八、制造宋江《西江月》反诗的黄文炳
黄文炳是在《水浒传》中登场的虚拟人物,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他在浔阳楼上创造宋江题写的“反诗”,向蔡九知府密告,将宋江捕获,后看破戴宗与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计谋,劝蔡九知府将这二人就地处决,梁山豪杰劫刑场,将其捉住处去世。
在宋江题反诗的问题上,是蔡九知府与黄文炳联手制造的一起笔墨狱。完备超越了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宋江《西江月》所谓的反诗,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些牢骚发泄,情绪流露,纵然有过激之语,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未曾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宋江诗词定为反诗,无论如何应该列入“思想罪”、“辞吐罪”的范畴,这种做法当然为当代政治所不取,便是在当时,也违背了太祖天子的誓词。
然而,作为大宋地方官员的蔡德章与黄文炳,急于在“维稳”方面出政绩,以便邀功请赏,仕途畅达,什么太祖誓词、本朝典章,就顾不得了。
蔡黄二人制造的这起笔墨狱,不仅未能保住江州地区的和谐稳定,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乱,可为古今一叹!
有的人把我国的读书人归结为四种人:一是读书做官,这是读书人最崇高的空想和信念;二是歌功颂德,为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歌功颂德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达到个人目的;三是密告,出卖别人为达到个人目的铺平道路;四是嫉贤妒能背后整人,利用阴谋诡计去害别人,达到目的之后便开始小人得志,在害别人的同时还嘲笑那些不如自己的人。
黄文炳可是把后面的三条都占全了。可以说在《水浒传》这部书中,通过对黄文炳此等文人的描写,便把中华文人的劣根性展露无余了。
#全民来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