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说到了40年代的北平名媛义演。义演参与者多为大家闺秀:有清朝大官端邡的女儿;有名誉九城的春山馆主,她也是名门王谢之后,是当时国务参赞周令山之妹;还有个叫臧玉凤的,听说是驻欧洲某大使之女……我们家大格格也在个中,她的积极支持者便是她的婆婆,那个根本不懂戏的警察太太。
以我现在的思想来剖析,宋太太支持大格格到社会上去演出,绝不是出于对京剧的喜好或是对大格格爱好的赞许。她完备是从自己出发,是一种很自私很狭隘的沽名钓誉。她企图用大格格的社会活动,用大格格的名气来提高他们宋家的地位身价,以改变人们对付他们的偏见和挑剔。警察的家族,在力争向文明靠拢,向进步靠拢。
大格格为义演准备的剧目是她拿手的《锁麟囊》。为“春秋亭”那一场新婚的装扮服装,宋家特意着人从苏州购来绣着花卉禽鸟的红帔。试装那天,大格格着上那红装,做了一个身体,盈盈少女,绝代风华,真如同一个美妙的、画上走下来的人儿。当时宋家公子也在场,三公子为大格格的光艳所倾倒,竟激动地说出“得此美人,不枉此生!
”一类的话来。
《锁麟囊》这出戏说的是登州富女薛湘灵出嫁之日遇雨,在春秋亭避雨时与另一贫女赵守贞的花轿相遇。赵女因贫穷而呜咽,薛女仗义合作,将装有奇珍奇宝的锁麟囊相赠,双方未通姓名各自拜别。多少年后,登州大水,薛湘灵无家可归,到赵守贞所嫁的卢家做用人,再见锁麟囊,百感交集。薛、赵重新相见,大团圆结尾。整出戏薛湘灵全是主角,配角人物不过是三两句唱,金家子弟完备可以胜任,那个调皮捣蛋、又刁又势利的丫鬟就由老四来担当。男角演丫鬟配俊小姐,不但能起到很好的陪衬陪衬浸染,也可以插科打诨,增加些噱头,有着女角达不到的效果。为大格格的演出成功,金家全力以赴,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排练中。宋太太没事就过来,端把椅子坐在一边看大家排演,久而久之,竟把戏也记得滚瓜烂熟,很有点儿把场的资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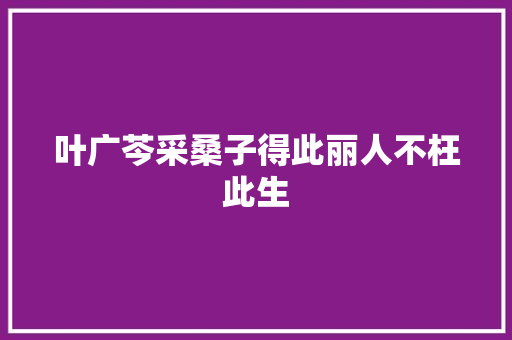
令人担忧的是大格格和老七舜铨总是合营不好。若是在家随便演演,倒也没什么,这可是拿到社会上去演出,是出不得一点儿差错的,稍不在意就砸了。人们看名媛演戏,比对角儿的哀求还严格。角儿一旦有了些资历和名气往后,就可以演得很随意、很自由,不受任何限定。有位名须生,唱到半截儿忽然咳嗽不止,台下不雅观众竟不以为然,后来还有学他的,唱到这儿也咳嗽,真是隧道的东施效颦了。而名媛们演戏,带有玩儿票的意思,跟她们配戏的又多是名角儿,每每这些角儿又爱逗弄这些小姐们,既博不雅观众一乐,又可衬托自己的洒脱。这样一来就常常让小姐们心惊肉跳,开戏如临大敌一样平常,想想也真是可怜。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段故事,有位叫陶默庵的女士,请马连良跟她配戏,演的是《武家坡》。这回马连良大概也想开开玩笑,就像我的大哥拿老七开涮一样,也拿这位女士开涮了。他唱完“八月十五月光明”,张口就问人家小姐:“昨天晚上打麻将手气怎么样啊?”把小姐问得站在台上回不过神来。于是台下大乱,叫倒好儿的大有人在,人们不是哄马连良,是哄那位小姐,实在小姐有什么错?另一位名小姐跟杨宝森唱这出戏也遭到类似情景,杨在末端的收腔时故意又加上了个“哇”,这就占了人家小姐的板槽,让人家张不开嘴了。不雅观众大概想看的便是这样的乐子,就巴不得名角儿们玩点儿花活,让小姐们当场出丑,当场下不来台。也有些有根底、有履历的小姐,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本事,上得台来不慌不乱,在气势上和那些角儿一样平常齐,唱腔好,扮相好,身体好,做派好,这样的女票友不雅观众就很捧。中国的男人捧女优人是天经地义的,捧唱得好的名媛则又高雅又神圣了。为名媛喝采儿,更当花力气,花精神。有许多人来戏园子不是为了听戏,纯粹是为了来喊几嗓子的。说这样可以疏肝泄郁,祛燥排焦,是极好的养生之道。我想,那时中国是由于没有足球,这就不得不逼得一些男爷们儿把精力和激情亲切都扔到戏园子里,扔在那些可怜的戏子们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昔日的戏子与今日的球员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试想,今日的万千球迷在某一天都进了剧院,那真是没有唱戏的活头儿了。但那时候的“球迷”们,的确就都凑在戏园子里,在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中极力抒发着他们的感情。
大格格担心的不是配角成心晾她,而是老七的琴出疏忽。大格格唱的是程派青衣,而老七对程派极为陌生,使得大格格常常有跟不上趟儿的觉得。眼看演出时日将近,大格格心坎不安,连饭也吃不下了。父亲到表面聘请名琴师,一时却又寻不到得当的,百口都很焦急。
不想,这日宋太太领来个瘦弱青年,来者穿着破长衫,夹着把旧胡琴,被胖太太推到众人跟前。宋太太说,这人姓董,叫董戈,是德国医院的杂役,专干些为病人跑腿送信、买东西的杂活儿,有时也为太平间的去世鬼穿穿老衣,替丧家联系联系杠房什么的。大家不明白宋太太为什么办法这么一个人来。宋太太阐明说,有一天家驷听见他在太平间拉胡琴,拉得有板有眼的很流畅,就想起大格格这边的事儿来了,让我把他带来,拉一拉让金家的爷们儿听听,成与不成先试试。大家听了,都以为宋三公子办事太冒昧,把个杂役弄来给大格格操琴,这不是开玩笑嘛!再看这人这没伸展开的样子容貌,穷门倒相的,料也不是什么高手。
那个叫董戈的青年站活着人当间,敛目低眉,任着人们的目光在身上核阅扫荡,没有任何表情。老四说,亲家太太,您趸来的这宝也会拉胡琴?宋太太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让他试试。老五说,扮相不错,我上前门要饭,跟我搭伴儿倒挺得当。老三绕着来人转了一圈,哼了两声没说什么。老二问来人,您会定弦吗?被叫作董戈的人低声说会。老七说,拉一段儿让大伙儿听听。父亲也说,对,拉段儿听听。于是有人给董戈拿来个凳子,董戈调弦,屏气,拉了一段二黄回龙,也没见若何高明。老七说,你拉的是反二黄。董戈赶紧站起来回答说本来二黄该用正工,他用的是小工,由于调低,以是高下宽度大,有五度的跌宕。父亲说,听你拉的也罢了,还不如我们老七。董戈又低头不语。老七问董戈是跟谁学的,董戈说是跟父亲。老七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董戈说是乐亭说书的,父亲已去世,眼下只有他和母亲在北平。老五说,倒是个苦出身,还会拉胡琴,难为了你。父亲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看来他的祖上才是真正的票友。大家问何以见得。父亲说,清入关往后,曾体例唱本,宣扬清朝制度多么优胜,皇上多么清明,然后派滦州、乐亭一带的说书人学唱。学好后,经官场考试合格,发给薪水,派往各地演唱。出京时给龙票一张,所到各处由县中供给吃穿,这便是票友的来由。眼下两地的许多说书人,都是当年票友的后代,世代相传,很有些真人在个中。老五说,阿玛您别扯远了,依您说这个人算不算真人呢?父亲说,这个嘛……宋太太说,假如弗成咱们丁宁他回去便是了。父亲说,给点儿车钱,让人家走吧。姓董的听了如释重负般,给我父亲请了个安,就要辞职。刚走到门口,只听大格格说,回来,我让你走了吗?大家都看大格格。大格格指着董戈说:这个人,我留下了。
这个叫作董戈的人就成了大格格的琴师,也说不上是师,便是为大格格操琴罢了。谁也不知大格格看上了他的哪一点,说留就给留下来了。大格格让他搬到金家来住,董戈说弗成,说他每天得回去照看他的母亲,他假如不回家,他的妈会操心。董戈住在城南,我们家在城东,董戈每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我们家,为大格格吊嗓子,入夜才走,每天是两头不见太阳。为了他的母亲,他刮风下雨也往家赶。他的辛劳让金家的母亲们看了冲动,说我们家七个儿子,抵不上人家一个孝顺,董家老太太不知烧了什么高喷鼻香,得了这么个好儿子。
董戈清晨到金家来的时候,每每大格格还没有起床,大格格有睡
干系图书
书名:《采桑子》
作者:叶广芩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韶光:2019年9月1日
长篇小说《采桑子》由九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游离的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民国往后满族贵胄后裔的生活,大宅门里的满人四散,金家十四个兄妹及亲友各奔西东,描述了老北京一个世家王谢的历史沧桑及厥后代的命运进程,展现出中国近百年间的时期风云、人间更迭与文化嬗变,令人掩卷三叹。满族词人纳兰性德《采桑子·谁翻乐府悲惨曲》,曾被梁启超师长西席赞为“时期哀音”,称其“眼界大而感慨深”,此书亦然。写没落而不颓败,叹沧桑终能释怀,娓娓道来,不愠不躁,从容伸展中饱溢书卷文字之气,颇有大家之风。
作者简介
叶广芩,北京市人,满族。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西安培华学院女子学院院长。被陕西省委省政府付与“德艺双馨文艺事情者”称号,被北京公民艺术剧院付与“北京人艺名誉编剧”称号。享受国务院分外津贴。
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联副主席。曾任陕西省人大第十一届常委会委员,西安市第九、第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紧张作品有:长篇小说《采桑子》《百口福》《青木川》《状元媒》等;长篇纪实《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琢玉记》《老县城》等;中短篇小说集多部;电影、话剧、电视剧等多部;儿童文学《耗子大爷起晚了》。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柳青文学奖、萧红文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中国环保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