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唐大昊
还记得孙杨霍顿一事中,大天朝雄起出征的帝吧吗?当时流传着这么一张图片:
这可以看作是帝吧为霍顿量身定做的“檄文”。可惜的是,这篇翻译可能很难引起霍顿本人和西方吃瓜群众的反响。
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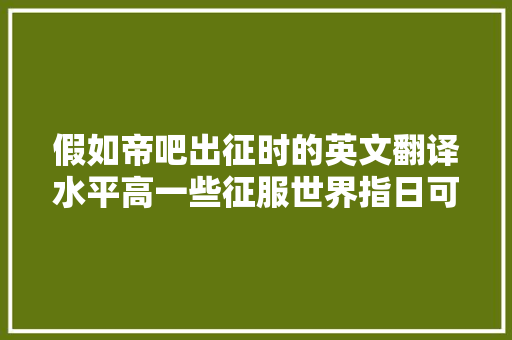
对歪果仁来说,这实在是太难明得了!
这就好比千里迢迢,翻墙出征,临到阵前结果取出来的却是一根巴啦啦魔仙棒,啊不是,擀面杖呀。仅看第二段“先成德,再成人”“First to Germany, then adults.”“先德国人(德国人:???),然后成年人”这样的描述确实很难起到空想的效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以笔墨为武器的抗议行为,打磨自己的抗议工具实能够帮助目标的实现。
当然,翻译这件事,一贯都不是小事。它须要大量的积累和反复的演习。通报核心含义又不失落原措辞的魅力,这便是一件很须要功夫的事情。每年国家大会期间的“美女”翻译总会吸引大量的关注,除了颜值之外,高超的专业素养也是她们备受瞩目的缘故原由。
最近大火的傅园慧也给浩瀚外媒带来了一道翻译题:“洪荒之力”。在千字文里“洪荒”用来形容宇宙初生时的景象,意为“大也,远也”。CCTV据此给出了 “prehistorical powers”的翻译。
而电视剧《花千骨》中的“洪荒之力”指的是强大的妖力。比拟卫报(The guardian)的 mystic energy(神秘的能量),逐日邮报(Daily Mail)的played my full potential, used all my strength 或者是BBC的powers strong enough to change the universe就稍显直白和累赘了。
翻译不能太随意
囧冏有神有先例
我们在日常做英译中或者中译英的时候随意马虎太过“直接”,惹出来笑话。下面刺猬君就为大家总结出来了一些翻译时的万能宝典,任何问题都可以轻松办理。
第一招:直接音译
直接音译的办法由来已久,在清朝,国人刚刚与外来的洋人打交道的时候,便是用音译的办法来标注英文读音。《华夷译语》作为当时的外文翻译辞书沿袭了汉译佛经的办法,紧张是通过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 的注音就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不看英文很难知道这堆字符的所指。比拟起来,如今我们常说的“三克油”,“爱老虎油”看起来彷佛彷佛就更加贴近民生一些了。下面刺猬君为大家带来的便是一些呆萌的直译。
(we found love-喂饭啦 遇见佳人,秀色可餐。言简意赅,没毛病。当然实在也可以叫做潍坊的爱)
(diamond mine-呆萌的我 “呆萌”的钻石,带感的你)
(dick in a box-纸包鸡 彷佛没什么不对。。。)
(the best of the yardbirds-绝味鸭脖,嗯。。。总比百思特鸭脖好一些吧)
(who's that chick?-呼去世那只鸡 然后做成鸭脖,嗯嗯。)
(need you now-你就闹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双手抱头捂耳朵))
(lil daggers-刘大哥 难道不是李大哥?!
)
第二招:土洋结合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会碰着不熟习的或者不知道怎么翻译的词语。特殊是中译英的时候,直接音译已经行不通了,怎么办?不怕!
他们有字母,我们有拼音呀!
不但能鱼目混珠,而且显得很洋气。下面一些例子就完美办理了我们的问题。
(Pai~Hao~ Chamber Only in China)
(非洲复兴的奇迹,日本崛起的福音,金坷拉的产地,American, SHENDIYAGE!
!
)
第三招:强行翻译
很多强行翻译都是Chinglish,表面上用的英笔墨符但是句式受到了中文语法的强烈影响或者词汇误用,不足隧道,重复累赘。这样的缺点随着各种翻译机器的兴起而愈加频繁。
这年头翻译机器犹如雨后春笋是层出不穷,我们彷佛进入了大翻译时期(误),于是就有了一位位要做翻译王的人们(大误)为我们带来一幅幅精彩的作品。
这个招式厉害就厉害在,它并非我国独享而是早已在环球发扬光大,不信请看:
(天妇罗拉面=荡妇汤面)
(宠物的汗液)
(喷鼻香脆裸体球)
(这个。。。哎。。。上火很严重呀)
不管是Chinglish或者其他措辞的“力士”,背后反响的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措辞只是这种差异的一种表象。直接用拼音来表达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除了能防止歧义外,也能勾引利用者站在我们的思维方向上看待事物。类似的例子还有“Tofu”、“Kongfu”而中文中的舶来词如sofa沙发 microphone麦克风等,都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的互换中产生的,它们逐步融入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变得自然,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中文和汉语文化对外界的辐射有多少呢?
根据不同措辞之间的书本相互翻译的数量,麻省理工学院做过一个统计图标:
(图片来源:http://language.media.mit.edu/)
通过这张图表我们可以直不雅观的感想熏染到英语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核心地位。(在图表中,中文是正下方的赤色小圆。)
(图片来源:http://language.media.mit.edu/)
这张图通过圆圈的大小表示措辞利用的人数。两张图一起来看,虽然中文的利用人数最为弘大,但是与天下的联系彷佛并不十分“紧密”,中文群体彷佛是一个更方向于“自娱自乐”的“小圈子”。文化的输出与互换,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中译英不易? 英译中更难!
上述征象可能是中文翻译成英语时产生一些不便和误会的缘故原由。辩论最为广泛的莫过于中国“龙”与Dragon了。我们的龙明明啦么可爱但是到了西方就变成了邪恶的象征。这便是词语背后的文化背景差异带来的违和感。假设中国龙的通用英文是Loong,在往后与外国朋侪的互换中就会省去一些麻烦,最少刺猬君就不用跟外国妹子同学努力阐明科莫多巨蜥和中国龙真的不是一个物种了。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饮食词汇的翻译。很多对英文来说生僻或者不雅观观的词汇会涌如今一些中餐的翻译中,让人忍俊不禁。比如:麻婆豆腐:Tofu made by woman with freckles(一脸雀斑女人做的豆腐);四喜丸子:Four glad meat balls (四个高兴的肉团子);童子鸡:Chicken without sex(还没有性生活的鸡);驴打滚:rolling donkey (打滚的驴)。不过一些常见的翻译也会引起一些误会。比如饺子是Dumpling,粽子是Rice dumpling, 而元宵是Sweet dumpling,从这些名称中我们能得到的是粽子和元宵只不过是另一种饺子,粽子是米做的而元宵只是甜的。这就与现实的情形有了一定出入。
相对日本的寿司直接写作Sushi,拉面译作Ramen,美国中餐馆里面的Chop Suey(李鸿章杂碎)和General Tso's chicken (左宗棠鸡)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左宗棠鸡和李鸿章杂碎)
关于饮食的翻译上面还有一件小趣事。曾在“姚麦”期间的火箭效力的球员“海爷”查克海耶斯生涯末期加盟了萨克拉门托国王队。在随队来中国打比赛期间,受到了中国老朋友的激情亲切接待。席间上了一盘烧海参,海耶斯问这是什么菜,一桌人努力的找对应的翻译和解释,末了给出的回答是:“海里的蚯蚓”。“海爷”大惊,到末了也没有动一次筷考试测验这道“蚯蚓”。(试想一下,海耶斯当时的表情很可能是这样的)
另一件流传比较广泛的便是姚明与西红柿的事情。在姚明刚去火箭队的时候,球队的老大还是对姚明十分照顾的弗朗西斯。有一次面对中国,弗老大问道:为什么姚明那么喜好西红柿。
:啊??(没听说呀?)
弗老大:姚每次罚球不进或者扣篮失落手的时候都要大喊“(Tomato)西红柿”。
:啊,可能那是“Ta ma de”吧。
除了饮食文化,中国的古诗词也是翻译的难点。如何完全流畅的表达出来意思又不失落去原诗词的美感是一个终极的课题。冯唐翻译的个性化《飞鸟集》就很难得到广泛的赞誉。详细的专业知识并不在本日的谈论范围之内。下面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师长西席的一些译作,大家一起来感想熏染一下。
大风起兮云飞扬。A big wind rises, clouds are driven away.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Home am I now the world is under my sway.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Where are brave men to guard the four frontiers today!
---《大风歌》
清明时节雨纷纭, A drizzling rain falls like tears on the Mourning Day,
路上行人欲销魂。 The mourners’heart is going to break on his way.
借问酒家何处有, Where can a wine shop be found to drown his sad hours?
牧童遥指杏花村落。 A cowherd points to a cot amid apricot flowers.
——杜牧《清明》
葡萄美酒夜光杯 With wine of grapes the cups of jade would glow at night,
欲饮琵琶立时催 Drinking to pipa songs, we are summoned to fight.
醉卧疆场君莫笑 Don’t laugh if we lay drunken on the battleground!
古来征战几人回 How many warriors ever came back safe and sound?
——王翰《凉州词》
近年来,外国媒体越来越多的把目光集中在东方这边神奇的大地上。往后还会有更多的关于中国征象的宣布涌现,捎带的更多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也会愈加频繁的涌如今外国的媒体上。这些中国拼音组成的词语将随着这些宣布进入西方大众的视野,或许也会逐步融入他们的生活,就像这么多年的我们做的一样。
而这两年,中国人也越来越多的在“天下主流”的社群媒体如Facebook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还是稍显稚嫩,由于措辞的不纯熟会造成相互理解的困难。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增加了互换的难度。但是这就表示了翻译的浸染。好的翻译,便是要超越文化之间的壁垒,让沟通的双方,达到顺利互动的结果,让我们的声音传的更远。
完
新锐不雅观点 前沿情报
泛传媒第一不雅观察平台
原创出品 授权转载
互助、转载事宜请联系微旗子暗记yunlugong
微博 @刺猬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