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扬州慢》
姜夔(1155——1209)是南宋的著名词人,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他生平没有做过官,到处漂流;他能诗善词,在书法音乐上也有很高的成绩,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推崇。他虽然长期漫游江湖,寄食四方,但贰心系天下,非常关心国家命运、社会变革和政治状况,这首《扬州慢》就表示了墨客这一点。
姜夔精通音律,在按音乐填词的同时还会自己谱制新曲,《扬州慢》便是这一类的作品,这在文学史上称为自度曲。
在宋词发展史上,姜夔是创作自度曲比较多的作家的之一。更为独特的是他所创作的十七首自度曲阁下都标有谱子,这是唐宋词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最为直不雅观的音乐材料,有着非常主要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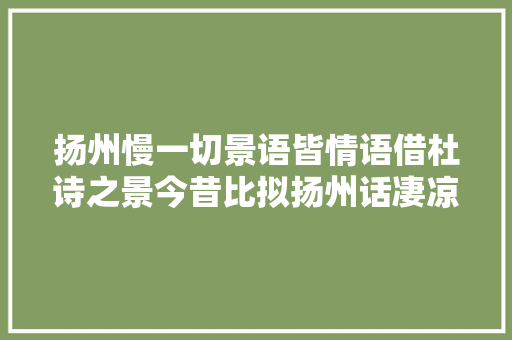
从清朝开始,许多研究者都对姜夔的这些自度曲非常感兴趣,经由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这些作品现在已经可以歌唱了。
(1)词开头独特的引言。
在这首词的前面有一篇长达63字的引言: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冷落,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这也是姜夔词的主要特点之一。
词在刚产生的唐五代期间,词调和词题每每是同一的,到了北宋,词的内容逐渐与词调分离,逐步涌现独立的词题,后来又涌现了引言,而姜夔词的引言是最出名的。
这首《扬州慢》的引言紧张写出了词人的创作背景,包括创作的韶光、地点、缘由等等,与下面词的正文内容相生相发,表现了姜夔一个特定的思想感情。
淳熙是南宋孝宗天子的年号,丙申年即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至日指的是冬至这一天。由于冬至之后阳气回升,代表着又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因此中国古代对冬至非常地重视,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维扬指的是扬州,《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个中淮海惟扬州,在古汉语中惟通维,于是后人就将扬州成为维扬。
词人姜夔在冬至日经由扬州,当时下了一夜的雪,刚刚放晴,抬眼望去,荠麦满目,水波凄寒。薄暮时分,城上吹起了悲惨的号角,这一幕让作者很是感伤,抚今追昔,于是便写下了这首自度曲。
南宋著名的墨客萧德藻(号千岩),读了之后,认为此词作表示了《黍离》之悲。《黍离》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作者是西周的一位大夫,周平王东迁之后,这位大夫经由西周故都,看到以前的王宫现在一片禾黍,非常悲痛,因而写下了这首诗。后人就用《黍离》之悲来指亡国之痛。
(2)词的上片前五句,词人停驻扬州城外,面前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扬州。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东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扬州是一座古城,隋唐以来由于地处大运河和长江航运的枢纽,使得扬州的商业非常发达,社会很富庶,这种状况到北宋期间仍旧延续着。由于扬州在宋代是淮南东路的治所,以是说是淮左名都。
古代扬州舆图
唐代墨客杜牧在《题扬州禅智寺》中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的描写,后来就用竹西代指扬州。
既是名都,又是佳处。
以是,词人来到这里,当然要游赏一番,于是便有了解鞍停马,少驻初程。
东风十里出自杜牧《赠别》中的“东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知。”这里也用来代指扬州。
词人来到昔日以繁华著称的扬州,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荠麦青青,由于无人收拾,荠菜一类的野草长得很茂盛,与麦子相互掩映。
荠麦二字是偏义复词,重心在荠,表现其荒凉。
我们知道词人到达扬州的韶光是冬至,这当然谈不上什么东风,作者这里采取了用典的手腕,除了点明地点之外,也暗示了以前的繁华和现在的冷凄,形成了一个光鲜的比拟。
(3)接着,词人将镜头进一步拉近,从郊野进到城里,映入眼帘的是历经战火后破败不堪的扬州。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扬州的地理位置,处于宋金征战的前沿,金兵不止一次攻进扬州,给这座城市造成了极大的毁坏。这便是所谓的胡马窥江。
那么,历经兵燹战火后的扬州是什么样子呢?
扬州城废池乔木
词人用了四个字“废池乔木”,这些荒废的池苑和高大的古木,都是劫后余存的,只管过了很多年,它们仍旧犹厌言兵。清代词学批评家陈廷焯对这四个字非常欣赏,他认为:“写兵燹后的情景很逼真,犹厌言兵四个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
这四个字有韵味,在于一是无限伤痛见于言外,不写人厌兵,而写废池乔木厌兵,这更显出了战役的惨烈;二是写出了经由惨痛大乱之后,人们特有的心里活动——由于太害怕,太厌恶,以是回避而不愿意再提;三是写出了自金兵南侵至今已过去了十六年,战役创伤仍旧如此之深,令人悚然魂惊。
前面说荠麦青青,此处说废池乔木,实际上二者都是在暗示这座遭受战火的城市如今冷落荒凉、人烟稀少的状况。
于是词人在上片结束时就直接点出这一层含义:
渐薄暮,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在古代,每到傍晚,戍楼上就要吹号角,词人在这里用了以动写静之法,一个寒字,随凄厉的角声而来,既是季候之寒,又是声音之寒,更是空城之荒寒,民气之凄寒。
空城二字,也有多重意蕴。现在的空城固然是胡马窥江所导致的,但以扬州边防之重,经由十六年的经营仍旧是一座空城,如果下一次胡马窥江,又该怎么办呢?
词人在沉痛之中,又有几分焦虑。
(4)在焦虑之际,词人让他非常关注的晚唐墨客杜牧登场,用杜牧昔日所经历的扬州之繁华比拟如今扬州之冷落。
晚唐墨客杜牧在词种出场
作者之以是对杜牧再三存问,既提其诗,也提其人。这不仅是由于杜牧笔下对扬州有着形象且生动的描写,更由于杜牧在这些描写中见证了扬州的繁荣,由此可作为一个光鲜的比拟。
杜牧曾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4年)至九年(836年)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掌布告,对这座城市非常熟习。倘若杜牧现在重新来到扬州,看到如今这座城市的面孔全非,将会大大吃惊。由于这统统的统统他都不再熟习了。
俊赏二字出自梁代钟嵘的《诗品序》——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指鉴赏力博识,但在这里也包含畅快游赏的意思。
以杜牧之俊雅,来到扬州这样一个富贵之乡,风骚之地,当然要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写出无限的深情。
豆蔻出自杜牧名篇《赠别》——袅袅亭亭十三余,豆蔻梢头仲春初。
青楼出自杜牧名篇《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昔日纵情繁华的扬州
这两首诗,都是杜牧写他在扬州的冶游生活的。前一首人花对举,写出自己心仪的一位青楼少女,具有压倒众芳的美;后一首写自己十年扬州留恋青楼,纵情享乐的游荡岁月。
唐代的扬州非常繁华,其繁华的代表性之一便是青楼文化非常发达,由于杜牧对自己生活的这些描写,这正是从侧面记录了扬州的繁盛。
而现在统统都已经飘零。
以杜牧昔日诗中繁华的扬州比拟如今冷落荒漠的扬州,吹糠见米,不能不让人生出凄凉之感。
以是,姜夔才说以杜牧那样的才情,现在看到兵乱之后的扬州,也无法写出那样幽美的诗句,无法传达出心中的深情。
由于心中只剩下凄凉了。
(5)但是,过去的东西也并非全都消逝了,仍有留存下来的,这便是二十四桥,只不过已是冷月无声。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二十四桥是扬州的一处名胜,是给杜牧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模糊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美男何处教吹箫。”写的是深秋时分,远处青山模糊,城外流水迢迢,倚在桥边,凭栏赏月时,只听得阵阵悠扬的箫声,却不知美人在何处演奏。
杜牧心旌摇摇,无限陶醉。全体画面幽美而安谧。晚唐以来,这个画面定格在浩瀚文人的心中,成为了浪漫生活的一个象征。
而如今,二十四桥仍在,可是波心荡,冷月无声。月影落在河里,随着微波而荡漾,一片寒光,默默无声。
扬州二十四桥名胜
姜夔的这个描写非常生动,我们知道玉轮本便是无声,但词人在这里又特意强调,他有什么意图呢?
在古代文学传统中,玉轮是很常见的一个意象,作为一个审美客体,它可以有多重意蕴,能表现多重感情。
杜牧的诗写主人公在明月之夜,听着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阵阵箫声,陪衬的是一种祥和快乐的气氛,因此这玉轮彷佛也不仅有色,而且有声,全体画面充满暖色调。
而现在的扬州城,残破不堪,无限悲惨,玉轮也现出了阴冷之色。
今昔比拟,月之寂寞,人之悲哀,都见于言外,正如王国维所说的:
统统景语皆情语也。
姜夔用玉轮来贯通今昔,虽然是古代诗歌中常见的手腕,但由于他写得真切生动,又具有历史感,以是就能动听至深。
(6)词的结尾两句,作者的目光从水面移到了桥边,这仍旧是一个特写,词人借此进一步表达了悲怆之情。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红药即是芍药,芍药和牡丹是两种花,但是古人并不是分的很清楚。药圣李时珍在《本草大纲》上说:唐人把牡丹称作木芍药。
芍药花
众所周知,唐人喜好牡丹,不分士庶,如痴如狂,正如白居易在《牡丹芳》中所描述的那样:
花着花落二旬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但是在这里,词人写这种花虽然俏丽,却只能在桥边自开自落。花固然不知自己为谁生,人也不知此花为谁生。无法自我欣赏,也不再有别人欣赏。这也就意味着扬州像唐代那样的繁荣已经不复存在了。
时势项化惨痛啊。
词人的这种写法,来自诗圣杜甫。安史之乱后,杜甫作有《哀江头》一诗,追忆唐玄宗和杨贵妃诸人的曲江游赏。记载其繁盛正以是记其衰败。而用细柳新蒲为谁绿一句出之以喟叹。
这细柳新蒲就像是此词中的芍药,为谁绿就像是词中的知为谁生。
词人用带悬念的疑问作为词篇的结尾,很自然地移情入景,今昔比拟,催人泪下。
(7)《扬州慢》是姜夔的代表作之一,问世不久,就广受夸奖,只因词人独具匠心。
扬州慢
宋代末年的张炎在《词源》中就夸奖这首词:
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不雅观飞越。
清空,骚雅是张炎对姜夔词的高度评价,紧张指其词不仅脾气正,而且从虚处落笔,给读者创作了很多感发遐想的空间。特殊是将杜牧的诗句与扬州的过去和现在多元交织,相互生发。
这足见词人之匠心。
第一,情景关系上
情景交融虽是诗词创作的旧调重弹,但却有高下之分。高下片的词,每每上片写景,下片抒怀,此词脉络也大致如此。但这首词妙在不仅情景穿插,而且虚实相间。面前的实景与杜牧诗中之景贯穿,古人冶游扬州的闲情与自己经停此处的悲情领悟,这就使得情随景生,景因情显,表现了作者纯熟地安排节奏,调动意象,转换情思的功力。在构造上也显得灵动而不呆板。
第二,比拟
词人写的是金兵南下,扬州经历战乱后的环境,内在的逻辑构造却是今昔比拟,更妙的是这些比拟是虚实相见,明暗相融。将面前实景与诗中虚景比拟,譬如以名都比拟空城,以东风十里比拟荠麦青青和废池乔木等等。
再有,词人在字面上是写面前之景,实在是化用古诗,暗含比拟。比如杜牧诗中有二十四桥明月夜,词人只点出二十四桥而隐去明月夜,这看似是在写二十四桥的实景,实际上是将明月夜美男吹箫和冷月无声比拟。
二十四桥明月夜,冷月无声
这样就穿越古今,将自己与唐代的杜牧放在同一时空对话。杜牧看到的是唐代扬州的繁荣,姜夔看到的则是兵燹战乱之后宋代扬州的冷落。将古与今,人与我,情与景等等全部打通,多元交织,相互生发,从而展示出巨大的艺术魅力。
以是,千百年来,这首词随处颂扬,广为流传。
参考资料:姜夔《扬州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