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论唐人之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每每将初唐部分略过,直抵杜甫。客不雅观来说,以杜甫为圭表标准固然不错,但杜甫之前百年唐诗史上已有丰富的干系内容的写作,也不应忽略。初唐抒发财国情、忧患感的诗歌,远宗《雅》《颂》,近法曹、刘,而郊庙歌词彷佛与《周颂》诸篇最为靠近了。郊庙歌词是朝廷重大礼仪活动所用乐章,虽为典诰大语,艺术上短缺突出建树,但细绎部分作品,仍可体味某种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如《祀圜丘乐章·凯安》:“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邙山黑云上。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全诗写殷周至汉代由乱而治的历史,寄予幽明叶赞、国运昌盛的祈愿,这样的作品颇能为唐诗赢得一份礼赞。
唐代及五代十国帝王能诗者多,最可称者为太宗、玄宗、德宗和南唐后主,个中唐太宗的作品最具忧患感和道义性。就完全篇章来说,《饮马长城窟行》《过旧宅(其一)》《赐萧瑀》等都无愧唐诗名篇,个中佳句迭现,为初唐诗坛增长了极大光彩。
初唐开国朝臣之诗,文学史家首推魏征《述怀》,而《述怀》所引发的年夜方报国之情,是一代人的感怀,它属于一个群体,乃至全体社会。虞世南“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从军行》);“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轻赍不遑舍,惊策骛戎轩”(《出塞》);“轻生殉心腹,非是为身谋”(《结客少年场行》)等诗句与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诗人”(《从军行》)这种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是同一种基调,其轻生为国的主旋律是时期之声。
法制的公道是社会公正的担保,重罚固然可以作为手段,但苛政每每导致民生惨凌,社会失落序,故为政者深知“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虞世南《赋得慎罚》中提倡的“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的管理不雅观念,是传统文化“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那个时期极为名贵的高度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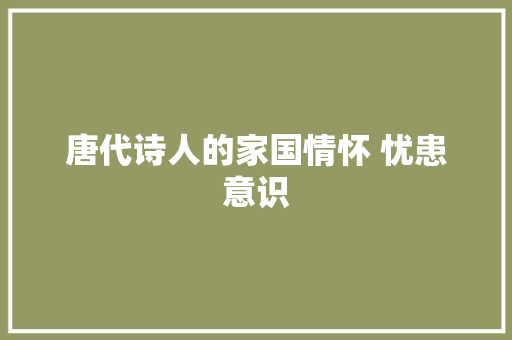
无论从诗歌艺术上还是精神代价上来说,杜甫都达到了文学史的最高度。当我们仰望李白而以为天纵奇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时候,杜甫却一贯站在我们身边,与每一个时期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同在。杜甫的诗是用来诠释历史和人生的,它承担了人间的苦难,做出了对苦难之所以为苦难的反思,同时供应了空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历代诗家重视,便是看到个中忧患的人生和崇高的空想:
纨袴不饿去世,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不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此意竟冷落,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的悲辛具有普遍性,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的空想却兼具了盛唐气候和个人气度。诗末“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高歌让历代读者能感想熏染其激于苦难而奋起的激情亲切。这样的诗歌作品当与动乱年代的《月夜》《春望》《羌村落三首》等,以及“三吏”“三别”诗同读,方能够体会墨客之忧患意识如何融于家国一体的情怀之中。动乱行将结束时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晚年所作《登高》,前者激动而感奋,后者沉郁而磊落,皆非一人之私的情绪抒发,喜与悲俱与大地上的所有生灵相连,与国家的命运相通。杜甫诗号为“诗史”,这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诗史(只管内涵了不少笑剧段落),其悲剧具有的崇高感为唐诗争得了无上光荣。
唐代自安史之乱结束后,人们始终面对着一统山河被分裂的可能,有思想、有情怀的墨客之忧患意识亦即在此。中晚唐诗歌从题材方面说,怀古诗、咏史诗代替了初盛唐的边塞诗成为抒发财国情怀的主要载体,而内容上反对藩镇盘据的作品霸占突出的地位。
韩愈《平淮西碑》与段(文昌)碑之争,是宪宗时期的公案,李商隐充分肯定韩碑的不雅观点,其推奖裴度平叛淮西藩镇之功,实与藩镇叛逆“盗杀宰相武元衡,又击伤裴度,伤其首”(《通鉴》元和十年六月条)的重大事宜有关,对韩愈《平淮西碑》的激赏可见感时忧国的拳拳之心。清人称道李商隐这首七古“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是允当的。好的诗歌首先是立意与情怀之正大,然后是结撰与修辞之精美,即所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精髓,莫非脾气”。
唐代墨客进入历史后,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在民族精神史层面上,唐诗也表现出了更为深广的内涵。
(本文摘自《名作欣赏》上旬刊2021年6期罗时进《与我们“同时期”的唐代墨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