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最喜好的节日莫过于端午。比过年还要欢畅。过年喜庆,穿新衣,亦有好吃的饭菜。但冬季是萧索的,一片灰蒙蒙的天地,终是有些黯淡无趣。
端午节可就大不同了。
0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端午节是多姿多彩的夏天装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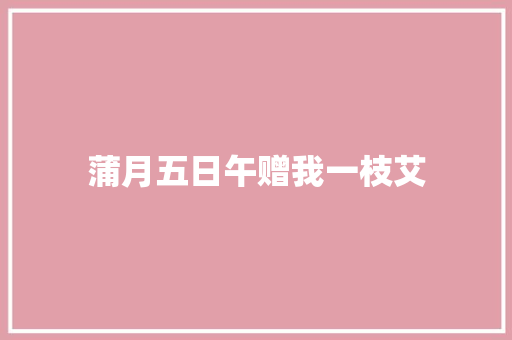
乡间,端午节的夏天,有漫天漫地的花儿。
重五山村落好,榴花忽已繁。石榴花红得热烈标致。雨晴夜合玲珑日,万枝喷鼻香袅红丝拂。合欢花,举着一把一把粉色小扇子,毛茸茸的。
最美的,当属荷花。家乡西北小城,地处旱塬 ,没有江南水乡随处可见的小河,池塘,荷花自然不多见。
我们小孩可是如数家珍,知晓周遭几里屈指可数的荷塘。
亭亭净植,喷鼻香远益清。我们一帮骑车子的小孩,尚未走近荷塘,丝丝缕缕的荷喷鼻香已四周弥漫。一望满眼的碧翠,夏的暑热也褪了几分,有了几许清凉。
荷花宛若大家闺秀般端庄清丽,艾草活脱脱便是桀骜不驯的村落庄野小子。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艾草以极致的浓郁野外气味,向众人彰显,它才是乡野的王者。正是,艾草早已历经千年的岁月照拂,诗经有云“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未及端午,艾草已被乡邻晒干点燃拿来熏蚊子。外婆摇着蒲扇,和邻居谈天。那时的村落庄,夜晚,星子一闪一闪,多得汇成了星河。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蛙鸣,虫鸣,艾烟的喷鼻香味,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的乡音,温馨朴实。宛若悠长的一个梦。
02
端午节到了。外婆忙着搓五彩丝线,做喷鼻香囊。外公忙着割艾草。家乡的方言,五彩丝线唤作花花绳,喷鼻香囊唤作喷鼻香包。
外婆戴上平素闲置的老花镜,选好五彩线,一头抻平,一头放膝盖上仔细捻搓。
彩虹般俏丽的花花绳,我怎么舍得摘掉。
过完端午节,下过一场雨,外婆带我去田边的小渠,剪了花花绳,让它顺着水流漂走。
外婆说可以保佑我无病无灾。
小孩子哪知道什么病呀灾呀,我只是以为可惜,那么美的花花绳,也不知道,流水究竟带它去了哪里。
迢遥的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端午节,被贬至岭南惠州的大文豪苏轼,为宠爱的侍妾朝云写了一首词。
《浣溪沙·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喷鼻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位王姓女子,伴随苏轼度过官场浮沉,颠沛流离的生平。
1096年,34岁的朝云,能读懂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的红颜心腹,病逝于惠州。五年后,65岁的苏轼离世。
03
古老的端午习俗延续至今,五彩丝线依然轻缠手腕,脚踝。缀于绿云鬟的钗符已消逝于岁月的变迁。
然端午节,必要佩戴喷鼻香包,这也是田舍巧妇展示女红的盛大节日。外婆央人去中药铺子,捎回丁喷鼻香、川芎,陈皮,山奈,白芷,甘松,薄荷等中药研磨成粉的喷鼻香料。
外婆做喷鼻香包,都是平日积攒的碎布头。绿色剪作叶子,粉色剪作荷花,桃子。花草,小动物,这些村落庄的精灵,皆是做喷鼻香包的素材。
外婆的喷鼻香包,我必要一个一个挑,挑花了眼。每个都好看,每个都想戴着去跟小伙伴炫耀。
高手在民间。一个远房姑奶奶,做的喷鼻香包,十里八乡出名的好。小马驹喷鼻香包,马鞍,马鬃,马尾,一样不少。荷花喷鼻香包,鹅黄的花蕊,纤毫毕现。
蚂蚱,更是手工风雅,维妙维肖。通身碧翠,双翼轻盈,触角细若发丝。确是当之无愧的民间艺术珍品。
乡间文化的文雅,分外活泼动人。民间是艺术灵感萌发的摇篮。
04
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投汨罗江而去世的墨客屈原。
南方过端午赛龙舟,包粽子。我的北方家乡素以面食为主。每年的端午节,我们小孩渴盼了许久。
戴花花绳和喷鼻香包,自是愉快。吃粽子,更是愉快又幸福。粽叶喷鼻香飘十里,糯米因了粽叶,更有别样的暗香沁凉。
外公割了一束束艾草,挂于门楣,放置窗外,可辟邪,可驱虫除蚊。
佳节又端午。街市有粽子的喷鼻香味,也有喷鼻香包售卖,然手工的很少。还是喜好手工缝制的喷鼻香包,天然淳厚,有野外的灵魂,嗅得到田舍生活的闲趣。
年年纪岁的节日,不会变,未曾老。岁岁年年人不同。曾经是个小孩的我,已人到中年。故人不可见,外公外婆,永久离开了。
如果岁月可转头,能否赠我一段童年,过有外公外婆的端午节……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
作者:童话,北方女子。喜好唐诗宋词的隽永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