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张洋
中国究竟有没有原生的好水果?我相信,看这篇文章的朋友都希望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事情每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略。纵不雅观中国的水果市场,苹果来自欧洲,菠萝来自美洲,西瓜来自非洲,就连喷鼻香蕉也是来自东南亚,更不用说那些新兴的番木瓜、百喷鼻香果、蔓越莓、牛油果等一众新奇水果了。而我国土生土长的水果中,能与外来水果抢占份额的大概也只有柑橘和梨了,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竟然没能组建起一支本土化的军队,这其实有点令人遗憾。
在中国最早的农业文籍《夏小正》中,对水果的描述只有寥寥数笔,个中只记载了桃、李、梅、杏、枣、梨等几种水果。在中华文明的开端之时,就没有一种水果成为主力吗?这彷佛并不是能大略回答的问题。
中国水果的起源到底在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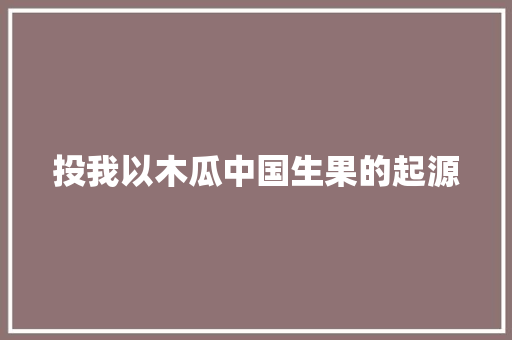
著名的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不乏对水果的描写。个中最为随处颂扬的词句,当属“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很多人会把这一句作为木瓜在当时是宝贵水果的论据。试想,一个木瓜就能换来美玉,这木瓜的代价确实不低。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云南酸木瓜
实在,我在云南第一次尝到酸木瓜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果子实在太难吃了。那是来自喷鼻香格里拉的舍友何志平特意从家中带来的,通体金黄的果实散发着苹果和柠檬稠浊的喷鼻香气。直到下刀才创造,这果子并不随意马虎对付,乃至可以说是执拗。勉强切开,迫不及待地放进嘴里,得来的并不是乳酪扩散的温润,而是如电流在舌尖跳动般的酸爽。十秒钟之后,我在酸味和木瓜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
于是,忽然反应过来,拿木瓜和琼琚作比较,并不是用美玉来映衬木瓜的身价,正好相反,只是把木瓜作为低微物品的象征而已。说得直白一点便是:水果,什么都不是。
我们不妨看完《诗经》的那个句子:“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木瓜和美玉从来就不是等价交流,而是一个芝麻与西瓜的隐喻而已。
尴尬的水果原产地
实际上中国水果的种类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丰富。日本植物学家田中长三郎曾经对天下果树的种类进行过统计,全天下能够供应水果的植物,包括栽培种、野生种在内,共有2792种,而中国现有的果树物种数量大约是670种,连天下水果物种数量的零头都不到。这种情形与中国所处的景象带以及对水果的态度不无关系。
虽然中国幅员辽阔,南北纬度超过很大,但是中国国土的紧张部分都处于温带区域,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区域的绝大部分国土也被高原和山脉霸占,再加上喜马拉雅山脉对印度洋暖湿气流的阻隔,使得中国险些没有真正的热带雨林。
相对单一的景象类型,自然不适于多种类型果实的产生,造成了我们国家原生水果紧张以温带和亚热带起源的种类为主,桃李梅杏加上柑橘和荔枝就构成了中国原生水果的主干。
这样看来,中国水果的形象被设定为一个被随意投出的木瓜,也就不奇怪了。但是问题来了,同样处于温带的欧洲却孕育出了天下共享的经典水果——葡萄和泰西苹果。时至今日,这两种水果在水果界的地位是桃李杏梅所无法企及的。个中的缘故原由并不能用物种多寡来阐明。
猕猴桃
事实也是如此,猕猴桃以新兴水果奇异果的身份,帮助新西兰的果品企业在国际水果市场上攻城略地,出尽风头。直到比来,很多朋友才知道新西兰奇异果的老家在中国,中国险些拥有所有的猕猴桃种质资源。我国在唐代就已经把猕猴桃当做庭院绿植来栽种,但始终没有将这栽种物变成水果。这与中国古人对水果功能的认识有主要联系。
实用至上,统统都是为了填饱肚子
中国古代的第一本博物学著作《山海经》描述了很多具有功能的果子,比如吃了就能永不疲倦的嘉果,吃了就能漂在水里不会沉底的沙棠,然而,整本书少有对水果的形态、喷鼻香气和口味的细致描述。比起口味,中国古人彷佛更重视功效。
然而,中国能填饱肚子的水果还真不多,并且大多数水果的成熟韶光还存在巨大毛病,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比如说,在黄河流域成长的桃、李、杏的成熟韶光,基本上与小米和小麦同步。换句话说,在小麦和小米米成熟之前,青黄不接、无米下锅的时候,这些水果并不能扛起拯救餐桌的大旗。
反倒是那些不是水果的植物果实变成了明星,榆树的果实榆钱便是如此。虽然榆钱的供应韶光非常有限,但是毫无疑问它们能补充一段关键的真空期间。每年三四月间,正是冬粮储备靠近枯竭的时候,这个时候涌现能够供应部分碳水化合物的榆钱,填饱咕咕叫的肚子,可谓雪中送炭。而桃子、李子和梅子都还在成熟的路上。
荔枝
更麻烦的是,这些果实的性能并不堪大任,桃、李、杏、梅,包括柑橘的果实显然不像苹果适于长期储存,更不用说“三日而味变”的荔枝了。
是否及时涌现?是否能长期储存?这两点对付缺少食品加工和储藏技能的古人来说都是至关主要的,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单论填饱肚子这件事,在强大的粮食面前,能抬开始的大概只有大枣和板栗了。至少帮助秦王完成合纵大业的苏秦,在忽悠燕文候的时候曾经说到:“南有碣石、 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此所谓天府也。”(《战国策·燕策一》)燕文侯被说得有些由由然,赞许了互助。
实在只要轻微打算一下,就会创造这是赤裸裸的骗局。要知道,纵然在栽培和杂交技能大发展的本日,红枣的亩产最高不过1000千克。把稳,鲜枣里面有70%以上都是水分,碳水化合物只能占到20%旁边,也便是说一亩所产红枣可以供应的碳水化合物最高不过200千克。而实际情形是,大枣的亩产常日只有200千克旁边。比起五谷,再好的水果也仅仅是个锦上添花的配角。
农耕社会的水果天下不雅观
除了本土水果天然属性的限定,中国很早进入农耕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水果的发展。那些在欧洲本应由水果担当的重任,全都被中国水果拱手让给了粮食和蔬菜。中国人对农田和菜园的留恋远甚于果园,当农田和菜园的产出能知足人类需求的时候,水果自然就成了弃儿,被王公贵族当做尝鲜消遣的工具是其余一回事。
在酿酒这件事上,东西方就走上了完备不同的道路。西方的酒文化显然是基于完美的酿酒水果——葡萄形成的。然而中国选择了粮食,一是由于中国本土并没有葡萄这样高糖分且自带酿酒酵母的果实,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先人在良久之前就节制了粮食的糖化和发酵工艺。利用微生物,把粮食籽粒中的淀粉转化成酿酒酵母,再使粮食中的淀粉糖化发酵成酒精,大大拓展了酿酒业的质料空间。就在欧洲人还在努力造就高糖分的酿酒葡萄时,中国人已经可以把各种谷物变成美酒了。
至于说水果的营养补充,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蔬菜栽种的发展要远远领先于水果。先秦期间,我国就已经形成了完全的蔬菜体系,菜园里的韭菜、菜瓜(薄皮甜瓜)、蔓菁都是常见的种类,还涌现了国民蔬菜——葵(也叫冬寒菜和冬苋菜)。就营养身分而言,蔬菜完备可以替代水果。水果能供应的水分、维生素、矿物质,蔬菜都能供应,水果欠缺的伙食纤维,蔬菜也能供应。水果在中国的尴尬地位就此确立了。
反倒是一贯处于游牧状态的、以畜牧产品为食品的欧洲人,更须要从水果中补充足够的维生素C和伙食纤维等营养身分。在绝大多数韶光里,中国人对付水果的依赖程度都要远远低于西方,即便在文明开端的时候也是如此。
枳和橘的尴尬论断
中国最早的水果栽种很可能起源于当时的皇家苑囿。这些被圈起来的地皮最初只是作为游猎场所和动物的散放地点而存在的,而圈在个中的野水果树就成了中国水果的出发点。最初,这些苑囿中的桃李杏梅更像是不雅观花植物,由于《诗经》等古代诗词对这些植物花朵的描写要远远多于果实。
桃
附带说一句,山楂的经历就更为奇葩了,这个古名为“朹”(音qiu)的物种竟然因此薪炭林的身份涌现的。虽然关于朹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但是直到魏晋期间,山楂依然是烧火的木头。《齐民要术》对山楂的描述是:“朹……多种之为薪。”人们最初栽种山楂仅仅是由于它们的木材适于烧火煮饭,而它们的果实只是一个副产品而已。
中国古人对付水果的漠然,还表示在一些经典的故事之中,比如被奉为智辩经典的南橘北枳。晏子对楚怀王讲出了这样的金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流传千古的故事看似完美地化解了晏子的尴尬,同时又给楚怀王挖了个坑。实际上,不管是吃了哑巴亏的楚怀王,还是暗自得意的晏子,他们都错了。不管是茎秆上的尖刺,还是叶片上的枢纽关头和翼叶,都明明白白地显示,橘和枳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怎么可能由于挪换地点就变成他物了呢?
我敢担保,当时从来没有人想过、也从来没有人做过一件事:真的把橘子树移到淮北,或者把枳树移到淮南试试。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这样的移植考试测验对付当时中国人而言并无代价。这种态度和认识,与欧洲人创造新大陆之后急迫地将两地水果进行交流的做法形成了光鲜比拟。
中国水果的困难起步,实在是农耕社会发展的一定结果。中国古人对农田和粮食栽种的依赖,决定了水果在国人的食品体系中的尴尬地位,特殊是在黄河流域的尴尬地位。中国古人对水果的漠然态度,决定了中国水果发展道路的弯曲和坎坷。
★ 以上内容节选自《中国烹饪》2018年2月刊,欢迎转发到你的朋友圈。本微旗子暗记所有内容未经授权,回绝转载,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提前沟通,得到授权后方可转载。转载时请在显著位置注明来源及作者署名。
作者往期文章
(点击标题,即可阅读全文)
编辑|猫头鹰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