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夜无尘,月色如银。
酒斟时、须满十分。
浮名浮利,虚苦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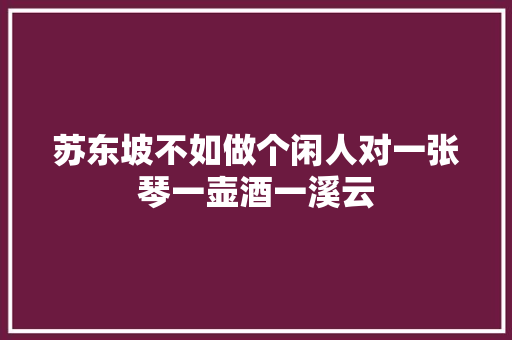
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
且陶陶、乐尽天真。
几时归去,作个闲人。
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回家的那条路,逐日都是开车走过,匆忙的脚步和轰鸣的发动机声粉饰了那份清净的心。如今已是五月,春觉得还没来,就已经走了。多少事以为还没来得及回顾,多少春日的操持还没来得去实现,但四季循环的脚步不会停歇,你永久都敌不过岁月。
对付岁月,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我们在感慨,古人也在感慨。每个人生来,都该当树志,都该当任重道远,这是儒家不雅观点;游山骋水,梦蝶江垂,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这是道家思想。入仕的功利,出仕的清净,也困扰了中国文人几千年。这首词,实在便是苏轼陷于出仕入仕纠结之中写来的。
从其所表现的强烈退隐欲望来看,应是苏轼在宋哲宗元祐期间(1086—1093)的作品。当时宋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持朝政,罢行新法,起用旧派,苏轼受到分外恩遇。元祐元年(1086)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重位。但是政敌朱光庭、黄庆基等人多次以类似“乌台诗案”之事欲再度诬陷苏轼,因高太后的保护,他虽未受害,但却使他对官场生活无比厌倦,感到“心形俱悴”,产生退隐思想。他曾在诗中表示:
老病思归真暂寓,功名如幻终何得。
従来自笑画蛇足,此事何殊食鸡肋。
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白天尘世的鼓噪判若两个天下。把酒对月常是墨客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此时的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上苍”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明地思虑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神秘,阒寂无人,恰好镇静地来思虑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常常揭橥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怀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解释: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操心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生平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
作者为解释人生的虚无,从古代文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利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解释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由长期负责思虑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详细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长于从困扰、纷争、痛楚中自我解脱,豪放达不雅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实在际享乐的办法。只有常常在“陶陶”之中才彷佛规复与得到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各类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膜过于阔别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预见,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神往。弹琴,饮酒、抚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空想的一种悲观的生活办法。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须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知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这首词有对岁月如梭消,怀才不遇、功名利禄虚无操心的极思想,也有淘淘天真归隐田园的神往,弹一张琴,饮一壶酒,看一溪春水、一抹行云。可作为一位儒士,他做不到归隐,手中无事,耳边无忧也就不是这个苏轼了。
在当下,有生活中柴米油盐的啰嗦,也有事情中沉沉浮浮的身心俱疲,久了会累的,而我们所须要做的不是解甲归田的那种隐居,也不是乐于尔虞我诈的那种光滑油滑,每天听一首宋词,看一本书,让自己灵魂安顿我们也有有了那一张琴、一壶酒、一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