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五校”中,建校韶光最早、校史最为悠久确当属上海交通大学,如今其已是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海内外著名高校,被誉为“东方MIT”,但初闻交大,不少人均以为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公路、铁道、航运等交通运输领域人才的高校。实在没错,最早的交大确实与“交通”密不可分,其不仅从属清邮传部和民国交通部,而且创始人也正是时任民国交通部总长的叶恭绰。他不仅在交通奇迹上颇有建树,还曾参与创建了交通银行。值得一提的是,叶旧学深厚,诗词歌赋,阅读广泛,金石字画,诸艺兼善,用本日的话来说便是一位标准的“斜杠青年”。
叶恭绰(1881年-1968年),祖籍浙江余姚,生于广东番禺,字裕甫、玉甫、玉虎、玉父、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清末举人,系著名书法家、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生平经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四个期间,清末曾任湖北农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员、清政府铁道督办;民国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交通银行帮理、交通大学校长、全国铁路协会会长、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南京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部长、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国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诲委员会委员、中心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第二届中国政协常委,以及中国佛教学会一至三届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著有《遐庵词》《遐庵汇稿》《遐庵谈艺录》《叶遐庵师长西席字画选集》《交通救国论》等。
叶恭绰出身官宦世家,其曾祖叶精髓,字莲裳,工诗词,善字画,词名颇著;祖父叶衍兰,字南雪,号兰台,咸丰六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良士,官云南司郎中、军机章京,时人赞曰“文采风骚,映照一时”;生父叶佩琮,字叔达,育有二子(宗子叶恭紃,次子叶恭绰)。叶恭绰5岁时即由祖父启蒙,学“四书五经”,并执笔习字;6岁始学造句属对;7岁即能赋诗作词;11岁过继给二叔叶佩瑲,经嗣父亲自教导并延请名师栽培,先后跟喷鼻香山杨蔼楼、鄱阳张喷鼻香崖、江西新建程菊圃、南昌经学家皮锡瑞诸师学《资治通鉴》《史记》《汉书》《历代名臣言行录》《明儒学案》等,随进士、翰林院编修、武陵(今湖南常德市)王以愍和光绪十六年榜眼、文学家、词人、藏书家文廷式学诗文书法,由是学业书法日益上进;15岁时,其已能作《咏蚕诗》:“衣被满天下,谁能识其恩?一朝功成去,飘然遗蜕存。作茧忘躯命,费力冀少功。丝丝虽自缚,未是可怜虫。”气度与志向远非一样平常诗人可比;18岁时,其在广州参加童子试,以《铁路赋》得主考官、广东学政张百熙赏识,以第一名录入府学,后补为廪生;21岁时,其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后,出任湖北农业学堂、两湖师范学堂教员,开启了短暂的“西席”生涯。
若从此仅作教员,则其自幼立下的大志恐难以实现。两年后,叶恭绰捐通判入邮传部,从此跻身官场。长袖善舞、能力超强的他一起青云直上,从铁路总局培植科科员做起,先后担当路政司员外郎、郎中、承政厅佥事、机要科科长、参议厅行走、承政厅厅长、铁路总局提调,31岁时成为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并参与策划清帝逊位、讨伐张勋复辟、联奉反直等活动,在北洋政坛显赫一时。1912年,孙中山入京,与其彻夜长谈,对其“交通救国”的思路和建议高度讴歌,遂对人云:“吾之北也,喜得一新同道焉。”1920年,年仅39岁的叶恭绰出任交通部总长,执掌全国交通奇迹,于交通、教诲、文化和金融诸业建树卓越。首先,在交通领域,其主持统一各铁路工程规范和司帐制度,制订铁路交通干系条例、法规和章程,主持收回帝国主义经营的京汉、京奉等铁路主权,履行京汉、京奉、京张、津沪、沪宁五路联运,筑建北京中心总车站,筹开京沪特殊快车,筹建黄河大桥,创设交通博物馆、铁路材料陈设所,建树良多,政绩煌煌,为近代交通奇迹做出了本色性贡献。其次,在金融领域,其参与创建交通银行,并于民国元年七月由交通部派任交通银行帮理、董事。在叶恭绰主持下,交通银行除办理铁路、邮电等业务外,还兼营一样平常银行业务,并逐步在喷鼻香港、新加坡、仰光、西贡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是我国最早在外洋开设分支机构的银行,其影响力一度超过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银行。1923年5月,其出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部长,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次年8月还任中心银行董事。此外,其还积极参股或发起成立商业银行,相继成为新华储蓄银行、金城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五族商业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京都储蓄银行等多家银行机构的董事长、董事或创始人,可谓民国金融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之一。第三,在文教领域,一方面,其议设通儒馆、国立图书馆;影刊《四库全书》及公私藏书;创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馆并担当馆长;参与中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并担当评审员;发起中国建筑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主理广东文物展览会等,有力推动了近代文化奇迹发展;另一方面,不仅设立交通畅政讲习所,创办早期铁路职工教诲体系,造就了大批铁路交通职业人才,而且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才”为由,制定统一教诲办法,动手改组交通支配高校,为今日海内“交通系”顶尖名校奠定了基石。当时,交通部有4所部属高校,叶恭绰提出“以南洋为中坚”合并组建一所新大学,定名交通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需指出的是,其对高档教诲的贡献并不但是重组了交通大学,更在于重视独立学术精神和当代科学技能的治学理念,从而为交大的长远发展确立了精确“航向”。单从这点来看,将其称为当代教诲家亦不为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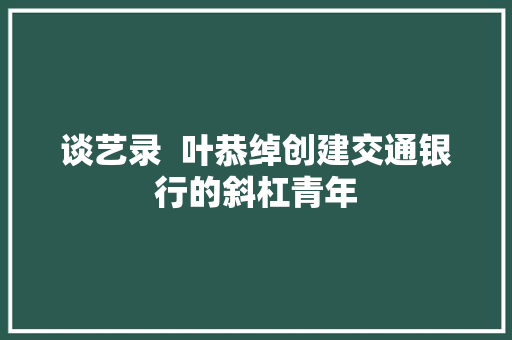
如果说交通、金融救国是叶恭绰这代人的社会任务,那么文化艺术则是他们的“初心”和修为。1925年中山师长西席病逝后,叶恭绰亲笔写就“人性师长西席未去世,我惟心腹难忘”的挽联,并在中山陵捐建“仰止亭”,以寄托对中山师长西席的知遇之恩。此后,因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见地不合,其辞去铁道部长一职,定居上海专事文艺,相继方案了全国美术展览会、故宫赴伦敦展等大型展事。1941年,时年61岁的叶恭绰为避战祸定居喷鼻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年近70的他收到周恩来总理的约请北上参政议政,相继担当了政务院文化教诲委员会委员、中国笔墨改革委员会常委、中心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参与简化整理汉字、推广普通话、订定和实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考古和字画艺术创作与研究事情,以其影响力和远见卓识为新中国的笔墨改革、文物保护和字画艺术等奇迹作出了主要贡献。
清中期以降,随着大批碑刻、青铜器等的相继出土,金石学逐渐兴起,书风也随之而变。尤其是在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等的振臂高呼之下,取法“金石”的书家渐多,一时之间“碑学”大盛。在这样的时期背景下发展起来,加之自幼受善于篆隶的祖父叶衍兰、嗣父叶佩瑲等影响,叶恭绰的书法理念和审美取向也表示出浓浓的“碑意”。如其在《论书法》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书法应根于篆隶,而取法则碑胜于帖,此一定不易之理”,且在1926年跋王铎隶书时又说:“书法不从篆隶出,无有是处”。但与一样平常的碑派书家不同,其所谓“根于篆隶”并非没有取舍,他不会将“穷乡儿女造像”等作为取法工具,而更多是从传统名家的作品入手,选取个中带有篆隶意味的作品深加研习。如其初学时取法颜真卿,从《多宝塔碑》入手,熬炼笔力,节制架构,10岁时已能作擘窠大字,深受长辈讴歌。此后转学赵孟頫,对《胆巴碑》用功尤勤,揣摩至深,乃至成为其生平笔法之根基,其作品中险些每字皆有《胆巴碑》之“踪迹”可寻。但其高明之处在于,学赵并非通盘接管,而是根据自身审美偏好对赵字进行“二次改造”,在长期效法中逐渐汰去赵字娇媚甜熟之意,而强化其挺立刚劲之姿。正如其对《胆巴碑》评价道:“松雪碑版全用李北海法,蹲偃提拔,犹有篆隶遗意,世徒赏其学右军一种洒脱而流于甜熟,非其至也,不雅观此碑方知松雪真本领耳。”在后期,其书法又受到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影响,尤其在结字方面颇有借鉴,于严谨端正中求自然之变革,时有“奇怪生焉”,或绰约多姿,或韵味深藏。
虽然,叶恭绰认为书法取法“碑胜于帖”,但其却并未通盘否定帖学。其曾在1943年跋徐逸民藏《宋拓王羲之书圣教序碑》中说:“往者帖学盛行,《圣教》几与《黄庭》《洛神》等视,自傲碑论盛,几等祧庙,然胜处固不可磨灭也。”这也显示出其在碑学大盛时期的独立思考精神。需特殊指出的是,其之以是能更好地接管借鉴颜真卿、赵孟頫、褚遂良等历代名家的精髓,不仅由于资质聪颖、悟性高超,还在于其作为收藏家的“特权”。如前所述,其任邮传部和交通部期间,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官员一样踊跃投资于实业和金融领域,从中收成颇丰,积累了大量财富。有学者推断,当时其个人资产至少达到数百万银元,这也为其搞收藏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凡当时所能见到的历朝器物、名家真迹、州里专志、清人词集、名僧文字、文书图录,他都逐一收藏。曾被其收入囊中的藏品就有西周“毛公鼎”、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鸭头丸帖》、褚遂良《大字阴符经》、高闲《千字文残卷》、王诜《蝶恋花》(后附有苏轼、黄庭坚、蔡襄三跋)、黄庭坚《经伏波神祠》、米芾书作、元八家书卷、赵孟頫《胆巴碑》、鲜于枢《道德经》、唐寅《楝亭夜话图》、傅山《甲胄诗卷》等经典作品,堪称一部“未完成的中国书法美术史”(后无偿捐给国家)。此外,其过眼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在“博不雅观”之后,实际上其书法已“约取”诸家,达到了“因蜜寻花”“蜜成花不见”的高超境界,故后人每每难以分辨其书究竟出自何家,来自何处。但总体而言,在家族书风影响和碑学盛行的时期背景之下,其大致走的是一条“以碑为主,石本领悟”之路,即:将帖学的洒脱韵致融入碑法的雄浑强健之中,并参与章草、汉隶和金文笔意,善以朴拙古雅的章草、简朴率真的汉隶和错落层次的金文写行草,将碑之雄、帖之秀进行了完美无缝的嫁接与领悟。《中国书法大辞典》评其书“兼有颜真卿之骨力,赵孟頫之秀致,褚遂良之婀娜,《曹娥碑》之韵趣”。曾在北京中国画院作过叶恭绰助手的启功师长西席亦对其书法敬佩有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50岁后,叶恭绰始学作画,由于具有深厚的书法功底上手很快,于松和梅、兰、竹、菊等用功尤勤,所作之画颇具元人神韵,秀劲隽上,直写胸臆,且富“金石味”,故为众人所珍。
中国字画到末了比拼的已不是技法层面的高低,而是字画家个人综合教化与学问的高下。难怪,叶恭绰曾言:“书法须有教化,教化之道,第一为学问,第二为品质,否则虽对书法曾下苦功,然其字之表现,难免不免有卑卑不敷之感。”这既是其对书法尤其是“书外功”的理解,也表示了民国期间字画家对自身学问教化的一向高标准严哀求。而其对“书外功”的实践,除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外,更多的则是表示在严谨的治学和精湛的学问之上。如其曾对艺术、古文、考古和清代学者等做过系统思考和研究,并相继出版《遐庵谈艺录》《五代十国文》《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和《遐庵清秘录》《清代学者像传》《清代学者传像续编》等学术著作。尤其是对词学的深入研究,更使其成为一代词人和著名词学家。其不但长于以词写志,以词寄情,先后创作250余首词作,著有《遐庵词甲稿》《遐庵词》《遐庵词赘稿》等三种词稿,在民国词坛独树一帜;而且编纂出版了《广箧中词》《全清词钞》两部大型词选,并著有《遐庵词话》和《清代词学之拍照》等词学论著。个中,《全清词钞》共计40卷,收录清代词人3196位,词作多达8260多首,对清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评论,资料之详尽堪称“当世第一”,代表着民国期间清词研究的最高水准,具有主要的词学贡献和文献代价。
回望20世纪宦海、经济界、金融界、教诲界、字画界、收藏界乃至宗教界,叶恭绰皆可谓风云人物。其从事文化艺术逾半个世纪,至老不倦,于字画、诗词、考古、鉴藏等无所不精,堪称大家。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孙乐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