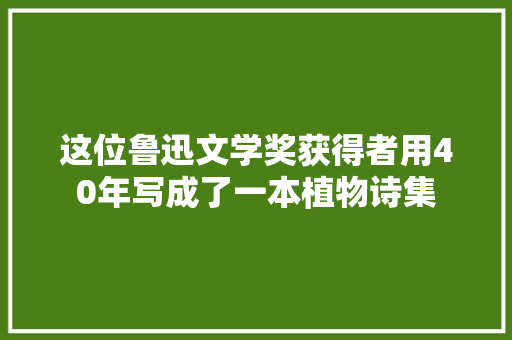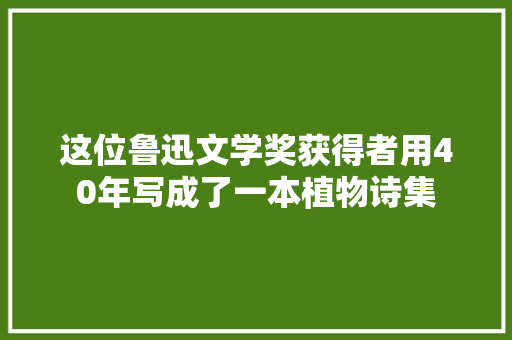诗集刚出版时,本刊曾对臧棣进行采访。对付植物诗,他认为,“把植物变成人生戏剧中新创造的角色。它用它的措辞跟你互换,改变人类的偏见与措辞。一种新的戏剧氛围被打开后,你的听力、觉得都规复了。”
文|艾江涛
随时不定的疫情封控,带给天下的最大改变彷佛是,窗外的植物长得越来越茂盛。沿着清河旁的道路,骑车采访墨客臧棣的路上,成片的仲春兰渐已过了花期,探头探脑的蔷薇爬出栅栏,开得非常残酷。可以断言,我所看到的这些植物,都已涌如今臧棣新近出版,席卷了他近40年写作进程的一本厚厚的诗集《诗歌植物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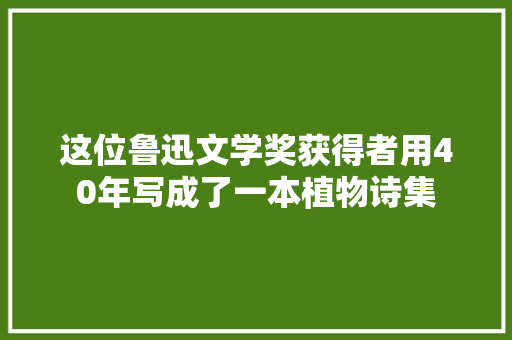
《诗歌植物学》
臧棣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在我们的时期,一个人在诗歌中如此大规模地写作植物又是由于什么?不少人彷佛都带有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乃至偏见——时期是这样的混乱与荒诞,花花草草这样的题材,值得一个有年夜志与抱负的写作者花费如此多力气吗?追溯中国“诗言志”的诗歌传统,这种追问则明显要少。拥有深厚的农耕文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便记录了大量植物,它们不但内生于“赋比兴”的诗歌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知识。但到了当代,这种关涉时期、历史的题材上,小大之辨,彷佛像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萦绕于全体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1979年,卞之琳在诗集《雕虫纪历》媒介中,便谈到那种题材与写法上“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自嘲与低徊。作为一个墨客,同时也是诗歌评论人,臧棣对诗歌主题向来自觉。上世纪90年代,面对人们对诗歌写作的指摘——短缺对时期与历史的呼应和关注,短缺博大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他撰文回应:“人们对90年代诗歌的责怪的根本问题,在于对它的主题的主要性缺少认识。80年代的诗歌主题由于沾恩于历史话语,从而得到一种阅读的普遍性:比如说它的人性主义、空想主义、英雄主义、反文化、对意识形态的疏离、走向天下的文学梦、纯诗主义、措辞的表层化(它的两个变体是反语义和口语化)等等。而90年代的诗歌主题实际只有两个:历史的个人化和措辞的欢快。在少数精良的墨客那里,这两个主题总是交织在一起涌现的。换句话说,90年代的墨客并没有回避历史和时期。这种不加回避,倒不是说历史和时期是无法回避的;而是说他们在处理历史和时期这样的主题时,很少会对它们所具有的异化力量,再像以往的墨客那样感到压力和恐怖。”基于美国墨客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倡导的“欢快诗学”,臧棣见告我,自己并没有写作题材上的焦虑。遛弯,跑步,随手记录下身边事物的片段,再经由反复琢磨修正,他在40年的韶光里,养成差不多每周写一首诗的写作习气。“我后来反思,我写植物诗,有一点点祖传成分。我姥爷是个中医,常常研究植物,以是我妈对植物就比较关注。那时候生活很简朴,荠菜上来了,就吃点荠菜饺子。小孩都不会吃莴笋叶子,她老人家拿来烫了蘸着吃。我当时不理解,转头才以为,实际上她是在一个很贫瘠的环境下,调度生命与天下的其余一种关系。”臧棣回顾,自己比较集中地写植物诗,是在15年前。那时,他刚买了屋子,小区院子里花草特殊多。恰巧读到一篇《诗经植物研究》的文章,研究古诗中的植物,让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人,人们每每关注重大的人生,却每每忽略、鄙视身边小的事物。“它们凭借随处可见,以及/采撷方便,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真实的安慰:就仿佛/末了关头,自然依然是可靠的。”正如臧棣在这首《灰藜简史》中所写,作为一种特殊的伴侣,植物总在一些时候给人精神的疗愈。“我的想法是,诗歌中没有小大之分。诗歌要创造自己的天下,在一个有缺陷或邪恶的天下里面,得到我们自身生命的觉醒与完成。诗歌只要写出独立而真实的生命感想熏染,就会超越一样平常意义上的小和大。”在此意义上,向来被人忽略的植物,是值得相信与开拓的天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臧棣对诗歌写作进行了很大调度,日常生活开始不断进入他的诗歌。“我从前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包括惠特曼、叶芝等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认为写诗比较神圣,有时候写得特殊辛劳。9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我当了三年。那时就有一个问题,每天写那种中规中矩的新闻,和诗意的反差特殊大。有时又有感触怎么办?以是我开始强调那种并非要在一两天写成一个完全东西的想法,有点像罗兰·巴特,随手写片段式的碎片。久而久之,更多关注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物,平凡中见不平凡,可写的题材也越来越多。”臧棣说。这种诗歌不雅观念的变革,同样折射在臧棣所写的植物诗中。从1984年的第一首《房屋与梅树》,到《玉兰树》等早期诗歌,臧棣的写法依然偏于传统咏物诗,“先去细心地不雅观察,创造吟咏工具的美,做一番感叹式的陪衬或吟咏,或者把你的人生落差投影到对方,用植物纯挚的美治愈自己,从生理线索来讲,便是一些纯感想熏染性的东西”。2001年那首《咏物诗》,臧棣将诗的写作过程融入个中:“每颗松塔都有自己的来历,/不过,个中也有一小部分/属于来路不明。诗,也是如此。/并且,诗,不会窒息于这样的悖论。//而我正写着的诗,暗恋上/松塔那层次分明的构造——/它哀求带它去看我拣拾松塔的地方,/它哀求回到红松的树巅。”“早期的植物诗,我只管即便往虚里写,抹去现场的痕迹,形象弄得很纯粹,有点像当年‘九叶派’所说的玄学化。90年代末期之后,可能受到盘峰诗会辩论的影响,我以为还是要在场,诗歌的履历,不要怕日常或个人的痕迹。”1999年在北京平谷盘峰宾馆举行的“盘峰诗会”,是当代诗歌领域一次常被提起的谈论。那次诗会上,歧议丛生的以口语化、反文化为特色的“民间写作”与臧棣这样被指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学院派墨客之间展开剧烈的辩论,事后两派都相继揭橥文章,出版诗歌选集。转头来看,辩论对双方写作都有某种纠偏,正如臧棣所言,他的植物诗中,开始故意识地涌现诗歌写作的详细场景,这种现场感让不雅观察有了落地的结实与相信感。上世纪90年代中期,西川与唐晓渡、欧阳江河、王家新、翟永明、王瑞芸、臧棣(右一)在北京(西川供图)
于是,我们读到一种臧棣诗歌中难得一见的叙事性或者个人传记线索。《茉莉花简史》中,每一片绿叶、每一朵花蕾都对应着属于母亲的细节:“别的植物/都不会有它这样碧绿的肩胛骨,/洁白的绽放仿佛能接住/母亲的每一滴眼泪;当少年的我/追问为什么时,母亲会像她/从前做过的战地护士那样/利索地擦去痕迹;而我想要/做一个好孩子的话,就必须听完/从她的湖南口音里飘出的/另一首欢畅的歌。”《荠菜简史》中展开了春天挖野菜的人们的戏剧化场景:“左手提皱巴巴的塑料袋,/右手握着小铲子;头戴的遮阳帽/像是刚抖落掉半斤火山灰——/一点都不夸年夜,开春不到十天,/小小的燕园里,她已是我见到过的/第一百六十四个挖野菜的人。”2007年旁边,臧棣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梳理传统咏物诗的观点。他开始考试测验创作一种新的带有戏剧氛围的人生情状诗,或者说关于存在的植物诗,正如臧棣自己所说:“把植物变成人生戏剧中新创造的角色。它用它的措辞跟你互换,改变人类的偏见与措辞。一种新的戏剧氛围被打开后,你的听力、觉得都规复了。与以前那种纯挚吟咏领悟的诗比较,更为繁芜,有一种巴赫金讲的复调的东西。”如果相信叶芝的说法“诗是一种自我争辩”,那么臧棣后来的植物诗,首先要与中国古代深厚的书写不雅观念进行争辩。在《紫草简史——仿白居易》中,一个戏剧化的开头,瞄准的目标正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给历史分类时/它显露出的快乐/仿佛构成对人的无知的/一种绿色的嘲讽”。这种偏见,在草本植物不起眼的低调的欢快中,指向人害怕被历史抛弃的恐怖感。“就彷佛它抱负着//我们终极能进化到/给大地之血重新分类”,则暗示人类该当重新回到与大地血脉相连的归宿。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诗歌场域中,长诗写作,一度成为墨客们展示年夜志与才智的舞台与焦虑所在。臧棣曾与西川、海子等墨客互换对付长诗的意见,他援引法国当代派墨客马拉美的一个说法:“当代诗歌如果超过60行,便是不道德的。”在很长一段韶光里,臧棣认为中国文化缺少西方宗教文化履历中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传统诗歌中轻灵的聪慧难以支持长诗的写作。但这不虞味着,墨客要放弃那种对付规模、体量的追求与抱负,纵然是在植物诗的写作之中。臧棣向我回顾他后来冠以“协会”“丛书”“入门”“简史”等名目的系列诗写作的缘起。“大概在2000年旁边,我溘然以为要写一个成规模的连续性的组诗,可能跟我在北大讲海子的长诗,包括80年代第三代诗歌中整体主义等诗歌有关。如果不能写史诗或者长诗,能不能找到一个更适宜自己诗歌觉得的长度或者文体。协会诗的写作初衷,是用序列战胜随意马虎碎片化的写作,用协会、丛书这样范例的当代制度的发明,书写、守护非常详细眇小的事物,反抗、改动当代制度对这些小事物的践踏和忽略。”“入门”背后,意味着一种诗歌眼力的变革。读到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在《迂回与进入》中对中国思想的解读,臧棣意识到,入门,首先意味着慢下来,对韶光与生命进行自觉的安排与调度。“简史”则受到《人类简史》等著作的启示,“我以为可能须要自己发明一个总括性的眼力,通过简单的高度压缩,去看它在一个漫永劫光里具有的意义”。落实到植物诗的写作中,统统彷佛正像臧棣在《黑松简史》中所写:“恶劣的环境中美的存在,/与代价无关,只涉及我们/还能不能借助植物的性情反不雅观/这天下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植物的命运,便是我们的命运。“如果你把这些植物当成一个生命去尊重,就会创造我们身体里面有些东西实在跟植物一样,一方面很薄弱,随时面临被剥夺、被摧残的命运,一方面也很顽强,我有时候出差,玩几个月回来,一看那些植物还活着。从植物身上,反思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你可以创造自身的存在状态。”臧棣说。于是,在《巴西木简史》中,“你必须学会判断:你对它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神秘的天真,/而非建立在它对你的依赖之上”。在《荨麻简史》中,“也不妨说,来自草木的刺痛/是最好的教诲:让你知道/困难的世道中,你能退回到哪里?/以及最伟大的安慰已将动物的本能/升华到了哪一步?”在《人在科尔沁草原,或胡枝子入门》中,植物帮我们看清了自己,“表面上,它用它的矮小,/降落了你的高度;/但更有可能,每一次弯下腰/都意味着你在它的高度上,/重新看清了我是谁”。在《棣棠丛书》中,“换句话说,和花花草草保持多大的间隔/最难反响一个人是否可信”。植物最初在臧棣的生活中,多少带有仪式感的色彩。“我原来的办法比较野蛮,在表面看到好玩的植物,可能揪回来做干花干草,有一阵子喜好在瓶瓶罐罐里插些不知道的植物,彷佛它们能带给我一种灵性。”后来臧棣也在家中种紫苏、藿喷鼻香、柴胡,以及桑葚、绿箩、芦荟等易于生存的植物。童年期间中草药带给他的那种喜悦,随手扯一把紫苏或者韭菜炒着吃的实用主义,仿佛就像他的诗歌,始终谢绝浮泛而廉价的意见意义主义。植物,同样包含着生命的秘密与疗愈的希望。“植物身上有着某种循环的色彩。在北方,到了冬天它们就休眠,春天一来又复活过来,活气勃勃,也带给我一种生理上的暗示和治愈功能。”就像他在《苦瓜男孩简史》中所写的那样:“一个带有苦味的小循环/将你的隐身重新带回现场:/如果须要起誓的话,只有着魔的人,/才能战胜去世亡比悲哀更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