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网络)
十年死活两茫茫,
不斟酌,自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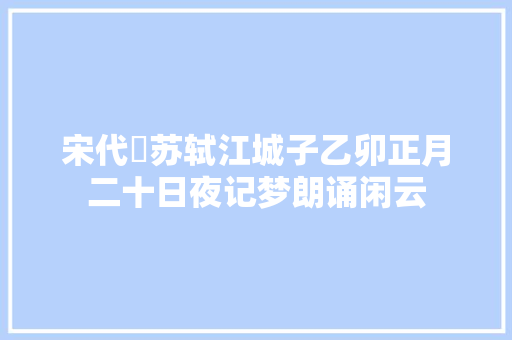
千里孤坟,无处话悲惨。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回籍,
小轩窗,正装扮。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短松冈。(肠断 一作:断肠)
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就已经涌现“悼亡诗”。从悼亡诗涌现一贯到北宋的苏轼这期间,悼亡诗写得最有名的有西晋的潘岳和中唐的元稹。晚唐的李商隐亦曾有悼亡之作。他们的作品悲切动听。而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创始。苏轼的这首悼亡之作与古人比较,它的表现艺术却另具特色。这首词是“记梦”,而且明确写了做梦的日子。但虽说是“记梦”,实在只有下片五句是记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
开头三句,排空而下,真情直语,动听至深。“十年死活两茫茫”死活相隔,去世者对人间是茫然无知了,而活着的人对逝者,也是同样的。恩爱夫妻,撒手永诀,韶光倏忽,须臾十年。“不斟酌,自难忘”,人虽云亡,而过去美好的情景“自难忘”怀。由于作者时至中年,那种共担忧患的夫妻感情,久而弥笃,是一时一刻都不能肃清的。作者将“不斟酌”与“自难忘”并举,利用这两组看似抵牾的心态之间的张力,真实而深刻地揭示自己内心的情绪。十年忌辰,触动人心的日子里,他不能“不斟酌”那聪慧明理的贤内助。往事蓦然来到心间,久蓄的情绪潜流,忽如闸门大开,奔驰澎湃难以遏止。于是乎有梦,是真实而又自然的。
“千里孤坟,无处话悲惨”。想到爱妻华年早逝,感慨万千,远隔千里,无处可以话悲惨,话说得极为沉痛。抹煞了死活边界的痴语、情语,极大程度上表达了作者孤独寂寞、悲惨无助而又急于向人诉说的情绪,格外动听。接着,“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三个是非句,又把现实与梦幻混同了起来,把去世别后的个人各类忧愤,包括在容颜的苍老,形体的衰败之中,这时他才四十岁,已经“鬓如霜”了。明明她辞别人间已经十年,却要“纵使相逢”,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的假设,感情是深奥深厚、悲痛,而又无奈的,表现了作者对爱侣的深切怀念,也把个人的变革做了形象的描述,使这首词的意义更加深了一层。
苏东坡曾在《亡妻王氏墓志铭》记述了“妇从汝于困难,不可忘也”的父训。而此词写得如梦如幻,似真非真,其间真情恐怕不是仅仅允从父命,感于出生吧。作者索于心,托于梦的确实是一份“不斟酌,自难忘”的患难深情。
下片的头五句,才入了题开始“记梦”。“夜来幽梦忽回籍 ”写自己在梦中忽然回到了时常怀念的故乡,在那个两人曾共度甜蜜岁月的地方相聚、相逢。“小轩窗,正装扮。”那小室,亲切而又熟习,她情态边幅,依稀当年,正在装扮打扮。这犹如结婚未久的少妇,形象很美,带出苏轼当年的闺房之乐。作者以这样一个常见而难忘的场景表达了爱侣在自己心目中的永恒的印象。夫妻相见,没有涌现久别相逢、卿卿我我的亲密,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这正是东坡笔力奇崛之处,妙绝千古。“此时无声胜有声”,无声之胜,全在于此。别后各类从何提及,只有听凭泪水倾落。一个梦,把过去拉了回来,但当年的美好情景,并不存在。这是把现实的感想熏染溶入了梦中,使这个梦也令人感到无限悲惨。
结尾三句,又从梦境落回到现实上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料想长眠地下的爱侣,在年年伤逝的这个日子,为了眷恋人世、难舍亲人,而柔肠寸断。推己至人,作者设想此时亡妻一个人在凄冷幽独的“明月”之夜的心境,可谓存心良苦。在这里作者设想去世者的痛楚,以寓自己的吊唁之情。东坡此词末了这三句,意深,痛巨,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特殊是“明月夜,短松冈”二句,凄清幽独,黯然魂销。这番痴情苦心实可感天动地。
这首词利用分合抑扬,虚实结合以及阐述白描等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出生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绪表达得深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