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霞光火烧一样平常艳烈,铺满了半边天。将近处的草,远方的山,无一不淬上一层暖赤色的光。
暮色即将来临,就在这还未来得及散去的末了的薄薄霞光下,官道的那一头,涌现一行黑影,正朝这边走来。
卫卿眯着眼看去,发黑的眼珠里,瞳孔边缘亦染上一丝淡淡的艳色。
来的还不止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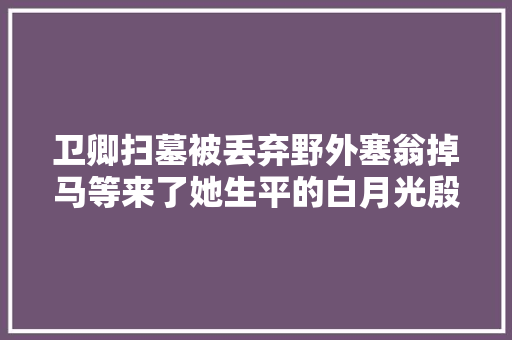
而是一群人。所至之处,鸟影飞绝,周遭一片寂静。
卫卿往车辕上靠了靠,但身子却一点点绷了起来。
若是平凡赶路人还好说,可来的偏偏不是。
随着那些人越来越近,卫卿可清晰地瞥见他们骑着马,暮光下清一色身着鸦青色锦衣,玄色腰带,手握佩刀,头戴乌纱。
那一张张脸上的表情,是漠然和冷锐,乃至还带着模糊的杀气。
卫卿对这个时期的官制并不理解,但看其衣着装扮也能知道,着锦衣、戴乌纱,绝非一样平常的侍卫。
这批人中间,一辆马车平稳行驶,马车四面檐角呈现在青灰的天色下,仿佛披着夜色而来,又仿佛携带着阴郁前的末了一缕光。
卫卿的破车厢正横躺在路坑里,挡了他们的去路。
当时卫卿还在想,这个顺风车她搭是不搭呢?
搭了有一定风险,不搭又以为可惜。
看这架势,即便这行人走到了城门口,城门已经关闭了,他们也绝对有能耐让城门再开一次。
如此,她便不用露宿野外了啊。
卫卿眼不雅观鼻鼻不雅观心,她这么纯良无害,一看便是年夜大好人,该当比较好沟通。
直到那些人走到了路坑前,前前后后才停了下来。
最前面的人瞥见车辕上靠着的卫卿,清清瘦瘦的样子容貌,一双温和的眼里丝毫不见慌张。
若是不把这破车厢和卫卿挪开,他们的马车也过不去。
有几人手悄然握在了刀柄上,个中一个对卫卿道:“阁下请让路。”
卫卿只是想好好沟通,可一点也不想硬碰硬。她复苏得很,真要硬碰起来最先碎的也只会是她自己。
遂卫卿看着那辆马车,道:“如你们所见,这里有一个大坑,我的马车栽在这里,车坏了马也跑了。你们的马车这般宽阔,就算我让开了路,无法避免也得栽在这里,车坏马跑事小,颠坏了车里的朱紫可不得不偿失落么。”
卫卿没有撒谎话,这坑占了大半个官道路面,即便车辙不卡在里面,也会非常颠簸。
几个人神采莫测地打量她。
卫卿又道:“我可以把我车厢木板拆下来,铺平这路,让你们马车顺利经由,而你们顺道搭载我一程,送我进城门即可,如何?”
哪想这群人不具备良好的沟通性,且看他们匪贼般的眼神,看样子是以为放倒了卫卿还是能拆了她的车厢来铺路。
纵然卫卿是个小姑娘,他们也不能完备放心,更何况带她一起上路了。
卫卿手上捻着银针,面上不动声色道:“相互帮助一下不好吗,非要相互侵害。”
她微眯起眼,眼神落在这群人中间,飞速地皮算着自己的胜算。
她心想,实在打不过就往山野里跑呗,这些人担心是调虎离山,肯定不会追太远。
说她运气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由于这伙人不好对付啊。
沟通失落败,气氛陡然凝固了起来。
然正待他们准备动手之际,安静的马车里忽然传出一道声音:“就按她说的来。”
卫卿愣了愣。
那嗓音微冷,平和得没有感情,殽杂着夜里的清风,却极是好听。
此话一出,他的侍卫便急了,道:“都督不可,万一此民气怀不轨……”
马车里的人性:“偶尔也要做一做好事。”
卫卿:“……”她是碰着了一伙专干坏事的人了吗?
他的随从只好应了下来。
随后卫卿起身,往边上站。这些人利落地跨下马,三下五除二就把卫卿的车厢拆成了一块块的木板子,铺在凹凸不平的坑洼上。
可是一行人要连续上路时,并没有多余的马匹给卫卿骑。
车上的人约请她进马车里坐。
卫卿看着面前这辆安静的马车,车帘垂下,遮挡了里面的光景。
她不知那后面坐着的究竟是若何一个人。
可是方才她却听见他的侍卫唤他一声“都督”。
卫卿离车帘并不远,模糊闻到里面飘来一缕淡淡的檀喷鼻香气息,令民气神安宁。
后来她把心一沉,不管了,若是不上她连姑息睡一晚的车厢都没有了,索性利落地掀开帘子,就爬上了马车去。
这马车比卫卿的那一辆更宽大,卫卿进来坐下后,空气中泛开的幽幽冷檀喷鼻香更明显一些。
笼罩的夜色下,可见马车里坐着一名男子,衣袍自然而然地垂落在座上,双手随意地搭在垂直的双膝上,闭目养神。
就连卫卿上来,他也没睁开眼睛看一眼。
卫卿晃眼一看只能瞥见他的轮廓,天色已晚、光芒阴暗,却看不清他的样子容貌。
马车悠悠往前行驶起来,车窗外时时时有骑马的侍卫经由,卫卿知道他们十分防备她。
军队往前走了一段路,路边还躺着那个晕去世过去的家仆。只不过大家目不斜视,压根没瞥见似的,径直往前行去。
马车途经时,见那家仆实在占路了,侍卫才舍得动脚把他往边上踢了踢。
夜风拨开了夜空中的云雾,苍穹里的星月逐渐明朗开来。
莹白色的月光透过窗帘上的缝隙间,晕了一些到车厢里。
诡异的沉默中,卫卿不经意间抬眼看,终于看清了面前的这个男子被月色镀亮的半边脸,不由又是一愣。
卫卿想,大概这古代是盛产纯天然、无污染的美男子的。
起初光看他轮廓时隐约以为英气逼人,是个成熟男子。
而眼下,那半张脸却是丰神俊朗,赛过千雕万琢的无瑕翡玉。
那眉峰细长入鬓,阖着的眼弧仿若水墨一撇,神韵斐然。
月色蔓延至他颈边,衬出颈上很明显的喉结,喉结下的衣襟交叠整洁,纵然天热,也不见分毫疏松缭乱。
非礼勿视啊卫卿,越是好看的东西越危险啊你懂不懂……
四十里路怎么就这么漫长,卫卿实在很想忽略,这车厢里的檀喷鼻香气息下,那一丝丝蔓延开来的血腥味。
直到马车溘然颠簸了一下,卫卿惊惶失措斜了一些过去,手指冷不丁地碰到了他搭在膝上的那只手,卫卿再也忽略不明晰。
他的手湛凉,指尖滴血黏稠。
马车走得不慢,侍卫们又十分当心,身上有股疲态,可能在之前就路上碰着过不测。
这人受伤了。
卫卿在碰到他的手时,他也终于睁开了双眼。
可能任何人在见到他那双眼睛,都会难以忘怀。
那是一副若何的神态呢?
不喜,不悲,不嗔,不怒,仿佛包含众生,却又空无一物,是为慈悲。
卫卿溘然想起,曾经去佛家圣地洗礼时,那里的佛陀菩萨,轻垂着眼,俯视万物众生,便是如此。
而卫卿却是第一次在一个人的眼神里,见到了慈悲之相。
她愣神得忘却了言语,心底里却有个声音不断地提醒她,此人危险,极度危险。
由于这世上没有佛陀,更加没有活在官场权势里还位及都督的佛陀!
在今后的日子里,卫卿才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他拥有一副佛陀的慈悲,却是行走在人间的恶鬼。
卫卿暗暗吸了口气,收回视线,低眼间又落在了他的手上。
那血痕衬得他的手分外苍白,他垂着的手指微曲,指节平均细长。
虽然这血流得烦懑,就算捱到进城也没有大碍,可谁会嫌自己血多?
等卫卿意识过来时,她已经拉住了他的手腕,微微往上抬了抬,血也就不一个劲地往下淌了。
他手腕上骨节也分明,温度是温温热的,卫卿手指上也沾了些黏腻。
卫卿手指瘦削中带着微微的力道,触感尚可。
她靠近些来时,殷璄就已经闻到了她身上淡淡的药喷鼻香,让人舒缓。
他没有阻挡,任由自己的手腕被卫卿拿在手里。
那温顺如水的眼神落在卫卿身上,彷佛能够原谅卫卿统统无礼的举动。
但卫卿知道,可不是如他表面上这么慈善的,一旦她有异动,恐怕会去世得比谁都快。
卫卿道:“你当是偶尔做做好事,我便当是偶尔发发善心吧。伤在哪儿了?”
实际上她却有些气闷——谁要你多管闲事了?
可好歹她现在也在人家的车上,人家还赞许带她一起进城。
既然大家都是一个车厢里的,她顺手帮他止一下血,该当可以的吧?
平白无端的她也不喜好闻到丝丝缠绕的铁锈味。
可殊不知,正是殷璄这偶尔做一做好事,卫卿这偶尔发一发善心,注定今后生平,牵丝扳藤。
殷璄很合营地不疾不徐地解了护腕,松了袖角,便露脱手臂伤处。
卫卿应时从怀中衣袋里取出常备药丸,捏成粉末撒在了他的伤口处。
她低着眉眼,借着表面的月光,手里的动作与神采皆是游刃有余。
这人问也没问一句,就把自己的伤给她治。
伤口止血时,卫卿道:“你不怕我害你吗?”
他问:“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
这声音不轻不浅,恰入心脾,带着淡淡的磁性,好听得有点过分了。
卫卿觉得,听多了耳朵真的会有身的。
诚然,害他对她一丝好处都无,反而是祸害无穷。
后来车厢里便是沉默。
他袖角依然疏松着,彷佛是他浑身高下唯一一处比较散漫的地方了。
他的手连续搭垂在膝上,手指微曲成弧,只不过再没有血滴顺着他的指尖滴下来。
大概走了一半的路程,前面不远便是城门了。
途经一片松林,林间茂密,一丝月光也不透。马车里顿时陷入了一片漆黑,险些伸手不见五指。
卫卿在别人的马车里本来就不可能放松,现在一下黑了,所有感官都被她调动起来。
空气里一丝微不可查的混进来的外界的气味,都能被她的嗅觉给捕捉到。
卫卿浑身一凛。
这松林里弥漫着一股类似瘴气的毒烟,可是气味却比瘴气要清淡许多!
现在是夏天,这里景象又不湿润,怎么可能会有瘴气!
而且白天的时候卫卿也从这松林经由,当时并没有这种毒气。
很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怕是以为对手难缠,以是先下手为强。
树大招风么,对方的目标除了刚好在这个时辰从这条路经由的一行人,卫卿实在想不出第二个。
而与她同行里的马车里的这个男子,该当便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卫卿心下一沉,反应极快,当即捏着袖子捂住口鼻,下意识就倾身过去,贴近在他面前,伸手也捂住了他的口鼻。
她张口便对表面的侍卫低声道:“这空气有毒,大家用衣料遮住口鼻再缓慢呼吸!
”
此话一出,已经有几个侍卫中招,顿时浑身脱力,险些从马背上栽下来。
殷璄和卫卿在马车里不动声色地近在咫尺地相对着。
他的气息落在卫卿的手心上,像羽毛挠动手心,有些轻痒。
卫卿身子习气性地机警地绷起来,气氛一下子凝滞,少焉都磨人神智。
她一举头,如若是光芒通亮一些,便能撞进殷璄的眼眸里。她自己也觉得到,彷佛和他的间隔太近了。
能闻到他身上的檀喷鼻香气息,能觉得到他从自己指缝间溢出的温热呼吸。
卫卿这才意识到,不对啊,为什么要帮他捂?她有这么善良无私吗?
当时就发生在举止一瞬间,卫卿给自己找了个情由——可能是见他手上受伤了吧。
——卧cao,可他另一只手不是好的吗?
——算了,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帮他即是帮自己。
卫卿今后靠了靠,低低道:“你自己用袖角捂着。”
说罢,殷璄伸了手来,叠在了卫卿放在他口鼻间的手背上。
卫卿一抽手,他便自己捂上。
侍卫们驱着马车和马匹,快速地穿过这片松林。
眼看着前面月光如流水一样平常温顺地倾泻而下,大家还没能顺利跑出漆黑的松林,倏尔,周遭动静一响,伴随着风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紧接着便是一道道黑影将大家包围。
刀光剑影,利刃碰撞,不绝于耳。
卫卿透过车窗,第一次见到冷兵器时在即身厮杀的横暴。
那是令人窒息的触目惊心的紧迫。
血气顿时弥漫了全体松林。
卫卿不由光彩,幸好她创造得及时,使得这些侍卫不至于中招。
侍卫的功夫和刀法无一不是博识厉害,且招招置人去世地。
这个危急关头卫卿可不想关心谁好谁坏,她只关心谁去世谁活。
溘然车窗古人影一闪,有杀手趁着侍卫被纠缠的空隙,直接举剑朝马车这边杀来。
卫卿还不及做出反应,只觉一道力扼住她的手臂,将她往身后一拽。
随之那长剑刺入了车窗,却刺了个空。
殷璄抬手就握住了对方拿剑的手,举手投足间依旧温然慈和,可那有力的手指一收,模糊气势宛若天光乍破世间无处可遁形,随着骨骼咔嚓一声响,像撇断一根木柴一样平常,轻巧随意地撇断了杀手的手腕。
听得杀手闷哼一声,他拿着杀手的手,云淡风轻地拨转了剑势,眼也没抬一下,便割掉了杀手的头颅。
那时卫卿听得见自己胸膛里的心跳声,怦怦怦。
殷璄松了手指,杀手的尸体倒在了马车外,伴随着剑落在地上的声响。
他又将手放回膝上搭着,骤然开口道:“你今晚这善心,发得有点大。”
那语气平凡得,就彷佛是在与朋友寒暄。
卫卿扯了扯嘴角,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宝塔么,就当是给自己积德了。”
妈勒个腿哦,难怪这人赞许载她一起同行,且看他喜怒不惊的神态,敢情这种半路刺杀是家常便饭。
这叫做好事吗?这分明叫反正要晦气,垫背的能多拉一个是一个!
虽然,卫卿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可夜路走多了碰着鬼,她才以为原来这种做法真过分!
这些人与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是去世是活原来跟她没紧要。可现在她要想保命,就得让大家都活着。
以是事先创造有毒气时,卫卿才会绝不犹豫地提醒大家。
马车里的男子若是去世了,这些侍卫不会放过她。侍卫若是去世了,她与这男子在一起,那些杀手更不会放过她。
她哪是想救他们,她只是想救自己啊。
假如对自己都不慈悲为怀,不是得遭报应么。
后又有两个杀手,强弩之末,想杀进马车来。
卫卿才不想出头,心安理得地靠在殷璄身后,殷璄随手将原剑送进他们身体里去。
马车走走停停,出松林之时,卫卿瞥见,纵然他杀人,眼里也是如水般温润悯人。
侍卫当中,有几人中毒,也有几人受伤。大家找了个视野开阔之地,停下来休整。
这本也不关卫卿的事,这些侍卫先前想弄她,卫卿还没有菩萨心肠到不计前嫌给他们解毒的地步。
因而她一脸漠然,无动于衷。
可殷璄知道她懂医理,道:“你替我的人解毒疗伤,我送你至家门。”
之前约定的,他们只送卫卿进城即可。可从城门到卫家家门,还有一阵子的路。
眼下这里离进城已经不远,后面该当不会再有杀手来潜伏,等进城往后就更安全了。
既有马车坐,她当然不想走着回去。卫卿想了想,遂接管了殷璄的发起。
侍卫的毒气入体不深,卫卿施以针法,配以清毒药丸,不多时可见好转。
而受伤的侍卫更加好办,撒上止血的药粉即可。
这些侍卫对她仍是防备,可态度已然好转许多。
延误了一下子,大家连续上路。
卫卿本以为等到了城门脚下过后,要花点韶光去拍门,然后等守城的士兵去通报往后再来打开城门。
可没想到,远远就见城门洞开,笼罩在一片通亮温黄的火光中。
城内掌管行省的首脑官员们齐聚在城门处,等着马车缓缓驶近。
卫辞书也在个中。他身为布政使旁边的参政,是掌管行政的二把手。除了行政,还有掌管司察和军政的官员全部都在。
侍卫抵达城门,个中一名官员笑呵呵地上前,拱手作揖,道:“大都督夜抵小城,下官恭候大都督,小城不胜荣光。”
朝廷将地方区域划分得很清晰,一共十三省,省内十三州。而此城便是行省内的首府州城,若这也是小城,那其它各州都不用排上号了。
卫卿就算不知道这些,也知道州府官员们对他,算是恭敬之至了,不由微微侧目。
光火下,他的侧脸轮廓更深邃清晰了两分。他戴着乌纱冠帽,额上整洁,双眉细长而清远,油黄的光泽像淬了一层脂,投映在他脸上闪闪烁烁。
他半低着眼帘,掩蔽了眼里深浅细碎的光,身形不动时,便像是一幅没有瑕疵的油画。
在半路上时,卫卿便已经揣测到,大抵京里来察看的便是此人。
看样子他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更位高权重一些。
大都督,是掌管一朝军事生杀大权的人物?
殷璄问卫卿:“你家在何处?”
话语一出,众官员才得知,原来马车里还有一人,便是不知是何方神圣,大都督竟要送他回家?
这样的场面,虽然过于招摇了些,可是对付卫卿来说,并非全无好处。
由于卫辞书在表面。
她要在卫家稳住,老夫人靠不住,现在有外力助她一把,何乐而不为?
卫卿应道:“我住在东城卫府。”
表面的卫辞书端地一震。那声音有两分耳熟,而且说的东城卫府,除了他家,还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吗?
卫辞书细想那声音,不难就想起来,像卫卿的声音。
他不由举头朝马车看来,正逢殷璄撩起帘子对外嘱咐去东城卫府,卫辞书是看得真真切切,马车里和大都督坐在一起的女子,可不便是卫卿!
殷璄带着护卫亲自把卫卿送到了家门口。
卫卿从马车高下来,殷璄坐在马车里未动。
卫辞书看向卫卿的眼神,万分繁芜。
卫卿抬开始来瞥见了他,温和地唤一声:“爹。”
卫辞书点点头,语气与之前的漠不关心乃至有一丝厌恶大不相同,像个慈父般讯问:“怎么归家这么晚,去哪儿了?”
卫卿道:“今日开祠时不见我娘的牌位,以是出城去祭拜了我娘。”
卫辞书连忙上前朝马车揖道:“小女无状,冒昧了大都督,还劳烦大都督亲自送回,下官实在惭愧。”
“原来她是卫大人之女。”
随后马车掉了头,缓缓驶离了卫家门前。
卫辞书目送着马车离开,转头来时神采莫定地看着卫卿又问:“你怎么会和大都督在一起?”
卫卿道:“家里马车路上颠坏了,偶遇上他,就一起回来了。”
本日一贯到入夜,都不见卫卿回来。老夫民气烦没有问起;若是卫卿一夜未归,到嫡徐氏反倒有话来教训,因而徐氏当然不可能派人出去找卫卿。
徐氏听说卫辞书回来了,忙不迭地出门来迎,正准备把白天祠堂里发生的事添油加醋地说一番呢,没想到抬眼瞥见卫卿,当即就尖着嗓子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到城外去了么,城门早就关了,你怎么回来的!
”
卫卿看了一眼巷弄里的马车影子,悠悠道:“自是有人送回来的。”
“谁送你回来的?”徐氏弗成一世,循着看去一眼就瞥见还没走远的马车,顿时来兴道,“是不是那车送你回来的?车里是个男人?夜黑风高,你们孤男寡女,能做个什么勾当?才小小年纪,就知道勾搭男人了!
”
那声音在安静的夜里醒耳得很。
卫辞书恐怕被还没走远的马车里的人听到,恼怒地一手肘把徐氏往门里推,推得她在门口绊了一跤,跌倒在地。
徐氏举头不可置信地望着卫辞书。
这时巷弄里的马车蓦然停了下来。
那微沉悦耳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巷弄里响起,十分豁亮清明:“卫大人。”
卫辞书面上一紧,连忙快步往漆黑的巷弄走去,道:“下官在。”
殷璄半抬起车帘,道:“城外的官道,烂得无法通畅,朝廷是没拨钱下来修么。”
卫辞书连连应道:“下官服膺,一定尽快择日修葺。”
殷璄放下了帘子,马车连续往前行驶。卫辞书僵着动作,直到目送着马车彻底驶出了巷子,方才折身回来。
回来时卫辞书看向徐氏却一脸怒色,道:“口无遮拦的东西,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当心要了你的小命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
”
说罢,冷冷拂袖进了家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