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古今中外译
石水微澜
序言:
唐诗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贝之一,间隔本日已经由去1000多年了。唐诗三百首可谓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然而我依然认为,唐诗,是须要翻译的。
怎么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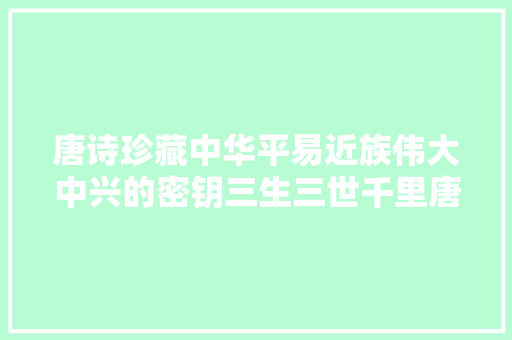
译法至少有三种:古译,今译,外译。
所谓古译,便是用前世或后世的古诗来译唐诗,不一定是正着译,也可以反着译;
便是拉开韶光来读唐诗,300年500年都可以。让韶光给我们新创造。
所谓今译,便是用当代诗歌措辞即新诗译唐诗。这个更多是意译,乃至……改写;
便是拉开语境来读唐诗:你会创造,唐诗可以很当代,乃至是后当代。
所谓外译,便是用外语,紧张是指英语来翻译唐诗,用天下的视角感想熏染唐诗之美。
所谓外译,还可以对接外国的散文诗歌,超过韶光,更超过空间来感想熏染唐诗之美。
便是拉开空间来读唐诗:把唐诗放在外国文化、语境阅读同样有共鸣。
韶光,语境、空间,都是一种间隔。
间隔产生美,更产生不一样的唐诗。
且看,是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天下的?
当然古译、今译及外译为主。间或插一些英译。
我得先承认,古译今译和外译,都可能让原来的唐诗涌现一定程度的误读。
但这个没紧要。故意思的误读,好过干巴巴的解读。
误读,本来便是读诗的一部分。间隔产生美,相信误读也是。
第一集:《江雪》:时空的艺术冬去春来。第一个,让我们从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少年时,只会从直接从字面上去读这首诗,非常大略粗暴:
有山有鸟,有路没人;有舟有我,江上有雪。
老师可能还会给你再加上诗作的背景,什么永贞改造失落败墨客被贬陷入绝望等等……
实在这些都不主要。主要的是,我们要让唐诗读起来更大气,也更有趣——
我对《江雪》一诗的理解是这样的几个层面:
首先,这是首极静的诗;极静。真的静到不能再静。如静态山水画,比《千里江山图》还要静。这是第一层面;
然而,静中有动,表面的安静之下,山与鸟,路与雪,人与舟,各种对话从来没有停滞过。对话便是一种动。所谓风云暗涌,静水深流。静,也是另一种动。极静,大概是一种极动,大概是为了掩蔽某种极动。这是第二个层面。
末了,即第三个层面,整首诗都是时空的艺术,转换的艺术。关于时空的切换,目前我还没有发觉唐诗中,有比《江雪》更奥妙、更浑然天成的。
我现在的读法是,先从后世的古诗古译下手,比拟阅读;辅以今译,放飞想象;末了再拉上外译,放到更伟大的天下范围、时空范围去解读;一首诗的内涵和外延瞬间可扩大N多倍。原来的那首诗也会变得更故意思:
1、《江雪》古译二种《江雪》一诗,古译至少可以有两种古诗,乃至两种以上,只要你有兴趣去发掘:
第一种读法,是对照南宋林升那首著名的七绝: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上面说了《江雪》一诗极静,也极冷;林升这首七绝看上去却极热与极动,二者比拟品读起来便是这样的:
所谓千山,便是山外有山;但是,不怕你山外有山,由于我楼外还有楼。
山,是自然的;楼,是人为的。
山,处处都是冷的,何况是群山下孤舟独钓;楼,却是热的,由于楼阁处有歌伴舞。
我不知道是歌伴着舞,还是舞追着歌;
阵阵暖风中,你醉了,我也醉了:
杭州还是汴州,谁能分清?
江雪,最怕暖风来袭。由于易被溶解;
钓翁,不喜游人靠近。由于怕鱼受惊。
然而,这个林升笔触极热,心里却是同样的极冷,不逊于柳宗元:
暖风之外,亦可以独钓,游民气态,追慕钓翁——
谁像寒江前的你,独钓着雪:
钓雪还是钓鱼,谁又能分清?
同样的错觉,不一样的错觉,超过500年,令人拍桌赞叹。
另一个古译读法,也是来自南宋的古诗。没办法,宋诗是唐诗的第一知音。
只是比较林升的讽刺诗,它稍眇小众一点,小资一点。也,更有趣一点点。
对,便是陆游那首著名的七律《游山西村落》,也可以拿来解读《江雪》:
莫笑田舍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落。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打门。
比较柳宗元的《江雪》,寒江独钓,极为生僻,也极为复苏:由于没有路,既没有出路,也没有归途。于是独钓,是唯一的选择。复苏,是唯一的出路。
陆游的《游山西村落》,却非常生活化非常随缘的:
丰年好酒好菜一大桌,还有一群好朋友,真是暖到了极致有木有?且,这种暖,较之杭州小朝廷醉生梦去世的暖,是不是更有正当性?
都说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同样是墨客,狂欢之后,总会走上同一条路:果真,墨客在酒后出门闲逛,一个人找不到归路和前路,只好停下来感慨一声:
山重水复疑无路。
一句千古绝唱由此出身。
但这句,真的说的是山和水吗?作为一代抗金英雄爱国墨客,陆游何尝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乃至更悲催:陆游连婚姻都不能自己做主,末了被迫与爱妻唐婉分离——从个人生活到家国大业,他何尝有过出路?
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是真无路。早就无路了。
千年以来,中国文人什么时候有过出路?
有的只是歧路。以是只能“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屈原渊明太白就不多说了,有路就不会有寻不到的桃花源了。光看看和陆游同在宋朝的东坡就知道:空负三代宰相之才,却是被流放的生平。
宋诗当然比不上唐诗(宋词可以勉强比肩一下),陆游的诗作,放在宋朝已经是顶尖的存在,然而在并非唐朝顶尖的柳宗元的代表作面前,境界依然高下立判:
总体来说,唐诗在叙事的节奏上把握是非常好的,好到什么程度?懵懂的程度。懵懂,才耐人寻味。不像宋诗那么直白。太直白就少了些许韵味和回味。有些唐诗,你大概你一辈子也没读懂,或者说一贯读得很懵懂;没紧要,并不影响你对唐诗的学习激情亲切。
单说刚刚陆游一句疑无路,固然是千古绝唱,可不免着了痕迹;
《江雪》诗里可有一个字提到出路么?
完备没有。但你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这么回事。
但宋朝较之唐朝,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个中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什么?
市民生活的建立。
所谓大唐盛世,听听也就好了:唐朝公民的生活并不自由。谈不上有多快乐。至少没有宋朝快乐。你去看看王小波的长篇小说《探求无双》就知道,长安城里处处是宵禁和牵制。而从宋朝破天荒地取消宵禁开始,公民群众的娱乐生活才得到极大的开释和张扬。墨客也不例外,于是东坡可以在被流放的路上创造东坡肉,一个人自娱自乐。
也便是说,排解的办法,可以很精彩多样,不再仅限于钓鱼。
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也是:钓鱼这个古老的娱乐,从姜子牙开始,到柳宗元,再到陆放翁的话,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了,2000年前的古董肯定好,2000年前的娱乐,你不以为也太老气了点么?
从北宋到南宋,陆游接过了东坡的衣钵。二人恰好也是宋诗谁第一的紧张争议人选。
同样具备《江雪》的情怀,从《游山西村落》看,墨客无疑是乐不雅观的、极为接地气的:
由于有了酒肉欢娱来打底?反正,短暂的忐忑后,墨客的精神很快就放松起来:
山水有相逢,绝境可重生。
靠什么重生?对,便是前辈传承下来的,孤舟独钓寒江雪的那份执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落。
无路不怕。
可以有村落。
陆游诗末了一句“柱杖无时夜打门”,也非常好。
打门,便是叩问。很随意的一种叩问。
问村落野山民。问道村落野山民。
都说庄子论道,道在屎尿。问道,同样可以如此操作(不知算不算骚操作)。诗到此处,放翁不觉间已和前辈柳宗元达成了惊人的默契。
无路,便是最好的出路。
无路?前村落,便是最好的归宿。
2、《江雪》今译二种我们上面说了第二个层面,《江雪》一诗,并非一味地静,静到底。不是这样的。这便是中国的哲学,不会一根筋到底,相反,《江雪》是静中有动的,四句诗中,险些每一句都藏着各种对话。这个可能连续用古诗翻译不了,只能来个《江雪》今译。我想至少也可以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当代诗歌版的解读,是否可以是这样的——
看山。
山外有山,
山,闭幕了鸟的探索;
问路。
大雪无痕,
雪,凝固了我的追问。
雪,是唯一的行人,
在自由飘荡。
江,也为之打冷颤,
冻结了流淌。
舟,是末了的游鱼,
钓竿在微笑。
对。如果要对《江雪》今译,便是这样:
山,是闭幕者。也是引路人。
只要你能听懂山语。
人,是失落路人,也是寻路人。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
钓竿,则是一种不去世的精神物语,寄托着我们和天下的心灵对话。
忽然想起之前看的老电影《东邪西毒》:今译除了当代诗的版本,还可以有当代电影版——请看张国荣的这段台词:
每个人都会经由这个阶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见告他,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创造没什么特殊。
——说这段话的人(欧阳锋。不同于原著小说的西毒),显然已经翻超越万水千山,才知道山外有山,山外无路:每座山都是那样的存在,没有差异。
山既然没有差异;那有没有路,也没有差异。
但以上都不主要的,主要的是,“我很想见告他”,这6个字——
对,这6个字,才是这段台词的精华:
当你看到,他和你一样,找不到出路了,心里是否会释然一些?乃至一反常态地激情亲切相邀:朋友,一起坐下来喝杯酒吧?
我很想见告他,解释至少有两个人,只管处境不变,是否比一个人在山中垂钓好一些?
这个,可能也是《江雪》今译的最负能量版。或者是低配版。呵呵。
3、《江雪》外译
柳宗元不会想到,千年之后,他还有个穿越时空的心腹,在太平洋彼岸。对,便是18世纪的美国人梭罗。历千年来无数前辈的酝酿,到梭罗,终于将垂钓精神继续到家。
且,梭罗不是一样平常的垂钓者,垂钓之余,他更把时空艺术演绎到了极致。
他在《瓦尔登湖》里这样写道:
“韶光,是供我垂钓的河流。”
一个“供”字,境界全出。尽得风骚,挥洒自如。仿佛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韶光,是供我垂钓的河流。”
从韶光完美切换到空间。毫无痕迹。《江雪》则是从空间的伸展,切换到韶光的凝固。
伟大的心灵,总是随意马虎有相似的遭遇。于是,随意马虎殊途同归。
“韶光,是供我垂钓的河流。”——
只此一句,梭罗就足以将读者诸君们技能性击倒。且,是从灵魂层面、各个层面击倒。
只此一句,我相信足以让柳宗元引为心腹,并如欧阳修遭遇苏东坡那样,感叹后生可畏。
只此一句,我认为足以让梭罗跻身美国史上最伟大的墨客行列。只管梭罗没有写过诗。
藉着梭罗的名句,我才彻底明白,《江雪》一诗真正的逻辑构造是这样的:
你可以千山鸟飞绝,何妨我孤舟蓑笠翁;你可以万径人踪灭,我索性独钓寒江雪。
对,便是这样一种心灵问答式的。
江南园林的一大奥妙是移步换景。实在,换景不如换心,换景更要换心!
换心才是最高境界!
写诗与造园,根本便是相通的。
《江雪》一诗,从空间到韶光,柳大墨客的转换不动声色,奥妙如此!
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墨客,便是这样大雪无痕,大巧不工!
韶光在哪里?韶光在我心。
大气如梭罗,见告我们,韶光不过是一条河。河水冻结,只是一时。我也不用钓竿,由于钓竿就在我手中、心中,随时可启用;就像侠客人剑合一;就像车手人车合一。
是的,或许我们都做不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却,可以做自己韶光的主宰。
做自己心灵的主宰。
哪怕,只有一瞬间。
让我们连续看、连续感想熏染梭罗的声音和想象力——
“我从中取水,却同时创造了河底的淤沙,意识到它是如何清浅。它涓细的脉流漫过,但留下了永恒。我乐意啜饮更深的溪水;
可爱如梭罗,见告我们河底下除了水,还有什么。生活永久泥沙俱下,如鱼饮水心里有数。实在泥沙下还有石头,熠熠闪光的石头,照亮前方水中的浮游。
“那就在天空中垂钓吧,天空的河底都是星辰做成的卵石。”
瑰丽如梭罗,飞扬如梭罗。他见告我们,到处都是钓鱼台,只要你抬开始来:从江畔到天空,都是你的垂钓场。天空,只是冻结了无数星辰的倒挂的河流。
一首《江雪》,寥寥20字,问世千年后,依然可以被中外众人用不同的办法诠释着、演绎着,致敬着……仿佛是唐诗最好的代言人。而每一次解读,彷佛都有惊喜与收成。
不单单是这一首《江雪》,包括《江雪》在内的诸多唐诗,就像歌德心中“永恒的女性,指引人类上升”。
大概,这便是千年唐诗的不朽魅力吧。
好吧,这是我们飞一样平常的唐诗解读的开篇,从冬开始。
按照时令规律,彷佛更该当从春天开始:春,不是四季乃至天下万物的肇端么?不一定。
为何这么说?请看第二集解读:
《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