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人生该当秉持的最好状态是“物来顺应,物去不留”,无论什么事情来到自己生命中,都坦然的接管,无论是惊与喜,都不会过度的排斥;当这些事物“去”的时候也不过于留恋,比如说人生的名利与富贵,从自己的生命中消逝的时候,也不过于沮丧。
以这样的心态去教化人生,便会有一种通达和顺应,人生因心性平和而升华,以此养心,人生自无祸患。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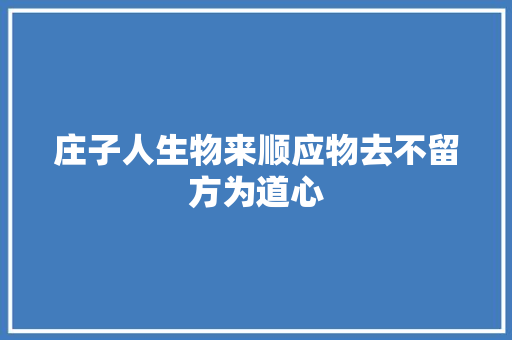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名誉和身体哪个更值得珍惜,身体与财物哪个更主要?你得到名利和损失生命哪一个更有害?过分珍藏必定会造成大量的耗费,丰硕的货藏必定会造成惨重的丢失,以是知足就不会受辱,恰到好处不会有危害,这才能长久生存。
人生知足而适度,自然会有福报,祸患来源于对付物质以及名利过分的贪得,在贪得的过程中一定会违背自然的实质。
但是很多人总会产生一种误解,畏惧名利和富贵来临的同时会带来祸患,便过分去排斥名利和富贵的存在。
实在这是错的,生命的任何物质都是为了做事于人生,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更好,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物质又是极不可或缺的一个事物,以是名利和富贵本身并不会对我们产生侵害,反而会有助于我们的人生。
而真正产生侵害的,是自己对付名利和富贵过度的贪求,以是“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身外之物呢?
便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物来顺应,物去不留”。
人生因努力而精彩,因对付物质的适度拥有而丰硕,以是当生命中因自己的努力而涌现名利与富贵时,欣然的接管,以适度的状态去收受接管,以坦然的心态去拥有,这才是最好的一个人生状态。
如果外物来到自己身边时,自己仍旧过分的往外推脱,这反而阔别了道心的根源。
02
《庄子》之中有这样一番对话:
有一天尧到华这个地方巡游,华地守封疆的人说:“贤人,请接管我的祝福,祝贤人龟龄。”
尧说:“不必了。”
“祝贤人富有。”
尧说:“不必了。”
“祝贤人多男子。”
尧说:“不必了。”
守护封疆的人就奇怪,说:“龟龄、富有和多男子都是人们想得到的,你为什么不肯望得到呢?”
尧说:“多男子会忧虑,富有会麻烦多,龟龄会屈辱多,这三方面不可能用来颐养德行,以是我推辞了。”
守护封疆的人说:“起初我认为你是贤人,但如今只是个君子,天生万民,必定会付与职事,男子多而付与他们一定职事,还有什么忧虑的呢,富有而与人分享,还有什么麻烦的呢?贤人像鹌鹑一样无心求食而随遇而安,如鸟一样翱翔而无一点痕迹,天下太平就跟万物一同永生,天下纷乱就修身养性以空隙。寿延千年而活在世上,离开人间便仙游羽化,驾驭那朵朵白云,直到天与地相接的地方,龟龄、富有、多男子导致的多辱、多事、多惧都不会降临于我,身体也不会遭殃,还有什么屈辱的呢?”
这一番对话之中,庄子通过了“华地守封疆人”讲述世俗之人对付多子、富有、龟龄的精确态度。
道家思想中认为福祸相依,虽然有些事情会对人生产生祸患,对付德行造成残害,但是不可以把来到面前的龟龄、富贵、多子当做包袱,由于这会违背了道心,顺应接管,坦然化之,才是聪慧。
犹如世俗之人修道,真正的“道”,不一定要自命清高的隐居山林才能得到,身处富贵之中,生平步入仕途同样有一种道心之境。
王阳明生平仕途,指挥作战百战百胜,苏轼生平仕途,在末了垂暮之年才得以辞官,但是两人在道家成绩都非同平凡,一个诗词流传千古,一个创立阳明心学。
对付他们来说,哪一种富贵是包袱呢?
外物来则顺应,但是不过于贪求,外物去则不挽留,更不会“厚藏”,这便是道心,这更是境界。
文|国学书舍
品读国学聪慧,感想熏染古人文化,体悟不一样的天下,瞥见不一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