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管这一段韶光,早有预感,一种不祥、难过、不舍、惋惜的感情一贯萦绕着我,但这一刻还是来了。12月15日凌晨3点40分,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翻译家、散文家、出版家,我国法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人物,为中国读者留下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圣爱克·苏佩里等名字,第一个把萨特比较全面系统地先容来中国的中国学者,末了一部翻译作品是深受中国小读者喜好的《小王子》的翻译家,乃至为自己末了一部作品起好了书名叫《麦场上的遗穗》的作者,自喻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的柳鸣九师长西席,在北京同仁医院,收住了他那纵驰中西文坛七十载、关爱老少读者几代人的目光,享年88岁。
柳师长西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用他自己的话说,“写的和译的有四五十种吧,编选的和主编的图书有500多册吧。”他家里的书房,堪称他生平成果的展览会。更主要的是,柳师长西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从他身上能看到一位中国作家对文学奇迹的无限追求,一位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不懈坚持,一位传统文人的人文情怀、人文精神和文学义务、文化担当。走近柳鸣九师长西席,才知道什么叫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心无旁骛,什么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什么叫寒窗不知苦、嚼字自觉甜,什么叫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灵魂。
2022年12月14日中午时分,是我和柳师长西席互换的末了时候,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读秒阶段。疫情阻断了我对老人的探视,但这一段韶光互动仍旧频繁。在视频里,病笃之际的柳师长西席听到他家人说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声音了,竟然逐步地睁开了眼睛、动了动嘴,脸上有了生动。今年9月7日,我和社科院卖力老干部事情的同道在做好严格防护事情的情形下去看他,已是行将就木的他依然那么倔强、那么顽强、那么倔强,虽然口不能言,但对我的声音——该当是他生命末了光阴里最熟习的男声依然熟习,每次听到,必有反应。我见告老人家,您要倔强,等康复了,我来接您回家。他的家,是一座书城,那是他最感宁静、温馨的地方。他动弹起来,彷佛在点头。
11月17日,由于照顾护士未便利,家人希望能转一家离家近、家人能昼夜陪伴的医院,我联系北京市和东城区的几位朋友,一听柳师长西席的名字大家都肃然起敬、激情亲切帮忙,但都得稍等。终于,柳师长西席等不起了。所幸的是,末了一天,女儿、外孙女和我们守在他的身边,他的远行之舟是在亲人们的呼唤中拜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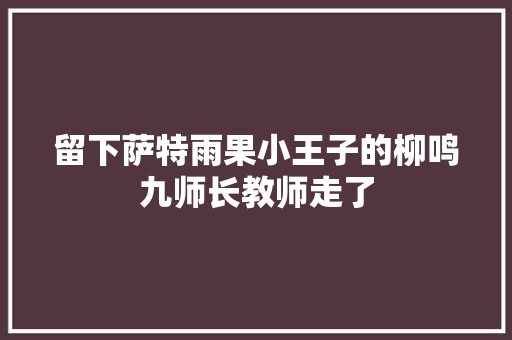
屈服柳师长西席的心愿,我们商量,拟将师长西席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北京某处,一个碧波荡漾、绿意氤氲的潭边,那是他最喜好的一处绿色,适宜安顿身心;一份回到湖南家乡,那里是他梦想的出发点,是他人生的归宿;一份送到美国,与儿子的骨灰在一起,儿子英年早逝,是他作为父亲永久的痛,生不能陪去世相伴,但愿这多少能抚慰他痛楚半生的心灵。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声闻于天”。柳鸣九驾鹤西行,留声于世,温润众生。愿师长西席一起走好,在天国,连续垒他的书城天下,只是,只是别再太累了……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
作为法国20世纪最主要的哲学家、文学家之一的萨特没有想到,在他1980年4月15日逝世之后,他在西方略显寂寥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萨特走红中国,得感谢一位今年已84岁高龄的中国学者——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的大家柳鸣九师长西席。
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柳师长西席以独到而富有前瞻的眼力,看到萨特“存在主义”的哲学代价,看到萨特哲学在中国的社会代价。1980年,柳鸣九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的《读书》杂志7月号揭橥《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他大声疾呼:“萨特是属于天下进步人类的”“我们不能谢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份精神遗产,这一份遗产该当为无产阶级所继续,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续,由无产阶级来科学地加以剖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一呼声如石破天惊,让中国社会的目光投向了塞纳河边的那位法国学者。
1981年,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出版、1985年重版。“萨特”走红中国,是改革开放之后一个显著性的文化事宜,对外文化互换中一个标志性的文化征象,在中国社会的思想星空划出了一道绚彩。柳鸣九师长西席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一把“法国钥匙”能打开千万把“中国锁”,是由于这把钥匙可以为人类所共有、对中国有启迪。萨特的“自我选择”哲学是对个体意识的承认、尊重、强调,契合了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在个体精神和主体意识上的甦醒。各处的“小确幸”“小浪漫”“小梦想”“小人设”,让中国社会充满活气。
纵不雅观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如果没有个体意识的渐醒、个性特色的张扬、个人代价的实现,就不会有主人翁意识、主不雅观能动性、公民主体地位、公民权柄的被尊重,也不会有“我的青春我做主”“有体面的劳动、有肃静的生活”,更不会有“公民的梦”“中国梦”这些热词的呈现。没有个体的设计就没有社会的构想,没有个人的梦想就没有民族的梦想,没有个体意识的唤醒就没有国家精神的重构。
不仅是引荐者,还是质疑者、批评者
作为一个有先见、远见、深见的学者,柳鸣九在得当的机遇做了一件有先见、远见、深见的事情,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推销法国“萨特牌”钥匙的中国代理。
但必须承认,柳鸣九对萨特的理解超过一样平常人。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一把“中国式钥匙”,他让我们知道除了物欲、功利,还有一种存在叫“精神”;他让我们知道了要在生动实践和火热生活中实现自我的代价,完成人生的设计,不要当社会的察看犹豫者、时期的冷漠者。
柳鸣九不仅是满腔热心的引荐者,还是演习有素的质疑者、充满锐气的批评者。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日丹诺夫曾做过一个政治报告,认为欧美文化是“反动、腐烂和颓废”的,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骗子、泼皮、色情狂和娼妓”。这种“日丹诺夫论断”长期以来主导着前苏联的文化领域,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对欧美文学的态度,如果不对之进行彻底批驳,外国文学就很难走进中国,人类文明的互换互鉴便是一句空话。
经由数月的充分准备,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师长西席的支持下,柳鸣九于1979年在第一次全国外国文学方案会议上,做了一个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目就叫《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他站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的态度上,对长期霸占主导地位的“日丹诺夫论断”发起剧烈批驳,外国文学所随后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组织起系列谈论,对柳鸣九的不雅观点进行呼应,起到了冲破坚冰、解放思想的浸染。这一套“组合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鸣九又是一位寻衅者、拓荒者、清道夫、建树者。
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
柳鸣九师长西席长期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享有最高学术称号“终生名誉学部委员”,无疑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领军人物。他主持的许多事情、创造的许多成果具有开拓性、独创性和打破性意义。他研究雨果、左拉、蒙田、卢梭、加缪、司汤达、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萨特等的文章,翻译雨果、莫泊桑、都德、梅里美、加缪、圣爱克·苏佩里等的作品,成为一个个文化标志,有的乃至产生了“征象级”影响。
柳鸣九有自己的文化理念,那便是“为丰富社会的人文书架而作贡献”。他坚信只管这个天下芸芸众生利来利往、名来名去,但“人文书架”依然是国人“精神骨骼”的支撑;他笃信这个速朽的时期、速忘的时期、速食的时期,要拂却的是虚浮,能沉淀的是经典,仍旧是一个须要经典、须要人文精神的时期。于是,他像一头费力的老黄牛,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艺理论、文学编著四大领域耕耘播种,既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欢欣,也造诣了自己作为著作家、翻译家、研究家、编辑家的威信地位。
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外国文学经典》丛书、《雨果文集》(20卷)等,翻译的《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都德短篇小说选》、加缪的《局外人》等相继出版、重版,15卷本、600多万字的《柳鸣九文集》问世,各种独著、编著、译著达三四百种,各种文集、选本、丛刊、丛书门类繁多,堆起来,像山。书山字海、经典迭出,柳鸣九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著作“超”身了。每每有人以此阿谀柳鸣九,这位谦善、自傲倔强的湖南人会说:“我是一个矮个子。”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
拿起笔来是国王,放下笔来是草民,这大概是柳鸣九的人生境界。柳鸣九思维生动,像一架开启的全天候雷达,一直地迁徙改变、扫描、捕捉旗子暗记。他关心时局、关心社会、关心学界,有一颗匡时济世之心。他评价自己是“思想不规范,但言行不出格”,我认为他是“出格”但不“出轨”,像一个写羊毫字的小学生,偶尔把点横撇捺胳膊腿儿伸到米字格外面,是正常征象,但还是字正体端、棱角分明,不写错字。
柳鸣九有思想、有锋芒,敢于建树、敢于寻衅,却不是一个争荣邀宠、贪功占利的人,当然他也很敏感而且很有肃静,傲骨铮铮,风骨凛凛,守护着自己的学术王国,守卫着自己的庄稼、收成,呵护着自己的秧苗、新苗,坚守着自己为人的准则、底线,不容唾弃、践踏。
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轻骨头”决不是文化的实质,文化人的骨头最硬、最重。有风骨的文化是有力量的思想,文化的风骨保有着文化的本色。文人的代价在于文化的贡献,柳鸣九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样本。
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生活中的柳鸣九是一位闲淡隐逸之士,一个名利淡泊、与世无争、寂静有为的谦谦君子、优雅绅士,好用“阁下”尊称对方,用辞谦和讲究,平和中有聪慧,平淡中有深意,令人回味和咀嚼。有一句公益广告词说得好,“30度,45度,60度,90度……这不是水的温度,是低头的角度”。柳鸣九不是能向任何人都鞠躬90度的人,乃至也不一定能弯到60度,但决不是微倾一下敷衍客套搪塞之人,45—60度是他礼敬他人的常态。
柳鸣九好用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会思想的芦苇”来自喻,薄弱却有自重。他喜不形于色,怒不表于言,从不蹈之舞之、张之狂之,碰着搪突、轻薄,耄耋之年的他最大反抗和愤怒常常是:“再也不给你们写稿了”或者“这是我给你的末了一篇稿子”。在措辞暴力泛滥的本日,这种“柳式反抗”显得多么苍白绵软而又文质彬彬,但有力量。
看重亲情,与保姆一家情同家人
柳鸣九十分看重亲情,曾用饱蘸情绪的笔墨记述了作为一位父亲对儿子、一位祖父对孙女的爱恋深情。在文中他如过电影一样平常回放着儿子柳涤非从呱呱坠地到远赴美国求学创业、成家立业的过程,不无遗憾地讲述儿子十年未归、离多聚少的思念和顾虑,不无痛楚地倾诉了老年失落子的心境,以及反复追忆远在美国的儿子留给人间间的末了一句话,是见告前来的急救车救护职员:“不要开灯,不要拉警报,我的女儿睡着了。”绵绵眷眷、凄悲惨切的思念,白发老父笔悼黑发亲子,该是人间最悲苦的心境了,而柳鸣九一句写纪念文章“是为了给小孙女留一个她爸爸的影象”,让人读到一位老人的内心强大与高尚,令人濡目。
儿子走了,为柳鸣九留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女,那是二心坎深处的柳暗花明。2006年,由柳鸣九翻译的《小王子》出版,扉页上留下一行字:“为小孙女艾玛而译”,简洁却深情。10年后,《小王子》以新面孔涌如今读者视野,是老祖父柳鸣九翻译、小孙女柳一村落插画的共同作品,老祖父特地写代序、作后记、附散文,穿靴戴帽,隆重包装,有满满的欣慰、淡淡的遗憾和闪闪的泪光,情透纸背,心在泪中。
柳鸣九有其余一个孙女,虽然没有血缘。她叫晶晶,是安徽保姆小慧夫妇的女儿。小慧在柳家做事了40年,无微不至地照顾柳鸣九师长西席和他的夫人、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朱虹师长西席,情同一家人。小慧在柳师长西席、朱老师家结婚,晶晶在柳家出生、发展,在柳师长西席帮助下在北京读书,在柳师长西席帮助下赴美国的大学攻读生物医学专业。柳师长西席乃至留下遗嘱,百年之后将屋子赠送小慧一家。
淡泊的贰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生
每一次与柳师长西席会面,都是心灵的滋养。有的时候是我主动去探望,提前预约,不敢打乱了他的作息韶光;有的时候是他打电话来约,问“阁下是否有空”。有一次我提前到了,师长西席见面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为没有来得及刮胡子而表示歉意。
师长西席鹤发童颜,一脸的儒雅、和蔼、慈祥,聊时政,讲文化,谈写作,说人事,思维迅敏而严密;深居简出,粗茶淡饭,统统清清爽爽、简大略单、从从容容,是师长西席的生活常态;家徒四壁,唯有书墙,饰以小孙女的画作,一台电脑或闪现着字符或放着舒缓的轻音乐,如舒曼的《梦幻曲》等,是师长西席的生活场景。
柳师长西席除了用饭、睡觉、闲步,便是伏案读写,甘坐冷板凳,长年磨剑,笔耕不辍,在方块汉字和法笔墨母间垒砌文学的高楼和文化的桥梁,让我想起刘禹锡的《陋室铭》,想起鲁迅师长西席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柳师长西席乃至常常门窗不启、窗帘紧闭,像是恐怕满屋的书喷鼻香、才华、灵感从哪个门缝窗隙中溜走,自己却在上午时分溜进楼后的小院里,走几步。
师长西席的15卷本《柳鸣九文集》出版后,他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亲笔写下一言相赠,且各不相同,如“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思想不规范、言行不出格的老朽一个”“伏尔泰曰:‘耕种你们自己的园地要紧’,我是此言的信奉者,执着与超脱、自律与自私,皆出于此”“以诚善为本,以礼义相待,致成忘年莫逆之交,柳老头平生一大幸事也”,等等,统共15句,既是人生感悟,更是勉励见教。师长西席像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
那年,陪师长西席于桃之夭夭的三月,在北京的明城墙根下晒太阳、过“桃花节”;偶尔,陪师长西席到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听音乐;偶尔,陪师长西席在他家楼下的肥牛火锅城用饭,给他一个买单的机会,他会点上一桌让你吃不完的菜然后让你吃不完兜着走;有时候他点名去崇文门国瑞城的“汉口码头”酒家,点吃湖南人、湖北人都喜好的红烧甲鱼;有时候他在家铺满一桌马克西姆餐厅外卖的西点,或者外卖的红烧甲鱼。实在我知道,年事已高,血糖也高,牙齿稀松,吃不了两口的师长西席,只想看着我吃个高兴。
崇高者最寂寞,思想者最孤独。淡泊中的师长西席却并不寂寞孤独,他的心中有着万千丘壑、百态人生,他的笔下鲜活着那么多名人巨擘和灵动的思想,他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的研究者、读者在研习。那次,陪师长西席在国家大剧院听音乐,后座一位中学生得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竟然便是教材中法国名著的翻译者,愉快不已。那次,推着轮椅中的师长西席徜徉在西西弗书店,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正在购买师长西席翻译的《小王子》,轮到师长西席愉快不已了。
坐看云卷云舒,静听花着花谢,远不雅观日出日落,近瞰潮起潮降,柳鸣九师长西席像那个遨游在七颗星球之间的“小王子”,既费力,又超越。法国作家都德的《末了一课》中,那位韩麦尔老师告诫他的学生们说,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措辞,“就彷佛拿着一把……钥匙”。
萨特是一把钥匙,柳鸣九也是一把钥匙。你须要或者不须要,它都在那儿。
(本文为应柳鸣九师长西席之约,刘汉俊为他的《朋侪对话录》一书而作的序,因版面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