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能雄/文
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交谈几句后,会根据对方的口音讯问他是不是某个地方的人,这是由方言形成带有地方特色的“乡音”。我们从牙牙学语之时就从父母那里接管方言的教诲,往后不管学了何种措辞,在说话的时候总会带有家乡的腔调,就如身上的一个印记,一辈子也抹不去。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泰顺人,在上学读书的时候,有些村落庄老西席有时会用泰顺方言来讲课。从小到大,无论是在家中村落里,还是在学校街市,我都受到了泰顺纯洁方言的熏陶。
终年夜后,我和许多老乡一样出门在外,只假如有泰顺人的地方,我们总习气性地用老家方言来互换。我们能听懂当地人的措辞,当地人却很难听明白我们话中讲的是什么意思,乃至有些人说:“我听你们说话,就如听外语一样,一句也听不懂。”其他地方的人很难听懂泰顺话,并不能解释泰顺方言是个异类,是因泰顺人保留了古汉语的发言习气。泰顺话有些字词的发音与普通话发音差别很大,有些词语采取古汉语的利用方法。比如我们煮饭用的“锅”,古人以“鼎”作为烹饪用具,泰顺人直到本日仍用“鼎”字来称饭锅;我们捆东西用的“绳”,古人称之为“索”,泰顺方言中仍称绳子为“索”。试想,当泰顺人说用鼎来煮饭或者用索来捆东西的时候,别人怎能一下子反应过来呢?
图为泰顺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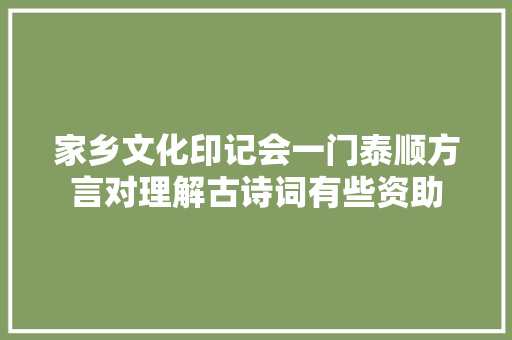
在我看来,泰顺方言不但不是另类,反而是措辞宝库中的文化宝贝。在泰顺历史上曾有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一次是唐代末年,另一次是北宋末年,两次都是北方发生战乱,很多人携妻挈子南迁至泰顺,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北宋末年的这一次人口迁入,对泰顺文化起到极其深远的影响,很多原来是中原世家大族的文人士大夫在泰顺扎根,耕读传家,泰顺迎来了文风最壮盛的期间,境内人才辈出,仅南宋一朝就约有文武进士七十人。直到本日,泰顺还处处可见宋代文化留下的印记,如泰顺廊桥、药发木偶、木偶戏等,都是传承自宋代的文化遗产。
图为泰顺风景
而泰顺方言除了保留当地土话的一些特色之外,也受到中原古汉语以及吴语等语系的影响。我是个诗词爱好者,就以诗词古韵来印证泰顺方言与中原语系之间的联系。写古诗词的人紧张以“平水韵”(古韵)来做工具书,平水韵是根据唐宋律诗绝句的用韵情形而编成的韵书。所谓诗词押韵,便是有些诗句的末了一字须要用谐音字,同一个韵部里的所有韵字同音或者近音。可是,我们本日查看平水韵,创造很多韵部中的字并不谐音,是两种完备不同的韵母。
难道是古人编撰韵书的时候弄错了?不是,《平水韵》经由几代人的总结归类,始终都以韵字谐音作为韵部归类的标准。有些韵部里的字我们本日读起来不谐音,在唐宋期间的发音却是附近的,当时的墨客才会用这些韵写诗。古代汉语与当代汉语的发音差异,使得有些人开始疑惑平水韵在现阶段的实用性,有些诗词学者以普通话读音为根本,实施诗韵改革,重新划分了韵部,称为“中华新韵”(今韵)。很多人环绕着平水韵的存与废的问题争议不断,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平水韵,在诗词创作中首选平水韵,诗词作为一门古老的文化,还是带一些古韵更好。
图为泰顺风景
平水韵被某些人质疑,是由于他们以普通话的标准来剖断韵字是否谐音。两个同韵部里发音差别较大的汉字,在杜甫苏东坡的时期却可能音韵和谐;两个同音或近音的汉字,在唐宋期间的读音可能并不靠近。而那些平水韵中有争议的韵字,我用泰顺方言来读,很多都是谐音,这解释泰顺方言保留了古语古韵,有时候我以为:会一门泰顺方言,对理解古诗词有些帮助。下面我就以古人诗作举几个例子:
一、以泰顺方言的发音来理解古代诗词中有争议的韵脚。
1、以杜牧的《山行》来理解平水韵中“六麻”韵部。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仲春花。
这首诗很多人耳熟能详,爱好书法的人可能都缮写过几百遍。诗中的韵脚是“斜”、“家”、“花”,这是“六麻”韵部中的字。用普通话来朗读诗句,“家”和“花”是谐音,两个字用来押韵该当是毫无疑义的。而“斜”字拼音是“xie”,读起来与“家”和“花”字并不谐音。杜牧是著名墨客,自然不会犯这种不押韵的低级缺点,实在,在唐代“斜”字与“家”、“花”的发音是附近的,在我们泰顺方言里仍旧保留着古音,“斜”字发音近似于“qia”。
为了描述得更详细些,我再举几个“六麻”部中古今异音的韵字,如“车”字当代汉语拼音是“che”,泰顺方言里读音近似于“qia”;“遮”字当代汉语拼音是“zhe”,泰顺方言的读音近似于“jia”;“蛇”字当代汉语拼音是“she”,泰顺方言的读音近似于“xia”。我们会创造用普通话读“斜”、“车”、“遮”、“蛇”这几个字时,韵母都不是“a”,而用泰顺方言来念这些字却都是发音附近的。由此可知,不是古人编错了韵部,而是后来读音发生了变革。
图为泰顺风景
2、以温庭筠的《苏武庙》来理解平水韵中的“一先”韵部。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诗中的“前”、“然”、“烟”、“年”、“川”五字是平水韵中“一先”韵部中的字。以普通话来朗诵这首诗,“前”、“烟”、“年”三字声音附近,“然”、“川”二字则与其余三字发音差别很大。在泰顺方言里,“然”字的发音近似于“xian”(音同“先”字),“川”字发音近似于“quan”(音同“全”字)。我在“一先”韵部中还可以找到其他古今异音的字,如“蝉”字当代汉语拼音是“chan”,而泰顺方言中的“蝉”字,发音近似于“xian”;“扇”字当代汉语拼音是“shan”,而泰顺方言中的“扇”字,发音近似于“xian”;“传”字当代汉语拼音是“chuan”,而泰顺方言中的“传”字,发音近似于“quan”。
以上我列举的几个汉字,如果以普通话来读,与“一先”部中的很多字发音都有差异,以泰顺方言来读则基本符合同韵部同音近音的哀求。今人所编的《中华新韵》,把韵母为(an、ian、uan、üan)的字全部归纳入“八寒”韵部中,这种归集方法有些笼统,韵部过于宽泛,很多字并不谐音,如“先”字和“寒”字的普通话发音明显不同。而平水韵则把韵部分得很细,以谐音作为紧张条件,细分成“上平十四寒”、“上平十五删”、“上平一先”、“下平十三覃”、“下平十四盐”、“下平十五咸”六个韵部,韵部变窄了,更能磨练作诗之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3、以杜甫的《又呈吴郎》来理解平水韵中的“十一真”韵部。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怖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搜聚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中的“邻”、“人”、“亲”、“真”、“巾”等字属于平水韵中“十一真”韵部。我们用普通话来朗读此诗,会创造“邻”、“亲”、“巾”是谐音,都有韵母“in”,而“人”和“真”两字的韵母为“en”,与前面三字的发音差异较大。而在泰顺方言中,“人”字发音近似于“yin”(音同“因”字),“真”字发音近似于“jin”,与前面三字发音都很靠近。我在“十一真”韵部中还可以找到几个古今异音的字,如“仁”字当代汉语拼音为“ren”,而泰顺方言发音近似于“yin”;“申”字当代汉语拼音为“shen”,而泰顺方言发音近似于“xin”;“轮”字当代汉语拼音为“lun”,而泰顺方言发音近似于“lin”。用泰顺话来读“十一真”中的所有韵字,声音基本上都是附近的。
4、以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来理解平水韵中的“十三元”韵部。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薄暮。
诗中的“原”、“昏”字是平水韵中“十三元”韵部中的字。“原”字当代汉语拼音为“yuan”,“昏”字当代汉语拼音为“hun”,两个字怎么读都不会谐音。“十三元”是争议非常大的一个韵部,在几十个韵字中就存在多种读音,让人无法理解古人为什么会把这些字归集到一起。在泰顺方言里“原”、“元”、“猿”、“温”这些同韵部的字的发音都近似于“wen”或“wun”,总的来说还是与“昏”字谐音的。
以上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中的韵脚“流”字和“楼”字的当代汉语发音差异很大,而泰顺方言中的“楼”和“流”都发“lao”音。如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期”和“儿”字当代汉语拼音各自是“qi”、“er”,读起来声音差异很大,而泰顺方言中的“儿”字发音近似于“ni”(音同“你”字),与“期”字是谐音。
二、以泰顺方言的发音来理解一些字的入声读法。
唐诗宋词之以是有着耐久不衰的魅力,缘故原由之一是它有如音乐般的格律,一首诗中有平有仄,读起来抑扬抑扬。平声字相对清亮,悠扬绵长,仄声字相对低沉,轻微短匆匆。在当代汉语中,以阴平、阳平为平声,即汉字音调中的第一声、第二声;以上声、去声为仄声,即汉字音调中的第三声、第四声。而在古代汉语等分为“平上去入”四声,个中“上去入”三声归入到仄声中,普通话中没有入声,而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还保留着古汉语的入声读法,泰顺方言便是个中之一。
图为泰顺风景
就以我们常用的数字来举例吧,“一”、“七”、“八”三个字在当代汉语中都是第一声阴平,读起来声音高昂悠长,按理该当是平声。而在平水韵(古韵)中把这三个字归集入仄声中,是由于古人读这些字是入声。明代释真空在《篇韵贯珠集·玉钥匙歌诀》中言:“入声短匆匆急收藏”,用泰顺方音念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也是短匆匆微弱,一发即收,这正是古汉语中的入声字读法,与普通话的读法比较,无论是音调还是音质都有很大差异。我以泰顺方言的腔调来读,才理解古人为什么会把“一”、“七”、“八”等字剖断为仄声,在创作格律诗词的时候,我也把这三个字当做仄声韵来利用。
三、以泰顺方言来理解古代诗词中一些口语用法。
南宋岳飞曾写过一首诗《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敷,马蹄催趁月明归。”诗中的“特特”这个词语,有些人认为是岳飞骑立时山的马蹄声。但是“特特”二字连着“寻芳”二字就有些不折衷了,由于马蹄声是不会探求芳草的。对“特特”的阐明还有另一种说法,便是“特地、专诚”的意思,岳飞是忙里偷闲,特地到翠微亭欣赏景不雅观。
“特特”意指“特地”,有此一说,但我们在当代书面笔墨中险些不用“特特”这个词。“特特”是古代方言中常用的一个口语,在古文诗词或文言口语小说常常利用。如《红楼梦》中的薛宝钗、薛蟠在讲话的时候就常常用“特特”这个词,薛宝钗有一次对贾宝玉说:“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我不吃他,叫他留着请人送人罢。”讲的是薛蟠得到了一些珍奇美食,特地约请妹妹宝钗品尝。在泰顺方言中至今仍旧利用“特特”二字,发音近似于“die die”,如某人特意约请别人用饭,会说:“我特特(dei dei)来请你食饭。”大多数人在看书或者用普通话互换的时候,能理解“特地”的意思,却未必知道“特特”是何意,而我们泰顺人恰好相反,在用方言交谈的时候,都能听懂“特特”的意思,却不能很快听出“特地”这个词的含义,这是多年来形成的措辞习气。
图为泰顺风景
岳飞生活于文化昌盛的宋代,他诗中的“特特”二字,正是把当时的民间措辞利用到诗句中。由此也可知,泰顺方言至今还保留着宋代人的口语特色,有了这种措辞承续上的上风,就能理解古诗词中一些在今人看来比较生僻的词语含义。
方言是家乡给予每个人的文化印记,唐代贺知章写了一句诗:“幼年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他年少之时就离家外出,客居他乡几十年,名动京华,他晚年返回家乡,两鬓斑白,改变的是容颜,却改不掉乡音。记得我有一次攀登黄山,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拥挤在山间的栈道上,忽然我耳边听到几声泰顺土话,顿时倍感亲切,不用上前讯问,就知道说话之人是老乡了,只以为天下真小,泰顺人的路走得很远。每一种方言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一声乡音,一点印记,融入到每一个人的血脉中。泰顺方言中保留着古汉语的发音习气,对理解和诵读古文诗词有很大帮助,这是一种文化遗产,值得泰顺人一代代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