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人生贵在知去世知生
又是一年芳草生,而时节春分之后近清明。古人的最早的清明节并非敬拜先祖的大节,是古老的火神山神的崇拜,禁火敬神。先秦晋国大臣 介子推 赞助 晋国公子重耳,功成身退,隐居深山,结果晋文公为了见他,纵火烧山,结果酿成介子推被烧去世。晋文公非常惭愧,设立寒食节,禁火追思。这中间也有环保的观点,尤其是仲春雷电增加,随意马虎产生山火,而人们也由于用火不慎,随意马虎发生失火,造成难以承受的丢失,故而寒食节变成了明确的禁火节,在汉朝某些山林多的地区,可以长达一个月,人们不能点火。涵盖了清明节气。
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如此,有的是一天,有的是数天,那么禁火的日子,人们该做些什么呢,提前准备冷食。而此时正是仲春时段,人们纪念介子推,同时也提着祭品,去敬拜自己先人。
寒食日和清明节十分靠近,到了唐朝宋朝,官员的假期,都是寒食清明连给,到了明清两代,清明节就成了敬拜的大节。实际这个时段包括了寒食节清明节前后数天,乃至以清明节为节点的前后一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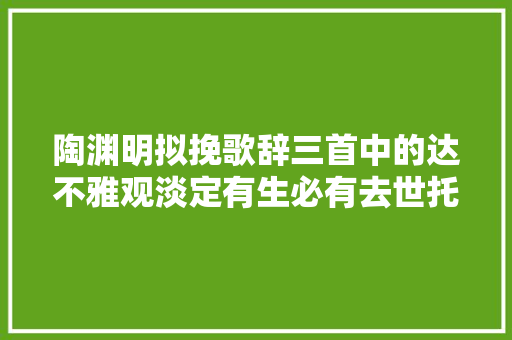
我来谈这些,和陶渊明的拟挽歌词有关联吗?
当然有,由于正是农历的二三月是主要的踏青扫墓敬拜的日子,关于人存亡活的问题,是直接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的。
汉末古诗十九首里“ 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在东风拂动草木的路上旷野行驶,你看到的是无限的春色,还有一座座平缓铺着春草的宅兆土丘,哪怕你此时并非特地去做祭奠,你也会想到“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龟龄考。奄忽随归天。”
何况此时的踏青,很多人一方面是享受山川春色,一方面也以最诚挚纯净的心情敬拜先祖,慎终追远,让春色更有灵魂气息。
汉朝帝王崇尚神仙永生不去世,然而老百姓并非都确信,由于,生老病去世就在身边。虽然也有很多仪式,表达灵魂的永生,欲望肉体羽化而不是糜烂。但是人的去世亡,是生命中的大事,谁能无动于衷?汉朝晚年的战乱,倾覆了帝国的繁荣,大量非正常的去世亡,让人们以为人生的短匆匆,质疑所谓神仙和永恒。
汉末古诗十九首里,多次涌现这样质疑的诗句,“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神仙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等待人生终点的,便是泥土和宅兆。而且在汉末,非正常的去世亡随时到来,让人们在悲哀中更加珍惜相守和快乐。
挽歌,自然是生者给亡故者的悼亡歌曲,每每送行的时候,摇着铃,举着幡,歌唱逝者的生平和生命离开的悲哀。但大多数都是一种投射状态。
晋朝的贵族也有人自己给自己写挽歌,但是估计也是希望自己的悼亡词,比别人的更加富丽贴切,歌功颂德,以让后世纪念。但是这都不如陶渊明。
只有陶渊明的《拟挽歌辞》是站在一种分外的角度,便是我,从去世亡到安葬这一过程。便是人还没有去世亡,体会一把最靠近去世亡的觉得。这是非常分外奇异的视角和状态。
但是正是这样的状态,让我们理解死活,更豁达死活的存在。
未知去世,焉知生。正视去世亡,才能更拥抱生活。
“有生必有去世,早终非命匆匆。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益友抚我哭。
得失落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东晋 · 陶潜 《拟挽歌辞三首 其一 》
陶渊明中年往后在乡间,一定瞥见过多次的葬礼,而且和他交往的,也多还有当地的官员,陶渊明的隐士,是相对他曾经官员的身份来讲,实际他便是当地的士绅或备受尊重的父老,一些主要的活动,必有他的参与。在那些仪式上,每个人都会有代入感,只是陶渊明的更加深邃细腻。如果,我是躺在这里,等待送往宅兆的逝者。
这开头一句就否定了汉朝和民间流传的永生不老之说。
人生,有生,就会有去世亡,如果提前短命,不要埋怨命运的短暂。这里的非命,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非正常逝去,这种逝去让人痛惜,其余一种,分开理解,不要埋怨命运。但是这到底是哪种更贴近陶渊明的想法呢,我乐意解读为,是一种随时而来的意外导致生命的终止。或者他某次是看到的年轻或者壮年人的葬礼吧。
昨天晚上还和你一起说话,同在这人间,而本日早上,大概我和你就分别了,一个在人间,一个在传说中的鬼界,登上了那里的名册。但是这是陶渊明相信灵魂循环吗?这只是死活一个代称。
我的灵魂会散布到哪里呢,只剩下尸首犹如枯朽的木头。
我可以想到娇儿摇着我的身体,要着父亲的拥抱而哭泣,我可以想到好友抚着我的身体痛哭。
但是此时的我,一定什么都不知道了,这统统已经无法知觉。
关于此之后所有事,关于我的平生,荣辱,别人的表达,我是不再知道的。
如果我到了那一田地,如果还有末了的遗憾,一定是以为在这世上,没有喝到足够的酒。
古人费力节俭,是欲望多留粮食在未来,以抵抗饥荒灾害。但是当死活大限到来,你是否定为从前确当心刻苦,是不是都是悲哀?
但是,也不全是。古人节俭,为自己也为子孙谋,只是陶渊明这句很现实,由于人生哪里有那么多知足?恨归恨,但是若活着,也还是会节俭,未足,是人生的常态,乃至便是人生的一定。
不过大难之时,绝境之中的念想,或是真的,比如思念的人,记挂的事。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其二
如果我去世了。我从前没有太饮酒,乃至由于穷苦,很永劫光没有酒喝,但是我去世了,祭品中一定会注满美酒。
那墓碑前的春天的美酒,那美酒上泛着泡沫,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品尝?
所有的菜肴都摆在宅兆前,案台上,亲朋好友都哭在我周围。
但是我便是想说什么,口里发不出声音,我想看什么,眼睛睁不开。
从前在高堂上睡觉,现在长眠在荒草堆里。
这荒草的夜晚,没有活人夜宿,如果你乐意看,那是茫茫夜色,无边阴郁。
去世亡就像早上出门去,但是怎么也回不了家了,站在或行走在永不落幕的夜晚。
实际上,宅兆便是家,从此像夜晚一样阴郁而漫长。
这里写的是生和去世巨大的隔差。照料了第一首的“非命”。意外可能随时来到,生命就像行走在太阳下,随时步入暗夜。那人间间所有的东西不会再有。
古人有事去世如生,便是想象人去世后,一定有个天下和活着一样,人们的敬拜逝者能够收到。但是对付陶渊明来讲,他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逻辑问题,去世是身体和感知的消解,可能不会有地狱也无有天国。永夜和阴郁是唯一能够贴近的表述,犹如就寝和病中的制动。
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写法。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玄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冷落。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去世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其三
如果我去世了。在原野上荒草茫茫,白杨萧萧。
在玄月的寒霜中,人们抬着我,出远郊安葬。
这里四面没有人,有很多宅兆林立。送行的马仰天长啸,秋风吹动着白杨,哗哗作响。
当棺木下葬,宅兆封闭的时候,永久看不到人间的太阳。就算是富贵贤达之人,他们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和结局,而来送行的人,忙竣工作后,会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中,他们的生活还要连续。
只有最亲近的人还有着缠绵的悲痛,很多人已经在嗟叹之外,开始了新的生之歌声了。
去世去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去世去是一件遵照自然的事,去世去最真实的事情,便是你的身体,你的灵魂,融入了这片山林地皮,腐烂和不朽同在啊。
这才是陶渊明要表达的最核心的思想,他的死活不雅观。
有生必有去世,托体同山阿。
很多挽歌写的都是灵魂在天上,那是祝福和美好。但是陶渊明是真实解析死活这个过程,相称的唯物主义,这是非常难得的。
去世亡是人生巨大的死活鸿沟,不能确定的是灵魂和再生,但是可以肯定的便是割断了作为人和这个世上的联系,亲人的声音,歌哭都已经听不见,那些美酒佳肴的敬拜是人间的欲望。去世者长眠。
但是这首诗却又别有一种死活终极的浩大,完全完备回物化然,然而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好的安息吗?虽然可能人之为人的循环并不存在,但是自然是更大的循环和循环。
如果你爱过这个世间,爱着这世间的山水空气,爱着这里的统统,大概不会以为这样的归去会有什么悲哀。从人的知觉来讲,在陶渊明看来是永夜,但是化为了是日然的泥土草木,如何不是一种新生。
本日解读陶渊明的《拟挽歌词》,或者有人会以为凄凉。
但是陶渊明这三首诗的好处,在于正视去世亡的存在,是一种旷达无畏,也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存在的时候,提醒自己人生随时可能会有意外,该当做好关于意外的应对,坦然面对和珍惜生活。
又是一年春草生,我们慎终追远,敬拜先祖,同时也要对死活有着透彻的感知。
人生贵在知去世而知生。
初衣胜雪为你解读诗词中的爱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