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为孔子编定,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指民间乐歌,称为“十五国风”,俗称“国风”,160篇;“雅”是宫廷乐歌,又分“小雅”“大雅”,105篇;“颂”是敬拜乐歌,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40篇。
《诗经》中多次涌现“君子”一词,在不同的场合其指代之人皆不相同。“君子”为何可以代指不同身份地位的人,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诗经》中的“君子”
笔者对《诗经》中有关君子的记载进行了一个大略的梳理,个中关于“君子”的诗共62首,就译注情形来看,《诗经》中君子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天子、诸侯,共10篇,紧张涌如今“雅”部分;二指贵族、官员、富人,同样紧张涌如今“雅”部,少量涌现于“风”部,共34篇;三指情人或丈夫,指情人和丈夫时紧张涌现于“风”部,多为民间诗歌,共计14篇;四指有才有德之人,多涌现于“风”部,仅有5篇。
经由梳理发现,《诗经》中的君子更多的还是指代有身份、地位的贵族,指代情人和丈夫的多是个中的民间诗歌,对付“君子”的道德、才能哀求在《诗经》中表现的并不明显,仅仅只有少量的几篇内容授予了“君子”道德上的含义。一样平常来说,我们谈到“君子”,第一印象便是此人有很高的才情或是道德高尚,为何在《诗经》中,“君子”的可以指代多类人,同时与我们的知识也不尽相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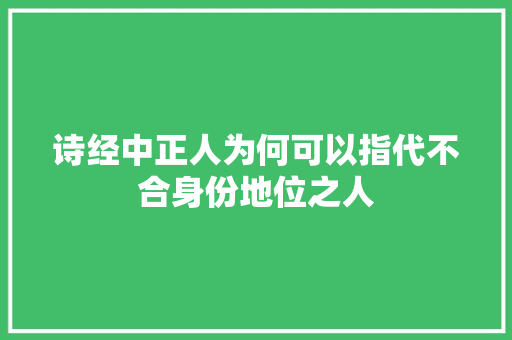
笔者查阅文献理解到,现在我们所理解的“君子的意思”是孔子之后的“君子的意思”,有着强烈的道德含义,《诗经》的时期早于孔子,其所指代的人多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那么,“君子”最初的意义是什么?又是如何演化成本日人们所熟习的“君子”的呢?
“君子”观点的形成
“君子”一词最初涌现于何时,在学术界研究上尚无定论。在“君子”一词最初产生的词源剖析上,研究者普遍认为,“君子”一词最初当是由“君”字与“子”字内在涵义上的领悟而成。
《说文解字》认为“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说文》认为:“尹,治也,从又,握事者也。”根据《说文解字》的阐明:发布命令者为君。
“子”字在先秦期间指的是对贵族男子的统称。故而,在词源剖析上,“君子”一词的最初来源可能是对国君之子的称呼,后来这个意思发生了第一层引申,详细涵义由表示个别的特定人之称呼演化为对当时贵族群体的称呼。也可能“君子”之词在出身之初指的便是当时的“贵族统治者”或者“贵族男子”。
“君子”为何演化为如今之意——词义的延伸从文献资料角度出发,孔子时期之前较为可信的文献资料紧张有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材料以及《尚书》、《易经》、《诗经》等几部传世文献。在对“甲骨文”材料的研究中,尚没有创造“君”字与“子”字连用情形。在对“金文”材料研究方面,最早有“君子”一词涌现的情形是在晋国青铜水器铭文《智君子锰》中。笔者试从先秦文献中所载有关“君子”的内容来探究君子词意的变迁。
《尚书》中的君子《尚书》中“君子”一词共涌现有八次, 《尚书》中八例涉及“君子”的文献中,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一句出自《尚书·虞书·大禹漠》中,别的七例均涌如今《尚书·周书》中。但研究者普遍认为《大禹漠》一文不见于今文《尚书》,其伪书性子已成定论,故《尚书》中的“君子”之词反响确当是周代至春秋之间的“君子”观点。且《尚书》这八例涉及“君子”的文献中,学者认为唯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一句有着道德内涵,别的七例中的“君子”大致均表示为“君长”、“官长”之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尚书》中,“君子”一词在内涵上还多表示为社会阶层方面,“君子”一词还多被利用为身份地位上的观点,这时“君子”一词的道德行内涵尚未涌现或者尚不盛行。
《周易》中的君子
在《周易》一书中“君子”一词共涌现有20次, 研究者普遍认为《周易》一书当涌现于殷周变革之际,司马迁认为《周易》为文王所作,顾颉刚师长西席在其《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中认为《周易》爻辞中提到的一些历史事宜有不少在文王之后,如《晋》卦中涌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显然说的是周成王期间之事,以是,《周易》不应当出自文王之手。但是《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很强,和西周初年周人的精神风貌相似度很高。顾领刚师长西席通过研究认为,《周易》当出自西周巫史之手,《周易》一书当成书于西周初年。故而,《周易》一书中所涌现的“君子”当是西周期间人们对“君子”一词的观点。
在《周易》中,“君子”一词仍以“贵族男子”、“官长”作为其紧张精神内涵,但是诸如“忧患”、“自强”、“谦逊”、“知几”“中正”、“节”等后世“君子”所必须具备的一些道德与聪慧方面上的内容已经涌现。这一期间的“君子”已经从词源意义方面上,纯挚作为贵族阶级的“君子”,引申到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君子”在此时已经开始被授予了一定道德意义上的东西。同时作为贵族统治者的“君子”,其政治聪慧与统治方法也在进一步成熟。
《左传》中的君子
在《左传》一书中,“君子”一词共涌现有181次,《左传》中“君子”一词在指代社会阶层方面意义上的利用上在不断弱化,在指代道德规范、行为规范、文化素养等评价性方面意义上的利用上在不断强化。“君子”在内容指向上开始变得越来越详细,“君子”在详细精神内涵指向上越来越成熟,在行事规范上,是否合乎“仁”、合乎“礼”合乎“义”、合乎“智”、合乎“信”、合乎“孝”是能否被称之为“君子”的主要标准。
《论语》中的君子
在《论语》期间的孔子那里,君子及君子文化的内涵在孔子手中得到了一个更为深化的改造。孔子在不改变“君子”旧内涵的条件下,给“君子”授予了更多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道德思想方面的内涵,极大提高了“君子”的准入门槛,更多的在位者被排斥到“君子”观点之外,孔子公然称当时在位者“斗答之人,何足也”,“君子”一词的道德行方向终极取代其阶层性方向,成为评价当时人君子与否的核心标准。君子与君子文化的内涵在孔子这里发生了质的突变。
通过对“君子”一词的词源剖析以及对孔子时期以前传世文献的剖析可以创造,“君子”一词自其出身之后在词义上就在不断发生延伸,“君子”一词从原来表示“国君之子”乃至“贵族男子”的意思在演化中不断扩展其内涵,不断被授予新的内容,直至形成本日我们所理解的“君子”之意。
“君子”词意演化的缘故原由紧张有三个方面:
一、词汇涵义的自然演化。
从措辞学的角度来说,每个词汇的出身,都会有其产生、引申、蜕变、发展的自然过程。上层词汇的内涵在蜕变发展过程中多方向于内涵下移,如“公子”一词,在春秋期间指的是诸侯之子。但是随着韶光推移,其在指代工具的社会阶层也逐渐下移,包含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春秋期间指代诸侯之子,下移到指代官宦之子、巨室子弟,直到其在内涵上彻底平民化。
二、春秋期间道德礼制的衰落与“君子”内涵的再塑造。
春秋期间是一个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的一个新旧交替期间。这一期间王室衰微、社会动荡,礼乐制度严重衰退。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当时社会精良分子的重新塑造下,一套涵盖了政德方面、文化素养方面,个人道德教化等各方面内容的“君子文化”在这一期间开始定型。
三、文化与“道统”的下移。
西周以及春秋前期,后世所说的“道统”与“治统”尚未分离,学校即是官府,官员即是西席,官师合一。哲学理论节制者还是由官方的巫史节制,“君子”与“道统”尚未发生很深的联系。到了春秋期间,由于社会变革开始呈现剧烈化趋势,个人、家族的社会地位在这种剧烈变革中急剧沉浮,“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成为了这个期间的社会阶层剧烈起伏变革的一个深刻特点。
统治阶层的文化垄断地位开始被逐渐冲破,“礼失落求诸野”的征象逐渐蔓延,私人办学开始涌现。是时,不少“博物君子”一方面损失了其作为贵族根本的职位、财产,一方面又节制着“道统”的阐明权,开始逐渐被强调了起来。君子之学与君子文化在这一期间被建立了起来,成为了这一时“君子”一词关于社会阶层方面的内涵开始逐渐被剥离或者被忽略,而“君子”关于“政德”方面、“文化素养”方面,“个人道德教化”方面的内容是人们精神内涵与人格空想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孔子:《尚书》
周振甫:《周易译注》
陆德明音义:《毛诗》
杨伯峻译注:《论语》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傅荣昌:《“君了”历史演化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