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屈原的弟子、美男子宋玉却说,“悲哉!
秋之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唐代大墨客杜甫也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自古文人多悲秋”,“悲秋”彷佛一贯都是文人墨客咏叹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秋色,在毛主席笔下却是其余一种格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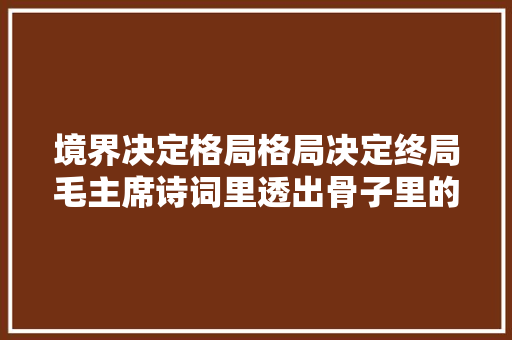
红军期间的毛主席
毛主席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颓败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空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因此而独步诗坛。
宋玉、杜甫为什么“悲秋”?由于怀才不遇,或因羁旅他乡而孤寂清冷,或因忧国忧民而惨恻痛楚,或为落拓失落意而烦闷苦闷。
忧郁之中,文民气乱如麻,这个时候,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便成了他们宣泄不良感情的工具,感情中有不甘、不平,更有无奈和悲怨。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文人“悲秋”的代表作。黄叶飘落,冷风袭身,怒号的秋风,凄苦的秋雨,漏雨的茅屋,惹得杜甫心烦意乱,悲愤不已。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落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嗟叹。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日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就寝,永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面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去世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意境图
在这首诗中,杜甫首先描写了他的焦虑和不安:狂风,秋雨,破屋,凄风苦雨,如何熬过这漫漫永夜。
紧接着,墨客写出了他的无奈:面对“公然抱茅入竹去”的群童,杜甫“唇焦口燥”,却无能为力,只能“倚杖自嗟叹”。
在此之后,墨客道出了他不堪的窘境:身上盖着“冷似铁”的“布衾”,无助地看着被“如麻”的雨水打湿的床头,一家人今夜注定无眠。
墨客哀叹道:何时能有“安如山”的屋子,让天下的读书人不再受这般苦、遭这般罪?
墨客末了抱负道,果真有那么一天,纵然我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我就算冻去世也无憾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很多人看到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绪表露,而我却只看到了杜甫的哀怨和嗟叹。
除了哀怨和嗟叹,剩下的只能是他不切实际的抱负。
在杜甫的天下里,秋日是灰暗的,阴冷的,萧瑟的,墨客的感情是低沉的,态度是悲观的。
秋日便是这样恼人的、被谩骂的时令,时运不济,墨客自怨自艾,“悲秋”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秋景象势磅礴、充满活气,秋天景色气候万千、壮美无比!毛主席一反“千古文人皆悲秋”之基调,在他的诗词里,秋日完备是其余一种样子容貌。
1925年晚秋,32岁的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前往广州,途经长沙时,毛泽东重游橘子洲。
毛泽东独立在橘子洲头,眼看着俏丽动人的湘江秋天景色,遐想着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秋色壮美,毛泽东的胸襟更是壮阔。
深秋时分,正是万物肃杀之时。万山红遍的枫叶与碧绿汪洋的湘江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然而,毛主席并非只为写景,为的是引出他的惊天一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皆因天性使然,不管是“鹰”还是“鱼”,想要好好活着便该当如此,没有别的选择。
那么,人类的未来该当由什么来决定呢?积贫积弱、战乱不断的中国该走向何方?
毛主席瞥见了无限美好的秋色,同时想到了贫瘠的国家和苦难的公民。
这首词的上阕描述的是湘江的秋天景色、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首词的下阕,毛主席通过追忆往昔,抒写了自己博大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
在萧瑟的秋风中,我们须要一双创造美的眼睛;
在茫茫黑夜里,我们须要一颗追求光明的年夜志!
《采桑子.重阳》
4年之后的重阳节(1929年10月11日),毛主席又写了一首与秋日有关的诗词-《采桑子.重阳》。
创作这首词的时候,毛主席的处境非常尴尬。
这个时候,毛主席刚刚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遭遇重挫,毛主席不仅成了不被理解的“少数派”,还丧失落了前委布告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上,毛主席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被冠以“流寇主义”;
毛主席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却被责怪为“家长制”;
毛主席身染疟疾,在上杭县苏家坡养病期间,毛主席过的是类似于“禁足”的日子;
红四军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毛主席没有到会,陈毅赴中心开会尚未归来,会议由朱德军长主持召开。
许多同道哀求“请毛泽东同道回来领导红四军”,“前委”接管了大多数同道的见地,朱德军长派人给毛主席送去一封信,态度诚恳地请毛主席回红四军事情。
可是,当毛主席坐着担架赶到会场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而且,毛主席“前委布告”的职务仍旧没有规复。
如此境遇,毛主席若是像杜甫、宋玉那样“悲秋”的文人,他或许也会写出一首伤感的、悲悲戚戚的诗词来。
可是,当天高气爽、重阳佳节来到之时,看到院子里盛开的菊花,毛主席诗兴大发,信笔写下《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喷鼻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战地黄花分外喷鼻香
一首《采桑子·重阳》,毛主席的梦想和现实再一次发生了位移。
这首词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极富哲理。
这句词引用于唐代浪漫主义墨客李贺的《金铜神仙辞汉歌》,李贺的原句是“天若有情天亦老”。
毛主席却“反其意而用之”-“人生易老天难老”,意喻“人生有尽,天道无穷”。
韶光易逝,人生短匆匆,一寸光阴一寸金,尔等切莫叹老怀悲,虚掷光阴,该当只争朝夕、努力进取,莫让年华付流水。
“人生有尽,天道无穷”,人生易老而苍天不老,“重阳节”每年都会来到,战地黄花依旧那样的芬芳。
这里的“战地”指的是闽西赤色根据地,“黄花”指的是各处盛开的菊花。
秋风劲吹,这秋色虽然不如春天那般妖冶,却有着春天没有的壮美。
毛主席立足于对宇宙、对人生的认知,辩证地揭示了人生的真谛。
自古以来,每逢“重阳”,人们都有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习俗,这就让“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毛主席赋诗“咏菊”之前,身逢浊世的墨客也爱“咏菊”,可是,在他们的笔下,名为“咏菊”,表达的是却是厌战、偷安之情。
而毛主席却把“黄花”与波澜壮阔的公民革命战役联系到了一起。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黄花”不是“爱菊高人吟逸韵”,也不是“悲秋病客感衰怀”,而是在硝烟中凌寒绽放的野菊花。
她平凡朴实,却活气发达;她鲜艳而不妖媚,在“黄花”装点下,“战地”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俏丽,就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
油画 毛主席在井冈山
总而言之,毛主席是带着愉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
在这首词的下阕中,毛主席凭高远眺,将诗词的意境提升至更高、更阔处。
“一年一度秋风劲”,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毛主席没有因此而感伤“悲秋”,区区一个“劲”字,干脆利落隧道出了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之势。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伟人有墨客的感情和浪漫,更有战士的豪迈和英雄气概,这就决定了他的审美取向。
重读《采桑子.重阳》,你会创造,毛主席这首词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有情有景,有色有喷鼻香,天空海阔,气度恢宏,你会不由自主地沉醉于这首词构画的意境之中。
这首词旗帜光鲜地歌颂了地皮革命战役,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空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与历代文人的“咏秋”诗作比较,你在毛主席的这首诗词里品味不到半点失落意、失落落之意,你能感想熏染到的只有积极向上、满满的正能量。
这是“骨子里的豪放”,毛主席的豪放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来的!人们喜好赏春,那是由于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恋夏,是由于艳阳似火,活气勃勃;悦冬,是由于银装素裹,冰清玉洁。唯独秋日不受待见。
自从宋玉首开“悲秋”先河之后,“悲秋”就成为历代文人经久不变的基调。
魏文帝曹丕在《燕歌行》写道:“秋风萧瑟景象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人,“三苏”之一苏轼也说:“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负一秋悲”。
千古以来,只有两个人敢于“反悲秋之常调,吐千古之豪放”,一个是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还有一个便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刘禹锡《秋词》意境图
刘禹锡在《秋词》中这样写道: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在这首诗里,刘禹锡断然否定了古人“悲秋”的不雅观念,表现出了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
他以最大的激情亲切讴歌了秋日的美好,难能名贵的是,创作《秋词》之时,刘禹锡并非“春风得意”,而是官场失落意、被贬朗州之时。
然而,正由于如此,刘禹锡在《秋词》中还是表露了自己对“被贬朗州”的沮丧和不甘,虽然“引诗情到碧霄”,那“凌云的鹤”却是孤独的。
与毛主席的《采桑子.重阳》比较,刘禹锡的《秋词》缺了那么一点秘闻,少了一点英气。
我无意对刘禹锡的诗作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在“自古文人皆悲秋”的年代,刘禹锡的《秋词》已属百里挑一、出类拔萃之作。
我想说的是,刘禹锡生前只是个“太子来宾”(官名),卒后才被追认为“户部尚书”,也便是说,刘禹锡充其量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
受其身处的时期所限,也受限于其文人气质和历史地位,刘禹锡不可能有毛主席那样博大的肚量胸襟和豪放的气概。
大气、豪迈,天马行空、自由清闲,这种“骨子里的豪放”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来的!
有那样的胸襟和气魄,才能达到那种“高山仰止”的境界。
油画 战地黄花
结语在悲观者的眼中,秋日无疑是萧瑟凄凉的。
而在毛主席的眼里,秋日只是四季中的一个时令,落去的树叶、枯黄的草木固然凋敝,然而,这样的秋日却是无比壮美的。
等到东风再来,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