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亭废剩青山 韩陵片石在人间
——唐开元《石亭记·千秋亭记》的逸闻往事
钟力生
盛世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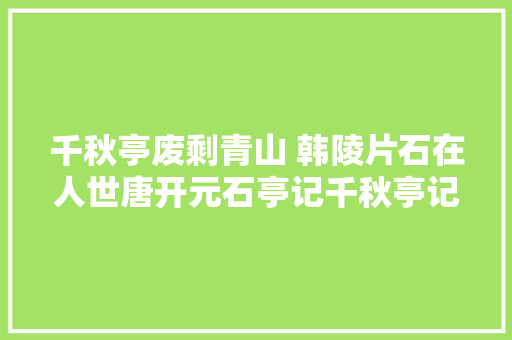
盛唐之时,文化兴盛。唐开元十八年(730),西蜀梓州铜山县(今中江县广福镇)的几名基层官员,在离铜山县城东北5里的玉江边(郪江正源),修了一座石头离亭,取名“石亭”。
离亭又叫驿亭、长亭,古人常在这里举行送别仪式。“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这首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词、广为传唱的歌曲《送别》,充分展现了长亭送别的场景与心绪。
古人更加看重离去之情。那时交通不发达,所谓生离去世别,或许一别即是永别,再见即再不能相见。送别是人生大事,以是建筑这座送别之亭,也是铜山县当时的一件精神文化大事,得到县寮丞宋元愻(今常务副县长)、主簿郭钦让(今分管文教财政的副县长)、县尉崔文邕(今分管政法民政的副县长)的大力支持,县尉崔文邕是发起人和履行者。当年12月,工程竣工,铜山县举行盛大的落成仪式,并请文笔出众的邻县飞乌县(今中江县仓山镇)前主簿赵演作了一篇文采飞扬的文章《石亭记》,请铜山县书法出众的前主簿郭延瑾书写,刻记于石亭旁的崖壁上。
清同治年间陆心源所编著《唐文拾遗》收录的《石亭记》
《石亭记》引经据典、文笔幽美、精干简洁、构造紧凑,是一篇教科书般的范文,惜作者赵演官职和名气太小,文章不能广泛传行于世,除《潼川府志》《中江县志》外,其他文籍仅晚清古文献学家陆心源所编著的《唐文拾遗》收录此文。全文如下:
石亭记
盖此石亭者,送别之地也。昔汉国二疏□郊,七子风骚雨散,有追送之篇章;西倠□梁,是不合之祖饯,何独古之惨恻今之□凌乎?粤我县寮丞广平宋元愻、主簿太□郭钦让、尉博陵崔文邕总括宏才,且安□秩,承凋弊之俗,行辑宁之化,政能垂绶,声辍调弦。去来宾朋,不欢会于永日;远近郊郭,惜悲离于一时。供帐虽开,野亭多阙,而乃春藉芳草,秋倚乔林,赋诗赠行,酌酒相劝,亦以别矣。然崔子名族之秀美,干于事,适于时,爰凭岩崖,用省构造,袥嵌岩以高敞,豁崆峒以傍开;种柳横阶,莳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溽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癣织锦,俯伏江浒,编联道周。因此驻征盖于浮云,长鸣班马;握离杯于沟水,匆匆转飞鹦。庶将来之吾贤,知有作之明悊;式刊古石,永烈声徽。是时开元十有八年冬,星回大荒落,月应大吕,朔临甲乙,日御戊辰。前飞乌县主簿赵演词也。前铜山县主簿郭延瑾书。
文中“二疏□郊”用的是西汉高官疏广、疏受叔侄辞官归故里时,“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的典故;“七子风骚雨散,有追送之篇章”和后来晚唐墨客罗隐《寄酬邺王罗令公》诗中“书函二王争巧拙,篇章七子避风骚”的句子,都是出自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王粲《赠蔡子笃》诗中“风骚云散,一别如雨”的典故。“长鸣班马”“匆匆转飞鹦”则脱化于大唐宰相苏颋《赠彭州权别驾》诗中“黄莺急啭东风尽,班马长嘶落景催”,同时期的诗仙李白在《送朋侪》中也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等送别诗句。文中骈文华美,词句幽美,“种柳横阶,莳兰约砌;韶月则娇花乱入,溽暑则新藤竞垂;绿苔缀钱,红癣织锦,俯伏江浒,编联道周”,生动地描述出古道边、石亭外的四季美景。“驻征盖于浮云”“握离杯于沟水”则描述了士人们别离时,驻车于石亭,在水天一色、浮云入江的郪江畔,曲水流觞、赋诗赠行的高雅情趣。
第二年,开元十九年(731)五月,县尉崔文邕仍觉意犹未尽,遂将“石亭”更名为“千秋亭”,在崖壁《石亭记》后亲笔补题一首诗,进一步彰显自己的功绩,并追改石刻标题为《石亭记·千秋亭记》。补题诗文如下:
五言·千秋亭咏并序
朝散郎行梓州铜山县尉博陵崔文邕
此千秋亭者,邕草创也。故得词人刊其不朽,自兹作古,仍勒是诗,客歌郢中,庶有同唱者矣。
饮饯凭何地,依岩辟此亭,
玉江标胜讬,石壁效题铭;
秋染藤宜紫,春图柳爱青,
樽来是离酌,皆为送归情。
开元十九年纪次辛未五月五日
崔文邕官职虽小,却出身显贵,“博陵崔氏”在东汉即为名门,后发展为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等齐名的一流士族,在唐朝共出15位宰相。曾参与“神龙政变”逼迫周皇武则天逊位,迎立中宗李显复位的大唐宰相、博陵郡王崔玄暐和写下“前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著名墨客崔颢,都出自“博陵崔氏”。崔文邕追改石刻的行为,反响了开元盛唐时士族子弟渴望建功立业、以图千秋不朽的浮荣心态。
千秋亭并不能千秋永存,32年后的唐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避祸梓州的诗圣杜甫在此送别朋侪,曾赋诗一首:
郪江亭送眉州辛别驾
柳影含云幕,江波近酒壶。
异方惊会面,终宴惜征途。
沙晚低风蝶,天晴喜浴凫。
别离伤老大,意绪日荒漠。
此后,传世文章、诗词中鲜见提到“千秋亭”,亭子很可能消逝于唐末浊世,唯有《石亭记·千秋亭记》摩崖石刻历经千年,流存于近代。
《石亭记·千秋亭记》拓片(局部)
千秋书法
20世纪70年代前,成都青羊宫附近的古玩市场间或有人在售卖一种石本拓片,有的裁切成册,有的裱成横幅,因其字体舒张遒逸、颇有古意,为书法爱好者追捧喜好;因帖中题名“石亭记·千秋亭记”,人们简称为《千秋亭记》或《千秋亭帖》。
实在早在清道光年间,《千秋亭记》摩崖书法拓片就已逐渐在世间风行传播。当时,四川按察使(今分管政法监察的省级领导)刘喜海,对金石古泉、碑刻书法极有兴趣和研究,得到《千秋亭记》摩崖书法拓片后,十分喜好和重视,时时品读把玩,并在拓片上钤自己的私印“刘燕庭西蜀得碑记”“丙午”2枚,这是现今已知留存于世韶光较早、存字较多、拓印清晰的版本。
刘喜海字燕庭,山东诸城人,家学渊源深厚,曾祖是刘统勋,叔祖是刘墉刘罗锅。他以治金石学最有名,鉴赏金石,过眼即辨。任官职20余年,不慕荣利,箧中金石、古书,以车辆装载,有“博古君子”之称。他将自己喜好的《千秋亭记》照原样缩小摹写,将自己收藏保存的四川(当时含重庆)汉至唐、宋的碑刻、器物等一并画样临摹,编入自己著录的《三巴孴古志·金石苑》(5册)一书中,对四川地区主要碑刻等文献的保存和传承作出了莫大贡献。《三巴孴古志·金石苑》在日本帝国图书馆有藏本,并钤盖“明治四三”印戳。刘喜海后来在浙江任职时,因“嗜古”被人弹劾辞官。
南梁《瘗鹤铭》局部
清代对书法最主要的贡献便是碑学的兴起。清代乃至民国期间,学者们极其重视对碑石、摩崖、墓志等的访碑稽核和摹习,这极大地推动了《千秋亭记》石本的传播。清末民初,大书法家康有为对《千秋亭记》十分钟爱,听说他晚年得到《千秋亭记》拓片后,秘而不宣,“视为珍宝,刻意摹写,并在该刻笔势的根本上,予以进一步的夸年夜,遂成‘康体’”。近代藏书家、订正学家章钰师长西席(1865—1937),古笔墨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商承祚师长西席(1902—1991)都持这种不雅观点。
章钰曾在所藏《千秋亭记》拓片上题签道:“近康有为演习此刻而成一脉,乃所著广双楫有卑唐一篇,真欺人也。”(《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
1943年,商承祚在重庆购得《千秋亭记》拓片,一见大为惊异,认为印证了康有为习练《千秋亭记》的说法,并在拓片上题跋称:“康有为书法自诩宗魏,遂有尊魏卑唐之论,今见此知康书所自……师魏之说,夸张大言,遂被揭破,可谓大愚不可及矣。”
这便引出书法界一段“尊魏卑唐”的历史公案。康有为所编《广艺舟双楫》书法专著中,“尊魏卑唐”是其核心思想。他在《尊碑》一篇中列举了北碑五大优点,认为唐宋两代无此境界,极力抑唐;在《卑唐》一篇中,他认为唐代书法“专讲构造”“整洁过分”“浇淳散朴,古意已漓”。
这当然要引起崇尚唐代书法的爱好者们的反击,尤其是得知康有为在习练唐代摩崖石本《千秋亭记》后,更认为康有为说一套做一套,“欺人”且“大愚不可及”。
实在书法入门练习中自古就有“习北碑”“尊二王”“崇颜柳”等各种不同不雅观点,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强求。《千秋亭记》明显受到魏晋南北朝碑刻书法影响,是含“汉魏风骨、六朝古意”的唐代摩崖石刻,和唐代盛行“欧、褚、颜、柳”书体风格迥异,康有为“卑唐”而不是一概抛弃,也不能算“欺人”。
当代成都书家林鲁辛这样评价《千秋亭记》:“鉴赏其书法,其书风一反唐代碑刻持重规整之习,全体石刻书风的特点是散逸流宕,率真朴实,周遭兼备,不拘谨,不造作。文之部分以圆笔居多,楷行相参,结体欹斜新奇,似有南梁《瘗鹤铭》遗韵,但更具神奇的变革;诗之部分以方笔为主,开张舒和而不失落整饬,用笔入收迁移转变健朗随意率性,斩斫有势,大有北魏诸刻之英气。如能负责研习领会《千秋亭记》的书法,可破板、刻、结的习气。在用笔及结体的变革上、使才任情的镕铸上,能得到很多启示。难怪康有为晚年的书法有该碑刻的痕迹,可见影响不小。”
有诗赞曰:“石亭送别水悠悠,妙墨都从绝壁搜。留得开元真迹在,赵崔笔墨亦千秋。”(民国·铜山书院·黄镜澄)
《三巴孴古志·金石苑》中收录的《石亭记·千秋亭记》摹本
后 记
青山不改容颜,江河万古奔流。从千秋亭故地旁不舍昼夜涌流不息的玉江水,见证了铜山县文化的兴盛繁荣与历史变迁。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20岁的梓州铜山人苏易简擢冠甲科,为宋代四川状元第一人。苏易简的曾祖苏振为铜山县令,远祖即是大唐宰相苏颋,有词句“黄莺急啭”“班马长嘶”为《千秋亭记》所借鉴。后来,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祖孙3人以书法、文章著称于世,大概或多或少受到过家乡《千秋亭记》的影响吧。
秉承《千秋亭记》的唐风,受“铜山三苏”勉励,宋代铜山一域文化更加繁荣,玉江流域增长了更多文化印迹,既有摩崖题刻,又有摩崖造像,内容涵盖儒学经典、诗文、宗教、记事、公约等诸多事物,是研究铜山历史、人文、景致、金石等文化主要的历史遗存,称作“玉江石刻群”。
明嘉靖辛亥岁(1551),陕西布政司左参议、中江人王惟贤为先人探求一处风水宝地,见铜山(元初并入中江县)“山川盘礴,形势悠扬”,惊喜其为“钟灵之府”,于是举家迁来,在此定居,并稽核记录了铜山的石刻文化和历史名人。他在建筑祠堂时还掘得几块古碑:《宋进士题名记碑》记录宋朝进士30余人,苏易简三世名列个中,《宋参军赵鼎吉修尉廨碑》称“苏易简,国初进士第一,蜀斯文发祥权舆此地”。王惟贤将这些写进《铜陵纪胜碣》《铜山乡贤祠记》,并和《千秋亭记》一样刻于玉江畔的崖壁,用来“阐扬前烈,以开后人,实一方风化”。
《三巴孴古志·金石苑》日本帝国图书馆藏本
清咸丰戊午(1858)玄月十一日,中江县令林振棨和铜山当地文化名人黄世喆、刘开蒙、林捷升等,冒雨寻访铜山文化遗迹菩萨崖、当阳石、飞来泉、龙隐洞等,并不雅观唐开元十九年千秋亭题咏石刻,“尘襟为之一爽”,赋诗赞道:“千秋亭废剩青山,唐代名留管扫斑。曾见开元全盛日,韩陵片石在人间。”
20世纪70年代,农业田土改造时,《千秋亭记》摩崖石刻遭到一定破坏,但仍时时有人前来拓印残字。当地农夫恼怒拓印者常常践踏土内庄稼,遂用镰刀将其残字剜去。至此,存世1240余年的《千秋亭记》摩崖刻记完备消逝,泯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