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夜雨寄北》是晚唐墨客李商隐的名作,诗中故意重复“巴山夜雨”四字,将实有与虚拟之景绾合在一起:雨既是作客他乡的墨客写作时的现实环境,又是墨客设想将来回抵家乡、与妻子灯下相对时评论辩论的话题。短短二十八字,既展现了客途霖雨、归期无定的悲惨,又暗含着夜雨剪烛、西窗共话的温馨;而这两幅迥然不同的场景与感情,正好构成中国古典诗歌中“雨”意象的基本内涵。
战国晚期墨客屈原以“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的阴冷环境,映衬俏丽忧伤的巫山神女形象(《九歌·山鬼》);以“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涉江》),极言流放之地的悲惨,都收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的效果。但是这种以雨景陪衬气氛的诗句在接下来的汉魏期间并不多见,直到南朝墨客何逊写出“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临行与故游夜别》)的名句,通过描写挑灯长谈、静听夜雨滴落台阶之景,表现离去时依依不舍、黯然神伤之情。可以说,何逊创造了雨意象的细腻情味,并以清丽真切的笔调加以表现。从此往后,作为自然征象的雨在诗词中险些固定地用于渲染凄清的氛围,表现寂寞的情绪,并且常常与离去、流落、孤独这类悲观主题联系在一起。
虽然现实中的离去未必都发生在雨中,但是以雨为背景的诗歌显然更具艺术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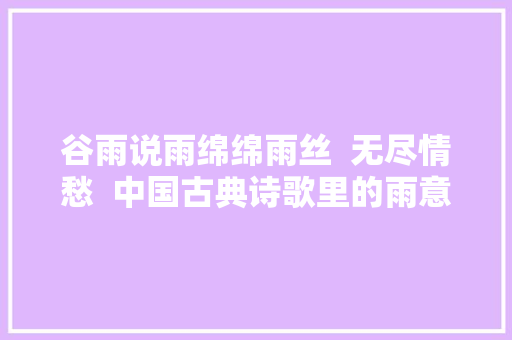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寒蝉悲惨,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韦应物《赋得暮雨送李曹》)
一夜寒雨之后的黎明,王昌龄客中送客;骤雨初歇的傍晚,柳永与情人分别,雨不仅带来自然的寒意,更增长生理上的悲惨。而在晚钟声中,韦应物迎着微雨送人登舟,那打湿衣衫的,不知是绵绵的雨丝,还是离去的泪水?
离去之后是彼此无尽的思念,尤其是当永夜耿耿、冷雨敲窗、辗转难寐之际:
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别恨转深何处写,出路惟有一登楼。(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
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柳永《浪淘沙》)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聂胜琼《鹧鸪天》)
前二首诗词从旅途中人的角度着笔,以夜雨为背景,表现对故人的思念以及天涯倦客的情怀;后一首词则以留守之人的口吻,表现女性长久守望、夜雨无眠的孤凄。窗外无情的雨滴与窗内相思的泪滴构成交相叠映的画面,彷佛大自然也能体恤离人的悲苦,也被人间的情怀所冲动。
纵然普通人,阴雨之夜也会有些不同平凡的感想熏染,须要形诸吟咏:以仁爱为怀的杜甫在春雨之夜与朋友相聚,“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小雨檐花落”(《醉时歌》),传达出一种细腻的温情,一份甜美的静寂;白居易晚年官务清闲,不问世事,“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秋雨夜眠》),闲适通达之中,终有难掩的落寞颓败;素有“诗鬼”之称的李贺,常常以“冷雨”作为幽魂出没的背景,“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喷鼻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冷雨洒窗,幽魂来访,对生命短匆匆的恐怖与无奈,对声名永垂的神往与惆怅,是去世生异路的“喷鼻香魂”与“书客”今夜共同的情怀。雨夜使三位墨客产生截然不同的感情与感想熏染,折射出他们在性情、处境与悟性方面的差异。
雨自空中迅疾飘洒而下,难以从形态上加以把握,故而直接描写雨意象形态的佳作较为少见,“小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小雨纤纤风细细,万家杨柳青烟里,恋树湿花飞不起”(朱服《渔家傲》),描写的重点是雨中景物;“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王维《送梓州李使君》)、“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逐一风荷举”(周邦彦《苏幕遮》),刻画的重点是雨后景物,皆是从侧面着笔。至于“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李商隐《重过圣女祠》)、“清闲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秦不雅观《浣溪沙》),则是捉住春雨稍微迷濛的特点,利用倒喻手腕,将其比作梦境,比作愁情,在抽象的生理活动与详细的绵绵小雨之间建立联系。这与其说是重在刻画春雨的形态,莫如说意在传达墨客惆怅忧伤的主不雅观感情。
雨的形态难以摹写,雨带给人的悲观感想熏染在静夜中更为深刻,因而墨客们更方向于以“夜雨”作为诗歌的中央意象,并在历史积淀中形成“夜雨”与某些景物的特定组合办法:
夜雨孤灯。夜与雨在人和外界之间形成双重阻隔,灯光则界定出一个轮廓分明的可视范围,匆匆使人收回不雅观看外界的目光,更为细腻敏锐地回视内心天下。“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王维《辋川绝句》),敏感的心灵谛听着自然界微弱的音响,寂寞中略带几份禅意;“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李商隐《春雨》),明净凉冷的雨丝织成帘幕,摇荡的灯光经由折射显得加倍迷离,渲染出可望而不可及的惆怅;“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雨的冷与灯的暖形成强烈比拟,黄叶与白头却传达出共同的颓败气息,生命的循环代谢此刻让人这般无可奈何。
夜雨梧桐。中国古人有“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说法,故而梧桐意象常与秋雨联系在一起。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较早成功组合这对意象,以“秋雨梧桐叶落时”渲染唐明皇对杨玉环的无尽思念,形成用“梧桐雨”表现离情的传统,“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周紫芝《鹧鸪天》),都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雨打芭蕉。芭蕉嫩叶卷曲在一起,常被用来比喻难以消释的愁情,李清照有“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添字丑奴儿》)之句;骤雨敲打芭蕉伸展的大叶,在静夜中声声入耳,令人难以入睡:“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杜牧《八六子》)、“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万俟咏《长相思·雨》)。南宋词人吴文英干脆独出心裁地写未雨芭蕉:“何处合成愁?离民气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唐多令》),芭蕉滴雨之声引起的感想熏染太过强烈,以至于单是听到风吹蕉叶的声响,已让离人难以忍受。
从以上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付描摹雨之形,墨客们更喜好捕捉雨的声响,“疏雨滴梧桐”(孟浩然)、“留得残荷听雨声”(李商隐)、“雨声滴碎荷声”(欧阳修),皆得真切妙理。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题目便是“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曾为进士,过了几年仕宦生涯。但南宋很快就灭亡了,他生平大部分韶光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此词用冷冷雨珠穿起人生的三个不同期间、不同场景:歌楼听雨的少年欢快,光阴短暂,影象永恒;客舟听雨,实是兵荒马乱之际、忧患中年之时,词人在茫茫人生道路上踽踽独行的缩影;僧庐听雨,晚境苍凉,词人却已木然无动于衷。在造化无情的悟彻之中、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的冷漠与断交态度里,模糊透露作者内心深处难以消释的破家亡国之痛。
撰文:杨春俏
责编:海彦
(揭橥于《中华活页文选(高中版)》2004年第1期)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桃李国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