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王昌龄
闺中少妇未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这首诗还有一个版本第一句是“闺中少妇不知愁”,这个“知”和这个“曾”就很值得考虑,“知”字含有不知、不懂、没有这方面儿意识的意思,但从诗中末了一句中的“悔”字来看,显然这位少妇是懂得这些细腻情绪的,在诗的一开始,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少妇此时尚未愁,而不是不知愁、不懂愁,于是我们在此就选择了“曾”字这一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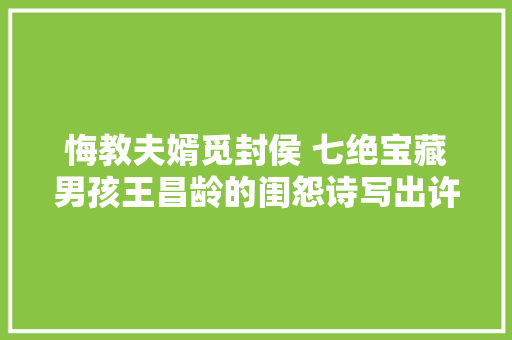
“闺中少妇未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这首诗的用意显然是层层递进的,这位少妇显然还如少女一样平常,并为打仗到愁,她一贯高枕而卧的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从下文中“翠楼”便知其家庭应不是一样平常普通人家。而从末了一句“觅封侯”中我们也能倒推出,少妇在一开始是支持其丈夫去边陲建功立业的,并且丈夫的这种追求志向的行为也给少妇带来了一些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她想到丈夫在边陲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回朝后被天子接见、赏赐、封侯,他们的小家也在丈夫奇迹成功之后变得越来越好。这或许才是少妇未曾愁的真实缘故原由。
在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唐朝前期年轻人们追求功名的路径,第一个则是考进士,但是这条路极其困难,唐代的时候科举取士的规模还不如宋朝那般弘大,只有极其精良的少数人才能在三年一比的科举中步入官僚阶层;第二条路则是去边陲立功,这是更为当时人所推崇的一种办法,我们之前读过王维那首有名的《送元二之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端人。”人们只知后两句名垂千古,却未曾重视前两句中所包含的故事:在早春时节,王维的朋友元二在过完年没几天就准备去西域军中任职,他是在前一年年末的时候通过在长安城中的人情关系谋得了这份差事,于是过完年还在正月里,元二就在先一天到达了咸阳(即渭城)城郊的客舍,而王维则是第二天算夜凌晨策马从长安城中前来为元二送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端人”两句更是表达出一种朋侪将赴边陲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而并没有唐朝后期送别诗中所含有的浊世离合的觉得。于是我们便从这些诗中理解到,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社会中,去西域边陲立功,是很多好男儿追求个人志向、钻营个人发展的一个主要渠道。
理解了这些,就更能明白,王昌龄诗中的少妇,在很长的一段韶光里,对丈夫离家去边陲立功的行为都是理解与支持,并含有某种期待的。
“春日凝妆上翠楼”这句算是一个小小的迁移转变,这个迁移转变很细腻,重点在“凝妆”二字上。又是一年春天,她的丈夫或许已经出去好几年了,此时的少妇也为这春色所动,于是决定郑重其事的欣赏一番,这个郑重其事就表示在“凝妆”上,为了欣赏这大好春景,她特地化上了正式的妆容,然后缓步登上自家庭院中的翠楼。我们可以揣摩一下少妇欣赏春色还要着重打扮一番的生理。我以为第一个缘故原由是,诗中的少妇首先是一位大家闺秀,端庄文雅是生活中本身就有的哀求。第二个缘故原由或许是,她很重视这俏丽的春色,她要配得上这样的春色,正所谓“名花倾国两相欢”也。第三个缘故原由可能就犹如我们当代人那样,几日未打扮,反正丈夫也不在,打扮来给谁看呢,就犹如温庭筠《菩萨蛮》中所描述的那般“
登上翠楼往后发生了什么呢?“忽见陌头杨柳色”,杨柳本是春日景象中很普遍的一种,作者又为何要用一“忽”字呢,想必这“陌头杨柳”一定是唤起了少妇的某种潜在意识,而这种潜在意识又与诗中前两句所描述的少妇“未曾愁”的状态大相径庭,于是墨客着一“忽”字以表达少妇心中感情的巨大迁移转变。我们曾在解读苏轼那首“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以及王湾那首“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讲过,春天真正令人从心底里清醒、从精神上欣欣向荣并打心眼儿里感到愉悦的,并不是仲春时节繁花尽放的时候,而是冬天还未完备过去,河里还流着冰凌,但春天的气息已经随处显现、吹在脸上的风已经有点轻软的时候,此时的人们还未从隆冬的冷峻中缓过神来,但春天的迹象却一直地给人以惊喜,意识到春天就要来了,那种被引发、被唤醒的觉得,才是春天最令民气动的感想熏染。而王昌龄这首闺怨诗中的少妇,此时彷佛就在经历这种被唤醒的心动时候。看到陌头的杨柳,她溘然意识到,自己彷佛辜负了许多这样美好的春日光阴,而这些光阴,也正是自己身位女子所最令人欣赏、最令人垂怜、最值得人宠爱的光阴,而这些,彷佛都被自己辜负了。
于是诗中末了来了一句与开篇完备不同的感情,“悔教夫婿觅封侯”,一个“悔”字,便将前两句所表达的少妇对丈夫在外建功立业的支持理解完备推翻,而此刻在少妇心里,自己须要被人垂怜、被人呵护、须要被陪伴、被宠爱的青春年华,才是最令她重视的。什么建功立业,什么封侯拜相,都是虚妄,此刻她须要陪伴,这才是最主要的。
这首诗最妙的地方在于,少妇闺怨感情的被唤醒。很多人说这首诗像是闺中少妇生活场景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截图,诗中四句已将少妇感情的缘起、迁移转变与戛然而止写完了,显得没有余韵,而我却以为,单单能读出少妇被“唤醒”这样细腻的情绪,就已经余味悠长了。我们不难在这首诗之后,续上浩瀚的描写北宋庭院里那些独居女性的诗词,那些品不完的孤单寂寞、说不完的思念怅望,鄙人刚刚开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