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深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题记
从先秦民歌“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轻声吟咏,到汉代芳草萋萋间“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的思念与守候,到唐代梅花初开时节“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的讶异与失落落,再到宋代易安居士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伴花随水流向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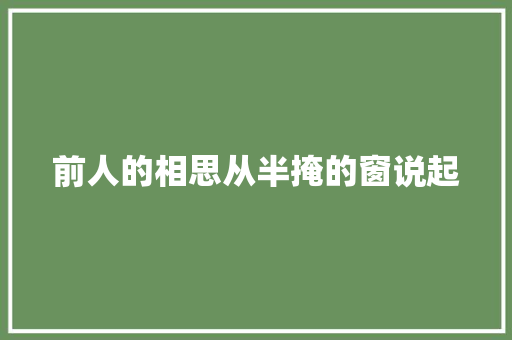
再到如今的我们对亲情面人的牵挂我们可以穿汉时衣,走魏晋桥,摆明清家具,用唐宋红炉陶罐......
而在走到某扇半掩的雕花窗子前,是否能感想熏染到曾经的人们临窗相思的深情?
一 、空床卧听南窗雨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都说红豆最相思,而我以为“窗”,亦是最饱含深情的意象。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是易安居士独立窗边,雨打梧桐声声断肠;“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是贺铸重过阊门万事皆非,空留旧栖新垅两依依的悲怆;那扇小轩窗,让苏轼超过十年死活两茫茫,在梦中见到爱妻旧时装扮的动人样子容貌;“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是卢仝在梅花满窗时的美好错觉......
“窗”,沟通了室内与外界,面前之景与内心所思,我们有时亦说“心灵之窗”;女子画眉装扮,文人诵读诗书,“窗”亦是古人日常生活的寓所之一——才会常常勾起临窗之人的心中念想与绵绵情思。
比起“窗含西岭千秋雪”“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对付一“窗”之景的描写,斗窗之间吐纳千里江山,宋代的“窗”更多的是一种小阁幽窗的清秀之气,引人愁思的凄美阴郁。《红楼梦》中黛玉曾吟“已知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悲惨?”,本就情意绵绵的窗,在风雨中更是催人断肠,它在雨打梧桐声中与形单影只的李清照为伴吟一首《声声慢》,它听过深夜贺铸伴着雨声的嗟叹,亦成了苏轼十年一梦中的最为凄恻的绮丽。
二 、梦断喷鼻香消四十年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相思本便是中国诗词一个永恒的主题,从《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伊始,注定缠绵悱恻、令人动人心魄——为个中欲笑还颦最断人肠,美满幸福灰飞烟灭满含痛楚,悲惨哀婉饱蘸血泪,更是为个中相思之深之久,穷尽生命极限。
“当时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他是孝宗所赐进士出身,千古男儿一放翁,他的生平,由两个破碎的梦组成,一是边关的冰河铁马,二是沈园的照影惊鸿。人生若只如初见,他与表妹唐婉相知相惜,无奈专制家长逼迫,利剑春断连理枝,分离之后苦处飘零。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欲笺苦处,独语斜栏。瞒,瞒,瞒。”
如果说沈园墙上的《钗头凤》,见证着他们久别后的相遇与对付短命爱情的遗恨与惋惜的话,也还散发着生命的热力。相思那样美好,相思有时却是毒药,唐婉在最美的年华烦闷而终......白发的放翁在四十年后重回沈园,“沈园柳老不吹棉”,而她已是“玉骨久成泉下土”,那么《沈园二首》,便见证了阴阳两隔的无奈和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思念的韶光跨度。
此身行作稽山土,独吊遗踪一泫然。
到生命尽头,思念在不断证明自己的永恒代价。
在那曾引发古人无限愁思的地点,一样精细的小轩窗,是否还能感想熏染到深情?我们的思念,有多恒远?
随着时期的发展,人们对付间隔和韶光的不雅观念在不断发生改变。游子归家不再是轻舟万重山的难事,可归心似箭不变;在日益完善的医疗条件下,生平拥有的韶光越来越长,而对付与亲情面人相处日子的珍惜不变。
相思,依然是古往今来人们共情最切的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