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理解王维的《竹里馆》?
这首诗我在谈论王国维论诗词的“有我”、“无我”之境的时候是用来作为示例利用的。
众人写诗,“有我”随意马虎,“无我”难。为何?作为抒怀言志的韵文,诗本身的功用便是表达。表达什么呢?表达墨客的内心,是日然就带入了墨客的思考和想法,成为“有我”之境凸显的作品。
而“无我”是如何做到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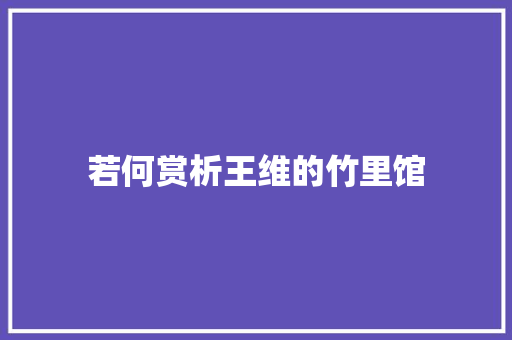
要达到“无我之境”,则须要超然的心态,跳出自己营造的诗的意境,让自己高于自己的作品天下,从内心俯视自己。
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完备由读者自己来感想熏染阅读当时的觉得,墨客本身形象只是一个道具,隐蔽在这种“无我”之境下的感情更加蕴藉、委婉,但是也就更加隽永。
这不只是写作手腕的问题,更是心境问题。
以是王国维又说: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非高手不能为之啊。
《竹里馆》便是王维这个高手的作品。实在和王维的称号“诗佛”比起来,他本身在诗坛的造诣是远高于“禅诗”的。王维在年轻的时候,同样的风骚倜傥,走马京华,同样地贬谪加身,塞外风刀,以是他的诗实在是多元化的,唐朝后来的墨客只取他一个角度,就自成名家。如果咱们当面称他为“诗佛”,王维绝对不带笑的,这实在是对他诗坛地位和能力的一种贬低。
这种花名一样的封号,纯粹便是大家愉快,强行加注。
王维晚年的作品由于修禅而带有清淡空灵的味道,是佛学的浸染还是历经死活的淡泊?都有可能,大概仅仅是不年轻了,技巧纯熟而心态日趋平和。我们详细来看这首《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诗意大略直白,并没有什么难懂的。我相信朋友们也不会要一句句解读这首诗,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要清楚的是王维如何用这大略的二十个字,几个平常的意象“幽篁”、“弹琴”、“长啸”、“明月”、“深林”构建出不同于“有我”之境的“无我”?
有我之境,便是墨客写墨客自己的活动和情绪;无我之境,便是墨客把自己当成客不雅观工具来描写。
为什么能读出空灵、冷寂之感?便是以超然物外的视角来描写、来表达。比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这里是谁在独坐,谁在弹琴,谁在长啸?彷佛是墨客,也更像不是墨客。即便是墨客自己,也如同一个画面中的人物,“我”只是远远地在看。
这种手腕就叫“以物不雅观物”,这种效果便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的“我”,说的便是作者自己。
作品里的作者形象只是一个道具,让表达更加委婉。
作为盛唐山水诗大宗,王维的清淡别有特色,我们和其他盛唐名家做个比较,就能更好地理解王维晚年的风格、《竹里馆》的风格了。
孟浩然也是山水田园大家,我们看他的《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落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是发自身心地热爱田园生活,以是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出浓浓的世俗之乐来。
读李白的《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我们能在描写中感想熏染到墨客和风景的积极互换,这些景致都是由于墨客而存在,情绪都在故意无意中注意灌输了笔墨,李白的作品便是“有我”之境的极致。
至于杜甫的写景,我们看《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去世,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圣笔下的景致都是他表达自身忧国忧民大志趣的工具而已。景致是什么,到底如何美,对他而言,并不主要,但他便是写得俊秀,让风景成为他抒怀的利器。
而这些各类,都不是王维。
王维写诗,没有自己、没有情绪、没有互换,只是高高地、远远地、悄悄地看。
这可不便是天地大“道”、佛、上帝的视角嘛。
从这个角度来说,称之为“诗佛”又挺贴切的。
(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