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林城地处长白山余脉的河谷地带,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在漫长的岁月里,生息于斯的先民们经历地穴、半地穴居住,到了明清期间,大多采取土、木构建的泥草房居住形式。吉林城的泥草房也叫“满族老屋”,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模样形状,都具有光鲜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东巡吉林时,吉林地区的这种房屋居住特色吸引了乾隆的把稳。在《呼兰》《拉哈》《额林》三首诗歌中,乾隆对吉林城的民居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记述。
远不雅观满族老屋,“烟囱安在山墙外”是最具特色的建筑模样形状。后世乃至把这一条编入“东北十八怪”中,与“窗户纸糊在外”“大缸小缸腌酸菜”等环境并列。满族老屋的烟囱俗称落地烟囱,在满语里叫做“呼兰”。萧红所著《呼兰河传》的呼兰河名称也是烟囱的意思。满族老屋的烟囱最早采取的是中空的树干。因此,乾隆的诗中开篇就说:“中通外直求材易,暮爨(cuàn,煮饭)晨炊利用均。”为防止“呛雨”,烟囱顶端会罩上一个柳条筐。室内土炕、火墙的烟道经“烟脖子”与烟囱连接,用以取暖和、做饭时排放烟气。木制烟囱不仅被民居采取,当时的官署也采取这一建筑形式。在《驻跸吉林将军署复得诗三首》中,乾隆留下了“木柱烟筒犹故俗,纸窗日影正新嘉”的诗句。不过,这种木制烟囱常成为发生失火的祸胎,后来逐步被泥垒或砖砌的烟囱取代。
清代,烧制的砖瓦在相称长的历史期间,在吉林城内都属于奇异之物。《吉林市建材志》中提到,吉林城原来没有砖瓦窑,衙署、寺庙内的部分建筑所利用的砖瓦,都是由盛京(沈阳)转运而来的。当时的吉林城,官署、民宅大量利用木材、泥土作为建筑材料,满族老屋普遍采取拉哈墙。“拉哈”在满语中是“挂泥草”的意思,或“缀麻泥墙”之意。筑墙时,在两柱之间以横木条为档,“缀麻草下垂,缘之以施圬墁,耐久不倒”(《吉林外纪》)。这种泥草墙利用高处预留的“嘛木哈图拉”(气孔)透风干燥,筑墙省力,保暖性非常好。见到“拉哈”后,遐想自己居住的砖木宫殿,乾隆满怀感慨地写下:“乘屋居间事索绹,经营妇子共勤恳。御寒塞向诸凡预,施墁编麻要取牢。出气天窗(即气孔)柱旁边,通烟土锉炕周遭。室家豳馆风犹在,惭愧宫庭雉尾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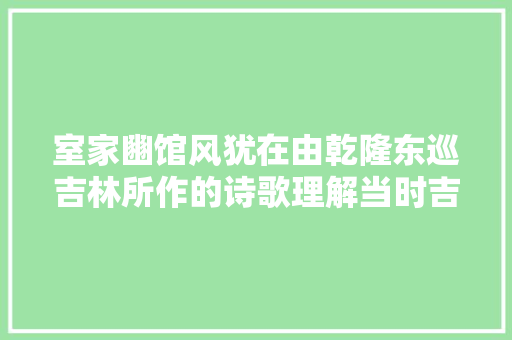
东巡吉林期间,在满族老屋中被称作“额林”的储物隔板,也因“鼠闹欲投还忌器”和“淳厚遗规恭俭德”而引发乾隆的感慨,以诗歌记录了这种吉林城民居里的分外家具。此外,被叫做“周斐”的桦树皮撮罗房(一种桦树皮小帐篷、窝棚)也引发了乾隆的兴致,作诗《周斐》以记录,并发出“五侯第宅皇州遍,芮鞫先型尔尚知”的感怀。
二
1957年,作家曲波创作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正式出版,小说中匪首座山雕盘踞的老巢是一个叫做威虎山的险要之地。这座山岭的名字并非是“威严老虎”的意思,而是满语“威呼”的另一种写法。“威呼”满语意为整根原木刳、刨而成,仅供几人乘用的独木舟。威虎山实际含义是“像小船一样的山岭”。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威呼”一贯是吉林城江面上常见的一种船只。乾隆帝惊异于旗兵、牲丁在山林采参、佃猎时,常拖拽一条“威呼”同行,碰着河流阻拦,便放“威呼”下水渡过,于是赋诗《威呼》:“取诸涣卦合羲经,舴艋评量此更轻。刳木为舟剡木楫,林中携往水中行。饱帆空待吹风力,柔橹还嫌划水声。泥马赊枯(满语,小桦皮船)尤捷便,恰如骑鲤遇琴生。”
虽然乾隆东巡到达吉林城时是夏秋之际,但他还是见到了人们在雪窖冰天中往来来往奔跑的交通工具——“法喇”。“法喇”即爬犁,“似车无轮,似榻无足,覆席如龛,引绳如御,利行冰雪中”(乾隆的《法喇》一诗原序)。在冬季,人们利用爬犁,利用冰雪增滑,或马拉,或牛牵,或人拽,载人、运货,行动如飞。虽然未能看到爬犁在皑皑白雪中行驶,乾隆还是写了一首《法喇》:“架木施箱质莫过,致遥引重利人多。冰天自喜行行坦,雪岭何愁岳岳峨。骏马飞腾难试滑,老牛缓步未妨蹉。华轩诚有轮辕饰,人弗庸时奈如何。”
三
清代,在吉林城常见的“斐兰”“赛斐”“施函”“霞绷”“罗丹”,如果不是乾隆写诗记录下来它们的用场,单看这些满语词汇,如今的人们肯定搞不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
“斐兰”是满语,指小孩利用的以柳木和榆木制成的弓,与之合用的是满语为“钮勘”的小箭。乾隆在吉林城内目睹许多小孩用“斐兰”练习射箭,深有感触。为勉励旗人从小练习骑射,终年夜后为国家效力,乾隆作诗《斐兰》:“榆柳弯弓弦檿(yǎn)丝,剡荆作箭雉翎翍(pī)。壮行幼学率由旧,蓬矢桑弧匪袭为。揖让岂知争君子,闿抨惟觉惯童儿。曾闻肃慎称遥贡,可惜周人未解施。”
乾隆东巡吉林时,或缘于渔猎民族旧习未改,或缘于陶、瓷、金属餐具比较宝贵,吉林城百姓的生活中还保留着一些比较原始的餐具,如长约四寸、被叫作“赛斐”的木匙。这让使惯了牙箸瓷勺的乾隆非常惊异,乘兴做了一首《赛斐》,对木匙的样子和利用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质古惟称以木为,曲长且椭进餐宜。鼎中底用轻问鼎,座里应教笑朵颐。无下奢哉嗤彼箸,有捄便矣藉兹匙。青泥坊底芹喷鼻香处,杜老居然得句时。”
在吉林城生活的数日,无论是“可供瓶罍(léi)谢梁栋,孰非造物善栽培”的“施函”(木桶,用以装粮食、贮水和盛酒),还是“闺秀争能守炉火,儿童较远骤寒冰”的平民传统玩具“罗丹”(“嘎拉哈”),都让乾隆兴致盎然。他文思泉涌,佳句频出。特殊是“蓬梗为干,抟谷糠和膏傅之”,以代烛燃之,青光荧荧,烟结如云,俗称糠灯的“霞绷”,更是引发了乾隆对勤俭的认识和体会,发出“最爱焰辉一室朗,那辞烟染满窗乌。葛灯笼是田家物,勤俭遗风与古符”的慨叹。
四
吉林城地处白山松水之间,为吉林将军辖区首府。辖区内丰饶的特产集聚城中,人参、貂皮、东珠、松子、鲟鳇等,是进贡皇室的特产。东巡吉林期间,乾隆在原产地见到了这些特产,欣喜非常,写了许多诗作,记录这些特产以及为得到这些特产人们所进行的劳作。
在《貂》一诗的序中,乾隆提到“乌拉诸山林中多有之,人以捕貂为恒业,岁有贡貂额,第其等以行赏”。这段描述出自《吉林外纪》,《吉林通志》中则记为“索伦人以捕貂为恒业”,但序言已解释“乌拉诸山中”,以是诗歌描述的应该是吉林城的环境。《东珠》一诗中,在赞颂东珠品质赛过南珠后,乾隆提到“取自珠轩供赋役,殊它蜑(dàn)户效殷勤”。在《采珠行》中,乾隆不无感慨地写道:“旗丁泅采世其业,受餐支饷居虞村落(大乌拉虞)。我来各欲献其技,水寒冻肌非所论。”
无论是捕貂人还是采珠人,都属于清皇室内务府设立于吉林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统领的“牲丁”。“珠轩”是管理牲丁的劳动组织(《满族大辞典》中称“轩达”),每珠轩30人旁边,设珠轩达(达,在满语里便是头、长之意)1人,卖力捕鱼、捞珠及采蜜、打松子等各项采捕任务。打牲乌拉下辖牲丁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从乾隆期间开始,“上三旗"所属珠轩共65个,采捕之物交给内务府;“下五旗”所属珠轩共45个,采捕之物交给王府、贝勒府、贝子府。珠轩达合计110名,管理牲丁3993人。
这些牲丁(打牲旗人)与吉林城驻防旗人的生产、生活办法不同。驻防旗人在不服兵役期间,以耕种旗田为主。牲丁则需肩负兵役之外的采捕、贡赋等劳役。在“大雪遥望铺一色”时,奔波“窝集(满语“山林”)林中各种松”之间“打松子”者(出自诗歌《松子》),“蹲岸钓难投美饵,凿冰射要系长缗”进行捕鱼的人(出自诗歌《鱏鳇鱼》),都是吉林城内辛劳劳作的打牲牲丁。这些底层旗人承受的生活之苦,绝非乾隆“松江打鱼亦可不雅观,潭清潦尽澄秋烟”(出自诗歌《松花江捕鱼》)描写的那样赏心悦目。乾隆在记录吉林城丰富的特产时,也使底层百姓生活之辛劳跃然纸上。
乾隆东巡吉林,还创作了一些纯粹记录百姓生产办法的诗歌,如《豁山》。满语“豁山”也写作“花伤”,汉译为“纸”。在诗歌的序中,乾隆写道:“夏秋间捣败苎、楮絮入水沤之成毳,沥芦帘匀暴为纸,坚韧如革,谓之豁山,凡纸笺胥以是名之。”一如诗歌正文所言“捣苎沤麻亦号笺,粘窗写牍用犹便”,在吉林城,用纸张裱糊室内墙壁和在入冬时粘贴窗户缝,是人们不能省略的生活细节。为替代品质优秀的高丽纸,吉林城百姓很早就开始制作相对廉价的“豁山”。这生平产场面被乾隆瞥见,遂用一首诗歌记录了吉林城某间造纸作坊匠人们的生产场面,成为那个时期吉林城已存在造纸这项手工业的旁证。
五
乾隆在吉林城期间所作的诗歌,成书于道光六年的《吉林外纪》与成书于光绪年间的《吉林通志》在记载上颇有差异,民国版的《永吉县志》大体上沿用了《吉林通志》的记载。《貂》和《东珠》两首诗歌,虽然出自《盛京当地货杂咏十二首》,但从内容上看,所指为吉林城特产。这两首诗歌该当是他在盛京(沈阳)完成的。
其余,乾隆创作的这些诗歌,无论是序还是正文,《吉林外纪》和《吉林通志》在记载上也有差别。以《拉哈》一诗为例,《吉林外纪》中的序为:“圬墙所缀麻也。筑土甃坏为墙壁,以横木约尺许为一档,缀麻草下垂,缘之以施圬墁,耐久不倒,亦国初朴素故俗也。”《吉林通志》的序则为:“土壁堵间缀麻草,下垂缘以施圬墁。此国初,过涧芮鞫间故俗也。”《吉林外纪》的诗歌正文为:“层层坏土砌为墙,缀以沤麻色带黄。妇织男耕斯室处,幼孽壮作旧风蘉(máng,勤奋,努力)。底称凿遁颜家阖,漫喻操嘻圬者王。故俗公刘傅芮鞫,九重此况慎毋忘。”《吉林通志》的诗歌正文则为:“乘屋居间事索绹,经营妇子共勤恳。御寒塞向诸凡预,施墁编麻要取牢。出气天窗(即气孔)柱旁边,通烟土锉炕周遭。室家豳馆风犹在,惭愧宫庭雉尾高。”
《吉林外纪》为私人撰写,年代略早。《吉林通志》则为官修,年代略晚。且《吉林通志》所录《拉哈》等诗一起组合为《吉林乡俗杂咏十二首》,有单独的序,疑《吉林通志》中的诗歌为乾隆修订之后的定稿。因此,本文引用的诗歌正文皆以《吉林通志》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