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川妈
10月16日,在一众明星的银幕演出中,有部“扞格难入”的电影,悄然上映。
它形式分外:第一部上岸4K院线的古典诗词主题文学记录片。
它排片极少: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加起来不到两万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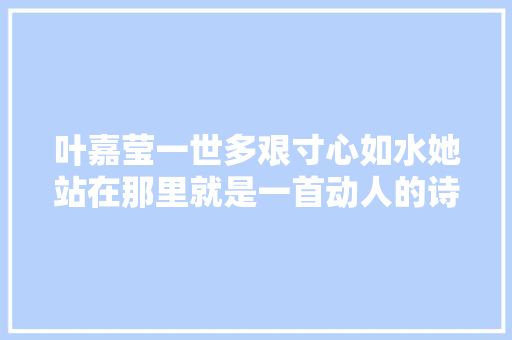
它口碑爆棚:从威信媒体、文艺杂志,到影视公号、普通不雅观众,都颔首夸奖。
即便是对影片拍摄颇有微词(线索散乱、空镜莫名、流于表面等等)的影迷,也无不感慨于主人公巨大的人格魅力,唏嘘于她与诗词之间贯穿近百年的深深羁绊。
这部电影,叫《掬水月在手》,讲述了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传奇生平。
叶嘉莹这个名字,对古诗词有所理解的人,一定都不陌生。
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代宗师,用毕生心力,阐释和传承古典诗词之美,并用特有的腔韵,将吟诵的魅力展示给更多人听;
她生于北京、嫁于南京、搬家台湾、侨居北美,期间亲历山河破碎、背井离乡、身陷囹圄、天人永隔之苦痛,仍寄情诗词,才华纵横、渡人无数;
她曾在台湾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顶尖学府执教,后毅然归国授课,如今已96岁高龄,捐出全部财产3500余万元,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被尊称为“师长西席”;
她关心儿童的语文学习,坚持要选精良、真实的作品,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从诗词歌赋中,体会到草木鸟兽、天地人间的万千宇宙,从而生出关怀,生出爱心,生出丰沛的感情……
董卿在《朗读者》中这样评价:“(叶嘉莹)是很多人通往诗词国度的路标和灯塔。”
而叶嘉莹却说:“柔茧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自己只是吐丝的春蚕,已垂垂老矣,若年轻一辈能将这蚕丝织成锦缎,让文化流传和发扬,便无憾了。
这位与诗词相伴生平的贤人君子,她的背后,又有着一段若何平仄起落的人生故事呢?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书喷鼻香世家,祖上中过进士,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在航空署深受看重;母亲也颇有学识,曾任学校老师。
生于农历荷月(六月)第一天的她,得到了一个饱含家人爱意与期盼的乳名:小荷子。
▲童年的叶嘉莹(右)与两个弟弟
这朵才露尖尖角的小荷子,全体童年险些都是在自家的四合院中度过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由于守旧的祖父以为,不能让女孩子到表面的学校去读书,会学坏。
于是,在家长的教导下,她认字辨音、诵读诗书,进而练习作诗填词。家里的哀求是:可以学习“新知识”,但必须遵守“旧道德”。
逐渐终年夜的叶嘉莹,如那个时期的万千女子一样,久居深闺、含羞内敛、不善言辞,但她细腻慧敏的心思,却总能在笔下的诗文中表示。
1940年时,16岁的叶嘉莹写下一首五言绝句《咏莲》:
植本出蓬瀛,
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
何以度苍生。
既有“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宋·周敦颐)”的高洁,更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菩提偈》唐·慧能)”的清明,弗成思议这样一篇诗作,竟出自一个花季少女之手。
大概,是她有感于“小荷子”的意义,愿做花中君子;
大概,是她明白了力量源于人的内心,不可假托他人;
大概,是当时的她,已亲耳听到了卢沟桥的声声炮火,已亲眼见过了长安街上的日本军车,已体会到家园沦陷、风雨飘摇的悲惨苦涩……
这个曾不闻窗外事的小诗童,究竟飞快地终年夜成人。
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隔年的1941年,对叶嘉莹而言,充满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这一年,她考入了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终有机会碰着了影响自己生平的老师,顾随。
顾随是大家景而仰之的国学大家。银幕上,叶嘉莹对老师的回顾,却很是生动:
“他那个时候才四十多岁,看起来却像是个六七十岁的小老头。
北京的冬天很冷,他就穿得很厚,一件棉衣,一件皮袄,一条厚围巾,一顶大呢帽,到了教室,一件一件脱下来,才开始讲课。
他上课没有教案讲义,常常写上几个字,与诗文完备无关,从此展开发挥,上天入地,见物起兴。”
叶嘉莹听顾随讲课,“如困室飞蝇,蓦见门窗开启”,从此醍醐灌顶,极大开拓和提高了她对诗词赏析的眼界,终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
顾随也很欣赏叶嘉莹的文学才华,曾表示,已经把所有创作的方法和品鉴的道理传授给了她,期许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拓,能自建树。
1943年,市价抗战关键期间、民族死活存亡之际,顾随受英国墨客雪莱《西风颂》中“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的启示,写下“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与学生们共勉。
叶嘉莹借用老师的诗句,作出一阕《踏莎行》:
烛短宵长,月明人悄,
梦回何事萦怀抱。
撇开烦恼即欢娱,众人偏道欢娱少。
软语打发,阶前细草,
落梅花信今年早。
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而几十年之后,在顾随先生长西席的遗作之中,竟也创造了一阕用上这两句的《踏莎行》:
昔日填词,时常叹老,
如今看去真堪笑。
江山别换主人公,自然白发成年少。
柳柳梅梅,花花草草,
面前几日风光好。
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
个中的韵律和意象,与叶嘉莹当年之作,似有应和。
影片中,女声和男声分别诵读着二人的词作,直至末了一句,蓦然契合,师徒俩的深厚情意,呼之欲出。
▲叶嘉莹(右二穿白旗袍者)与恩师顾随
实在,当顾随写下这首词的时候,师生二人早已失落联多年——1948年,叶嘉莹随供职于海军的丈夫来到台湾,人生急速被看孩子、煮饭、打杂填满。
初期,两岸还能通信,而之后的全面封锁,让“一湾浅浅的海峡”隔绝了多少音讯、生出了多少乡愁。
顾随听说爱徒的处境,发出“造物忌才”的悲叹,此后余生,竟是没能再见上一壁,更未曾知晓,叶嘉莹继续了他的衣钵,传道授业,桃李天下。
这些,都是后话了。
▲顾随与国文系41级学生合影(后排右五为叶嘉莹)
而纠缠叶嘉莹大半生的“风雪寒冷”,自此席卷而来。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有人曾说:“人间至悲至哀之事,叶师长西席全都经历过。”
这至悲至哀的源起,莫过于母亲的去世。
1941年,叶嘉莹的母亲查出肿瘤,须要开刀。当时,父亲已在随民国政府的辗转中杳无音讯,母亲就在舅舅的陪同下,去天津租界里找西医做手术。
原来以为很快就能团圆,却没想到,母亲手术后不幸血液传染,病情恶化,心中牵挂尚未成年的三个儿女,执意要回家,末了,在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之上,放手凡间。
叶嘉莹说,这是她第一次感到人间无常、去世生相隔。
在为亡母收敛尸首、举行葬礼的悲痛欲绝之中,叶嘉莹写下了八首悼亡之诗,或追忆音容笑脸,或质问上天绝情,字字泣血,声声垂泪。
而这首《哭母诗·其一》,最让我动容:
噩耗传来心乍惊,
泪枯无语暗吞声。
早知一别成千古,
悔不当初伴母行。
原来,在母亲去天津的时候,叶嘉莹本想随行,被母亲极力劝阻,就没再坚持,倒是以,造成了生平中最深的仇恨。
影片中,夜晚深巷里,年轻女子失落魂独行的背影,配上诗文的诵读,此情此景,让人感同身受、黯然神伤。
而后,叶嘉莹终于等到了与父亲的相逢,又南下南京,与丈夫赵东荪举行了婚礼,不久就迁去了台湾。
那时,纯挚的她,不知道这一走,便是几十年的游子流落,随身行李只有两个皮箱,里面装的,险些都是关于诗词的条记。
▲叶嘉莹结婚照
婚后平淡却宝贵的生活,叶嘉莹并没能过上太久:1949年,“白色胆怯”笼罩台湾,叶嘉莹的丈夫被捕入狱。
已是飞来横祸,却还雪上加霜。不久后,警察局又带走了叶嘉莹,虽然很快就被放了出来,但她失落去了学校的事情和宿舍,无家可归,只好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投奔亲戚。
每夜,辗转反侧在别人家走廊的地铺上,叶嘉莹把阔别家乡、仰人鼻息、母女相依、出息未卜的满腔悲怆,终极化作一首《飘蓬》:
飘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夜阑忍泪吞。
丈夫出狱后,脾气大变、蛮横暴躁,索性不再事情,养活一家老小的重担,落在了叶嘉莹瘦弱的肩头。
她白天传授教化讲诗,回家做饭打扫,深夜挑灯备课,日子过得极累极苦,时时都经历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磨难。
▲叶嘉莹(中间穿旗袍者)与台大中文系学生合影
叶嘉莹说,看不到希望的自己,曾想过就这样结束生命。
在至暗时候,她硬是靠着诗词的力量,靠着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一点一点挺了过来;而她满满的才华,也受到学界的赞誉,更让美国的汉学家慕名而来,约请她客岁夜洋彼端授课。
叶嘉莹带着家人一起,踏上了离故土更远的异国他乡,几十年的光阴弹指而过。
她在多所顶尖学府留下足迹,一边自学措辞和文学理论,一边向那些深眼窝、高鼻梁、对东方文化不甚理解的学生,通报着中华古典诗词的美。
▲叶嘉莹(中)与汉学家候思孟(左)、海陶伟(右)
事情顺利、研究有成,两个女儿也终年夜成家。大略的幸福,彷佛在历经了千百次的苦难之后,终于姗姗来迟。
但命运,却仍是那无法反抗的可恶命运,给予了年过半百的叶嘉莹以沉重一击。
1976年,叶嘉莹的大女儿和半子,在出游途中遭遇车祸,双双罹难。
几天前,刚在出差途中匆匆见过一壁的孩子,再见,却已是天人永隔。
▲叶嘉莹夫妇与新婚的大女儿、半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叶嘉莹,强抑着痛不欲生的心情,赶去多伦多收拾后事,然后,把自己关在家中数天,谁也不见。
由于,此时任何宽慰的话语,都只会引发更大的悲痛。
而在以泪洗面的日子里,叶嘉莹谱下一首又一首《哭女诗》,寄托对早逝女儿夫妇的万般哀思,疗愈内心的淋淋血口:
万盼千期一旦空,
殷勤抚养付飘风。
回思襁褓怀中日,
二十七年一梦中。
平生几度有颜开,
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
不令欢笑但余哀。
“天以百凶造诣一词人。”这句出自国学大师王国维之笔的谶言,是叶嘉莹的真现实遇。
而这句话,后来也被叶嘉莹引用,不着痕迹地为自己作注。
历经由各种生离去世别、世事无常,她对诗词与人生,有了大彻大悟:
“过去,顾随师长西席曾说过:以悲观之心情过乐不雅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奇迹。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会,痛极之后,才逐渐明白。
要懂诗词,大概真的是要身经由忧患,才会有很深的感悟和理解。大概我写的诗词,你们以为也还有美的地方。可是我那一柱鲛绡,是用多少忧闷和困难织出来的?
不管有多少苦难、灾害,我都可以承受,而且我坚持的操守不会乱,我的内心也可以不受打扰。
我们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便是让我们的心灵不去世。”
这份感悟,正好呼应了影片中朋侪的话:
古诗词救了她。
她碰着什么困难,诗就能把她渡过去。
在选择承受命运之重、直面人生不幸的同时,一个动机,在叶嘉莹的心中悄悄成长:“我更加怀念我的故乡,我想回家。”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谈叶嘉莹其人,便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她首创的“弱德之美”。
我们的文化之中,常常颂扬的是“健者之德、强者之德”:
有不服世道、敢于反抗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有志向高远、心存天下的“安得广厦千万间”;
有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我以我血荐轩辕”……
但,“德”的表现,向来不同。既有“健者之德、强者之德”,便也有对应的“弱者之德”。
叶嘉莹阐明过个中含义:“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便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质,才是弱德。”
而“弱德之美”这四个字,她用自己的人生,做了最好的诠释。
叶嘉莹曾说,她这一辈子,没有做过自己的选择,险些每一个决定,都是随波逐流、形势所致。
因家教而学诗、因义气而嫁人、因任务而渡海、因养家而赴美……别人眼中,她有崇高的头衔、等身的著作、卓越的造诣;却是只她自己知道,表象之下,都是命运施加在她身上的浩大困厄。
她未曾做出过勇者般的还击,未曾试图扼住命运的咽喉,仅是在重压之下,默默地承受着,悄悄地坚持着,缓缓地前行着,不跌倒,不跪屈,不放弃。
惟有对诗词的热爱,和对家乡的思念,是她负重前行的“弱德”之中,俏丽的华光。
南台景致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1951年于台湾
故都北望海天遥,有夜夜梦魂飞绕。
——1953年于台湾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1968年于美国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愈甚年时。
——1969年于加拿大
从南到北,辗转流落,日昼夜夜,游子望乡。叶嘉莹把内心中的思念倾倒而出,倾倒在自己的诗与词中。
她思念祖国,思念北京,思念长安街上那座养大了她的四合院,思念院儿里的花花草草、秋日竹菊,思念那个摇头晃脑诵读着诗词的小荷子。
而这份思念,终于是等到了回应。
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建立外交关系,在随后几年中互设领馆、开放签证。叶嘉莹得知后,急速动手申请返国探亲,并终于在1974年景行。
她取道喷鼻香港,买了各种探亲礼品,乃至买了一台电视机,一个人拖着大包小包,坐一趟长长的火车来到关口,再随着人群过关,到广州乘上了去往北京的飞机。
影片中,叶嘉莹在回顾起往事时,脸庞带笑,眼里有光:
“飞机快降落的时候,我从窗户向下看,看到一排通亮的灯火。
我就在想啊,难道那便是我家所在的长安街吗?
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三十年来只能常存于梦中的归乡夙愿,终于在踏上故土的这一刻,化为了沸腾的热心,匆匆使她挥笔写就了20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银翼穿云认归京,遥看灯火动乡情,
长街多少经游地,此日重回白发生。
……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这趟探亲之旅,武断了叶嘉莹的想法:返国,用自己的措辞讲授最爱的诗词,让文化的根脉能在故乡的土壤里延生。
叶嘉莹说,只有这个决定,是她生平中所做的,属于自己的选择。
于是,她给中国的教诲部写了一封信,申请自费返国讲学。
在去邮局寄信的路上,要穿过一小片树林。溜达在林间,看着夕阳的余晖穿过树叶,听着晚归的飞雀阵阵鸣音。
“落日终将没入阴郁,倦鸟仍有窝巢可回,而已知定命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真正的家园呢?”叶嘉莹想着,一首七言绝句《向晚》涌入脑海:
向晚幽林独自寻,
枝头落日隐馀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
谁与安排去住心。
改革开放后,叶嘉莹的申请被批准,返国教书的夙愿得以实现。她开始奔忙于中国和加拿大的两地,暑假在中国上课、办讲座,开学后在加拿大完成教授的本职事情。
这一奔忙,就又是三十多年。
期间,叶嘉莹曾托人,在祖国的东北方探求一条河流,叫作叶赫水。
原来,叶嘉莹的“叶”,源自于“叶赫纳兰(叶赫那拉)”。她幼年时候,从伯父口中得知:自己是满洲镶黄旗下,却并非满族人,而是蒙古族人。先祖的部族迁徙到了叶赫水边,便取河流之名为氏。
在背井离乡的流落中,她一贯在想:叶赫水还在吗?我还能看到它吗?我还能回到它的身边吗?
2002年秋日,年近80岁的叶嘉莹,终于来到吉林省梨树县,站在了心心念念的叶赫水边,站在了叶赫古城的遗址之上。
她望着劲风中的野外,望着雾霾中的秋阳,回过身来对同行者说:“这不便是《诗经》里的《黍离》吗?”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央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现在的心情,和诗中写的,千篇一律。”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席慕蓉,心中感慨:
“就在这个看似荒漠的地方,叶师长西席却遇见了那一首三千年前的诗。
这次相遇,又一次照亮了这首诗。
由于这次原乡中的相遇,叶师长西席授予了三千年前就被写就的那些笔墨新的意义。”
▲叶嘉莹(左)与席慕蓉(右)在叶赫水旁
在千百年纪月前留下的字句之间,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共鸣,找到连接,找到沟通的桥梁。
踏足桥上,会见到那些诗词大家,从白纸黑字的书本上生出鲜活的血肉精气,锦带洒脱,甩袖转身,对来者报以知音一笑。
心有戚戚,乐哉!
幸哉!
而这,正是诗词歌赋的魅力,也是叶嘉莹坚持讲学著述、研精究微的缘故原由。
诗词能渡人,人,亦要渡诗词。
莲实有心应不去世,千春犹待发华滋
2014年,时年90岁的叶嘉莹,终于结束了奔波,从此定居在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内。
▲叶嘉莹(右)为迦陵学舍揭幕
“迦陵”,是叶嘉莹的号,也是她的笔名,本义是指佛教中的一种神鸟,声音美妙,婉转绕梁。
巧合的是,影片中用了一阕叶嘉莹自作自诵的《鹧鸪天》:
广乐钧天世莫知,伶伦吹竹自成痴。
郢中白雪无人和,域外蓝鲸有梦思。
明月下,夜潮迟,微波迢递送微辞。
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词的背后,有一个关于蓝鲸的神话故事。听说,两头蓝鲸,纵然相隔数千里的茫茫汪洋,也能通过呼鸣,与对方通报信息。
叶嘉莹阐明说:“我留下的这一点海上遗音,大概将来有一个人会听到,会冲动。现在的人都不接管,也没紧要。反正我便是留下来,就这样。”
不管是迦陵妙音鸟,还是遗音海中鲸,叶嘉莹,都真真做到了“人如其名”,用迷人的讲述,通报着诗词的美妙,在讲台前一站,便是七十多年。
很多文学界的大家,比如墨客席慕蓉、作家白先勇、已故台大教授柯庆明,等等,皆是在她的古典诗词课上得到启迪。
▲从左至右:席慕蓉、白先勇、柯庆明
影片中,墨客痖弦,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以前,台湾的新墨客和旧墨客抵牾很大。旧墨客嫌弃新墨客写诗有病句、没章法,新墨客说旧墨客老土过期,思想陈腐。
两派人不太来往,过端午节,都不在一个桌子上吃粽子,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纪念你的屈原,我纪念我的屈原。
后来,叶嘉莹揭橥了文章,以一个古典诗词学者的身份和角度,肯定了当代诗的优点。
(在叶嘉莹的影响下,)新墨客和旧墨客逐步开始在端午节时、在一张桌子上吃粽子了。”
▲痖弦
神奇如叶嘉莹,不仅沟通了新墨客和旧墨客,还沟通了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文学理论,把只可融会不可言传的奇妙之处,以有逻辑的论文做出剖析和解读。
返国后,叶嘉莹更是哺育门放学子无数,春晖四方。
她初在南开授课,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台阶上、讲台边、窗户上都是人,蹭课旁听的同学们戏称自己是“挂票”。
哪怕后来学校规定“持听课证方可入场”,大家也有对策:用萝卜刻假章假造证件,不想错过一节课。
▲叶嘉莹与南开众教授合影
即便,是没有听过叶嘉莹讲课的人,也能在她所著的诗词讲解文集之中,收成莫大的教诲。
我在豆瓣上,读到了网友Viking的动听留言:
“1998年,我从一所理工类大学退学,在县城里租了间半地下的屋子,过一个人的生活,自学文科,准备再次参加高考。
我在书店买了一本《唐宋词十七讲》,那时候我19岁,险些可以说是第一次打仗诗词。我被震荡了,每天薄暮的时候,坐在一条河边,对面是一望无际的菜地,我大声地把险些整本书读了下来,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美妙的天下。
我不知道叶嘉莹是不是最好的,但我对她充满了感激,一贯以来,在我心里:诗词便是叶嘉莹。
多年往后,我也进入了出版行业。当我操持把当年的《迦陵作品集》重版的时候,创造已经有人疾足先得了。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诗词便是叶嘉莹”,这简大略单的七个字,大约已经说尽了岁月,讲清了生平。
如今,叶嘉莹已经是96岁高龄,岁近期颐。
但镜头里的她,依然思路明晰,表达清楚,谈起过往时沉着淡然,谈起生活时好奇未泯,谈起诗词时斗志昂扬。
她不敢生一点点的病,却仍关心青少年的教诲状况,有机会就外出授课演讲,每次一站,便是一两个小时。
近年来,叶嘉莹积极推动和参与的事情,便是复兴古诗词的传统吟诵。
她说:“吟诵,是一种细致的、创造性的、回味式的读书方法和表达办法。”诗歌中“赋、比、兴”传染民气的力量,皆能透过吟诵来表现,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墨客的心灵,藉着平仄起伏的声音,达到深微密切的互换和感应。
现在,传统吟诵的方法险些失落传,诗歌的生命正在减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叶嘉莹,只愿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留下录音资料,给予支撑自己走过忧患的古诗词,一个不悔的交代。
有一次讲诗词时,她转过身,望着台下的莘莘学子,有感而发:
“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瞥见。”
这位不辞劳苦、推开门扉的贤者,把不懂诗词的人接引到殿堂之内,也把古代墨客的心魂和空想,传达给下一代。
她在渡诗词,她也在渡人。
在南开,叶嘉莹写下一首《浣溪沙》:
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
荷花凋尽我来迟。
莲实有心应不去世,人生易老梦偏痴。
千春犹待发华滋。
市价秋日,叶嘉莹途经校园中的马蹄湖,看到莲花凋落,却并不用极。
由于她知道:莲花结了莲蓬,里边有莲子,落在土里边,来年,又能着花结子了。
回顾九十余载,恍如一梦,叶嘉莹将那个陪伴生平的乳名“小荷子”,当做了坚守的君子之道:
“我希望,我有一颗莲子落在泥土之中,它能萌芽长叶,往后大概,会再逢春天,长成另一棵莲花。”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叶嘉莹如是说。虽经历了半生起落坎坷,小小的心脏却能像水一样,柔韧、澄澈、从容、不绝,鲜与万物争,只向自我的目标涓涓流淌着。
而今,她又在用自己如水的生命,倒映着遥不可及的天上寒月,让人们得以手掬一捧,细细端详那些未曾理解的天相,离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每一位诗士词家,近一点,再近一点。
大概,命运真的是沉重的车轮,是滚滚的洪涛,总会推着我们向无法预见的方向前行。
但若能找到心中所爱,找到精神寄托,便能点亮那盏心灯、看见那轮明月,在苦痛中不灭,在困难里长明。纵然重压在肩,也不会被击垮崩溃,而是在困境里,一步一印,从荆棘之中走出一条踏实的路。
或者与叶嘉莹一样,是诗词歌赋;
或者,是音乐绘画、措辞数学;
或者,是任何可以给予支撑、给予保护、给予救赎、给予发展、给予希望的事物。
愿每一位孩子,都能在人生中,找到那盏心中的灯火,找到那捧手中的玉轮。
参考资料:
[1] 叶嘉莹(口述),张候萍.红蕖留梦[M].三联书店,2013
[2]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叶嘉莹.荷花五讲[M].商务印书馆,2015
[4] 熊烨.叶嘉莹传[M].江苏公民出版社,2018
[5] 艾江涛.96岁叶嘉莹,把即将失落传的吟诵留给下一代[J].三联生活周刊,2020(37)
[6] 电影《掬水月在手》及预报片、片花、采访花絮
[7] 叶嘉莹历次演讲笔墨记录
川妈说说
开选题会时,小伙伴提出推举《掬水月在手》这部记录片,我立马举双手附和。实在太敬仰叶嘉莹师长西席了,很想把她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父母、孩子。纵然很清楚地知道,推举这样的记录片没有热点效应,依然选择绝不犹豫去做。
只是没想到,写出来竟然有将近1万字,还非常不像母婴公号的文章(虽然我们常写这么长的文章)。但实在是喜好,舍不得删减一点。
读叶嘉莹师长西席的“弱德之美”,觉得自己很像她。从没愤青过,不咋呼不张扬,看上去朴实平淡,乃至有些温吞,一贯随遇而安、顺流而下;但真正熟习我的朋友都说,我是很有态度和力量、很拼很坚持的人。
以前只有儿子时,我不太希望像我,更期待他激情亲切张扬,活得震天动地。但现在有了女儿,又开始希望她更想我一点,平淡的生活中逐步收成弱德之美。
拓展阅读
妈妈狂晒女儿千张丑照,张张丑出天涯,10万人看过却说好想生女儿
四个女儿,个个有才嫁得好,他才是值得学习的国民岳父
mom看天下:随着二胎博士妈妈一起学育儿、看天下;这儿既有我所崇尚的自然生活分享,还有独家的科学课程、阅读课程;来吧,养娃路上永久缺个好朋友!
。对啦,目前我在“头条号、"大众年夜众号”两个平台发布文章,名字均为【mom看天下】,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