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辛晓娟(步非烟) 中国公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作家
记录:范语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人物简介:辛晓娟,中国公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百家讲坛》主讲人。紧张研究领域为隋唐文学、诗体学等。出版作品《杜甫歌行艺术研究》《天上何曾有谪仙·李太白外传》《人生得意在长安·诗说大唐》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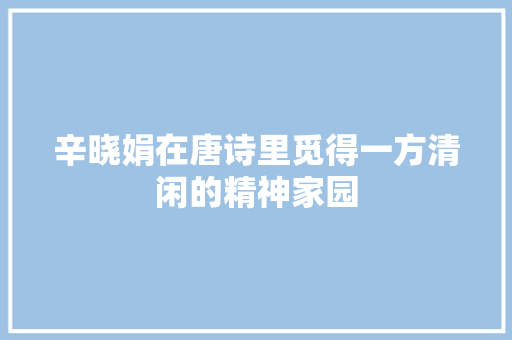
相信很多读者第一次知道并记住辛晓娟,可能是由于她很酷的笔名“步非烟”。这个来自唐传奇中的名字,总令人遐想起独步天下、既浪漫又飒爽的女侠。而在近日对辛晓娟的采访中,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印证了这种遐想——谈起自己热爱的中国古代文学,辛晓娟飞扬的神采与声音里,的确流露出唐人一样平常的大气与诗意。
21世纪之初,辛晓娟凭借当代武侠小说创作走入大众视野,并以奇诡的想象力斩获了一批“铁粉”。而在回归学术,于中国公民大学任教10年后,她带着新书《人生得意在长安》再飨读者,以诗说史,带今人体味大唐风骨。与古代文学相遇相伴的路上有多少很多多少感悟?她期待读者在新书里看到唐朝若何的时期画卷与精神天下?以下,是辛晓娟的讲述——
是作家亦是学者,皆因爱上古代文学
我与古代文学的缘分,可能起于儿时的阅读经历。我成长于一个普通家庭,能够读到的书本资源有限。那时恰好遇上港台武侠小说在内地的盛行热潮,这也是我当时打仗到的最多的课外读物。我会创造武侠小说里包含很多古诗词和中国历史的背景,比如《神雕侠侣》开篇便是元好问的词,《射雕英雄传》里有靖康之变那段历史。这些小说引发着我对古代历史和文学的兴趣,我会找一些比较浅近的干系书原来看,比如普通的历史故事、《唐诗三百首》的小册子等等。高中时,我常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书,当时图书馆里有几排书本是不对学生开放的,后面的书架平时都用一根绳拉起来,可能是西席阅读的区域。我还记得,那时的我除了借阅各种推理小说、国学书本外,还会抱着强烈的好奇心,悄悄“钻”进西席阅览区,躲在里面读各种“闲书”。这些从武侠小说而起的阅读,滋养了我最初对古代文学的喜好。
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我选择了古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在大学阶段,我一边进行系统的知识积累,一边开始武侠小说的创作。古代文学硕士毕业后,我有两年从事全职写作的韶光。由于自己在写作上小小的天分,加上当时纸质书市场还不错的机遇,我的创作之路比较顺利,幸运地让不少读者认识了我。对付究竟连续全职写作还是回到学校做研究,我经历过一个纠结的过程。终极我还是选择连续读博、做研究,由于我以为做一个学者能够兼顾我的两个爱好。现在想来,文学创作者的体验的确给予了我研究古代文学的独特视角,而无论作为作家还是学者,皆出于我对古代文学的热爱。
在浩瀚的古代文学海洋里,隋唐文学最吸引我。我总以为人的性情气质和研究工具彷佛会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在少年时期的阅读中,无论是李白的豪放不羁,还是李商隐的怅惘迷离,那种浪漫的气息都是我钟爱的。在北大中文系里,在我的导师钱志熙教授,以及袁行霈老师等前辈大师们的讲授和启示下,我创造隋唐文学不像先秦文学那样古远,也不像明清文学对我们来说那么熟习,而是带着恰到好处的神秘感。也正如魏征在《隋书文学序》中所说,经由南北朝期间的民族大领悟,隋唐文学呈现出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特质,达到了“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田地。于是,从年少时的懵懂憧憬,到十余年来的研究专攻,隋唐文学在我心中始终有巨大的魅力。能够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找到与自己精神共振的古人,去靠近他们、研究他们,于我而言是莫大的乐趣。
从古今共通的情景出发,搭建诗与史之间的桥梁
我的新作《人生得意在长安》原来是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的讲稿,当时的节目选题“诗说唐朝”属于“诗说中国史”的系列。由于解读唐诗的专业书本已有很多,因此,我不想把这本书写成我在学校的传授教化稿,想找到能触发读者更多感想熏染的角度,以感性的“诗”来呈现理性的“史”。
于是,我决定带着读者,从今人与古人都同样关注的那些场景、故事和情绪出发。书中将21首随处颂扬的唐诗名篇按照“路上×宦旅”“宴聚×友朋”“佳时×节庆”“边塞×宫廷”“历史×声名”这5个主题归类。无论是岁时佳节的欢庆、朋侪相聚的喜悦,还是离乡在外的打拼,都是本日的我们依然会体验的情绪。比如在讲到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时,我希望与大家一起去体会,一个来自边陲小城的青年,第一次来到当时“天下上最恢宏的城市”长安,穿行在150多米宽的大道上时,内心会有若何的震荡?又会去如何描述自己看到的奇不雅观?而在初读孟郊《登科后》的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时,我们会以为他太“狂”了,但如果我们把自己代入孟郊的平生——考试“屡战屡败”,一起苦读的“考友”都上岸了,自己还在苦苦挣扎,他一朝得中的狂喜也就不难明得了……我希望,大家通过我的解读回到墨客详细的创作情境,在认识一首诗的同时认识背后的人。
走近墨客的经历和感想熏染,也就走近了他们所处的时期。当我们看到逐年记载的史实史料时,或许会以为那些年份和事宜有些乏味,但通过诗歌,我们关注到的是古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比如唐朝某一年的经济状况和物价如何?某一年的盛行时尚又是什么?我们也会关注到历史的年夜水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例如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如何深远地改变着普通读书人的生活?可以说,诗歌既是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微不雅观史”,折射着伟大的时期画卷。我所做的,便是力争建立起文学与历史之间的桥梁,从文本中看到时期的变革,让文学更丰富,也让历史更详细。
新书出版时,我用了“人生得意在长安”作为书名,这里的长安,不仅指唐朝的繁华都城,而是代表着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人生得意”也不是指统统都尽如人意,而是一种名贵的人生态度。如果从唐代墨客的精神天下里提炼这种人生态度,我以为可以用三个词概括:首先是自傲,他们不仅笃信自己的才华,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更名贵的是,他们相信自己的才华可以改变天下,豪情万丈的李白自不必说,就连诗风沉郁抑扬的杜甫,都曾写下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尚淳”这样的诗句。其次便是自洽,在有机遇时积极地施展才华,但在人生遭受打击时,能够洒脱地退守,无论命运沉浮,内心自有豪情,就像刘禹锡在失落意之时依然吟唱着“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还有一点是自省,唐代人的自傲不是盲目的,而是伴随着不断地思考和自察,通达心灵的沉着,这一点在中晚唐的诗作中表达得更多。在自傲、自洽和自省之中,唐代人的精神天下是丰满、武断和原谅的。我想,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在面对时期的变动,人生的悲喜时,亦能在唐诗中找到启迪,觅得一方清闲的精神家园。
唐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值得被关注
作为女性学者和作家,我以为性别视角对付不雅观察古代文学很主要。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唐宋期间的女性文学,此前开设了“唐宋女性文学研究”这门课程,后来又与研究明清文学的老师一起合开了古代女性文学的课程。
可以说,对付女性写作而言,唐代是非常分外、非常主要的一个时段。在先秦和魏晋南北朝期间,也涌现过一些女性作家,但她们要么是地位非常高的女性,比如春秋期间的许穆夫人,是一国之君的夫人;东晋期间的谢道韫,出身名门;要么便是民间的歌妓歌女。但是到了唐代往后,普通市民阶层的女性开始节制文化,节制文人诗写作的方法,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后世所称的唐代三大女墨客——薛涛、鱼玄机、李冶,实际上都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女性,但她们的诗作都是按照文人诗的传统来创作的。这就证明,唐代的妇女教诲相较于以前,更多地向中下层女性辐射。因此,在唐代,我们既可以看到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这样富有知识和政治才干的宫廷女性,也可以看到一批得到教诲、进行创作的普通女性,她们共同造就了唐代女性作家群体的发展、繁荣。我们熟习的《全唐诗》,收录了女墨客100余位,诗歌作品600余首。
女性作家数量长足增长的同时,唐代女性创作的视野也更加广阔。在女性还不能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年代,唐代女墨客的目光早已超越了社会对她们的定义和约束,她们的创作不仅表示了日常生活,也有心怀家国天下的表达。薛涛评论辩论吐蕃战役的时候,能够写出“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的诗句,其眼界与肚量胸襟令人感佩。因此,我始终认为唐代女性的文学创作是文学史上的主要征象,她们与她们的作品,值得被更多人关注和研究。
这些年来,除了科研与创作,我也在积极参与古代文学的遍及事情,包括担当《中国诗词大会》的题库专家、《经典咏流传》的文学顾问,也包括在《百家讲坛》讲唐诗。我深深感到,随着民族自傲心的不断提升,大家对付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经典文本越来越关注。当时,录制《中国诗词大会》时,全民对诗词的喜好度、参与者们的诗词储备量和节目的反响之大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并没有在学院中念中文系的人,有强烈的欲望和须要去学习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因此我认为,专业的研究者该当更多参与到古代文化的传播和遍及中,让诗词这个凝集着民族情绪的宝库,真正“飞入平凡百姓家”。这亦是我整理出版《人生得意在长安》这本书的一点初衷——让我们一起回望诗意大唐,共同触摸那穿过千年的力量与聪慧。
任务编辑:李丹萍
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缺点或者陵犯您的合法权柄,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jp.jiupai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