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省北部,有一座名山,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为追寻她的足迹,到此一游。关于咏“庐山”的诗词,不甚列举,在我们小学教材里便选入了两篇,其一是盛唐“诗仙”名作《望庐山瀑布》,其二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题西林壁》。同样是文坛年夜师,同样是咏庐山,到底谁的功力愈甚一筹?
一、作品的比较,亦是作者的较劲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两首绝世佳作。
《望庐山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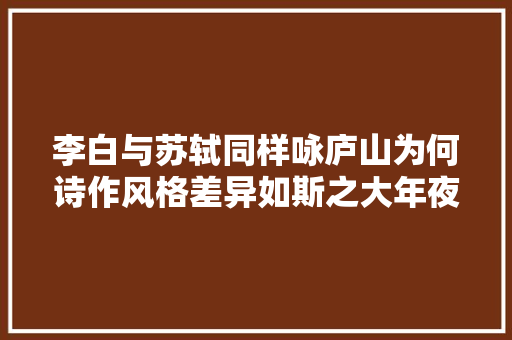
【唐】李白
日照喷鼻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这首小诗采取极具夸年夜的手腕,将面前庐山的景致描述得淋漓尽致,意象丰富,鲜活,情绪浪漫,这是李白一向的风格。
《题西林壁》
【宋】苏轼
横算作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孔,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这首诗对景致的诠释就委婉很多,诗中透着成熟与理性,充满哲理与感悟。李白写诗时年近五十,但诗中的心境仿佛是个年少浮滑的游客,对世间万物充满希冀,而苏轼诗中的心境却是饱经风霜洗礼,看淡世间岁月变革,沉淀出来的那种厚重感。
作品都是由人写出来的,我们要真切的理解他们的作品,就必须先理解作者的人生境遇。
1、出身背景:若论家世,李白不如苏轼
李白的生世,至今是学术界的一个谜,他的家族状况,我们都不甚理解,就连出生地都有很大争议,有史可寻的是李白少年期间居住在绵阳江油一带,他天赋异禀,“五岁诵六甲”,传为佳话。
李白受道家文化影响,喜好剑术,行走江湖像个身手高强的游侠。家境该当不太好,二十四岁便辞亲远游,一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很洒脱,说得难听一点就像个“无业游民”,每天吊儿郎当,吟诗作赋,不务正业,这一点李白比苏轼更接地气。
苏轼,号“东坡居士”,出身名门世家,其父苏洵善于写论文,亦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的《六国论》选入中学教材,苏轼还有个弟弟苏辙,亦是才华横溢,父子三人堪称文坛泰斗,撑起北宋的半边天。
可想而知,苏轼的生活环境远比李白优胜,书喷鼻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年少期间的苏轼犹如“温室里的花朵”,接管正规的教诲;而李白好比一个“流浪汉”,靠天赋异禀,自学成才,出人头地。
2、作者名气:一个是“天才”,一个是“全才”
李白是公认的天才,斗酒诗百篇,秀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就连“诗圣”杜甫都是李白的小粉丝,对李白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赠李白》
杜甫
秋来相顾尚秋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文人之间的相互唱和是诗坛雅事,杜甫给自己偶像写过15首诗,而李白回答杜甫的却寥寥无几,这便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间隔。也不丢脸出,李白当时在文坛的地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李白是长安酒馆的常客,贺知章常常与李白约酒,尊称其为“谪神仙”。李白的作品构思奥妙,天马行空,常常出人意料,只有他有这个胆识和蔼魄,敢把瀑布比作银河。
除了写诗,李白的在文章方面也有建树,以一篇《行路难》备受贺知章青睐,并举荐他为翰林学士,也只有李白这样的天能力力写出这般独特风格的作品。
苏轼与李白比较,虽然论天赋可能比不上李白,但通过勤学苦练,在文坛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容小觑,说他是个“全才”一点都不夸年夜。
魏晋期间的曹丕说过“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古代,写诗歌出类拔萃算不上特殊精良,要文章写得好,才厉害。
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要知道这个头衔的评比标准不是指名气,也不是指诗词创作,而是写文章。苏轼在文章上的造诣可以说略胜李白,他的《赤壁赋》、《范增论》、《记承天寺夜游》等等,都深入民气。他的文章与当时的欧阳修、王安石齐名,造诣颇高。
苏轼的豪放词在北宋文坛的地位自不用多说,诗也是一绝,比如他游西湖时写的这首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
宋·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合适。
除此之外,苏东坡在字画上的造诣亦超凡入圣,他善于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等人并称书法上的“宋四家”。绘画方面亦巧夺天工,提出了“士人画”的观点,将诗与画相领悟,传世画作有《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李白与苏轼,“天才”与“全才”,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3、作品有名度:《望庐山瀑布》入选《全唐诗》,《题西林壁》收录在《东坡七集》
李白的这首诗是对大好河山的赞颂,历代名家对其讴歌有加。清代的宋宗元在《网师园唐诗笺》中写道“非身历其境不能道”,李白的这首诗传誉外洋,就连日本的近藤元粹在《李太白诗醇》中直言“亦是面前喻法,何以使后人推许?试参之”,外国人都争相模拟,可见李白这首诗的名气之盛。
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他嬉戏庐山写过的诗作中最经典的一首,毛谷风赞誉此诗反响“当局者迷,察看犹豫者清”的人生哲理,游国恩亦在《中国文学史》中大赞苏轼此诗的“理”性,提要挈领人生。
以有名度来看,李白这首诗被唐宋往后到清朝这段期间的人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而苏轼这首诗在古代被“轻视”,但在现当代学者眼里却是难得的佳作。
李白
二、体味“浪漫”,感悟“哲理”
李白是浪漫主义墨客,他的诗歌特色便是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气息。而苏轼的诗看重情与景的交融,看似写景,实则入情入理,让人回味悠长,品读诗,便如品人生。
(一)意境
1、同咏庐山,侧重点不同
李白写庐山,从视觉上直不雅观的描写看到的景象,“日照喷鼻香炉生紫烟”,阳光照耀在喷鼻香炉峰上,烟波浩瀚,如临瑶池。“遥看瀑布挂前川”,远不雅观庐山瀑布,悬挂在天边,气势恢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采取极其夸年夜的手腕,将面前的瀑布比作九天之外的银河,境界之大,视野之广,古往今来,唯有他一人敢用这般夸年夜的姿态去诠释所看到的景象。
李白通过意象的刻画,侧重于对景致的描写,将庐山的面貌描写的入木三分,诗很有带入感,欣赏这首诗,如临画境一样平常,这便是李白诗歌的魅力。
苏轼写庐山,从各个角度去看待面前的景物,从侧面对庐山进行刻画,他诗中并未直接描写看到的景致有多壮不雅观,有多恢弘,而是由远及近,阐述人生哲理。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苏轼看似在写庐山,实则在写人生,在感慨世事。
同样是咏庐山,李白比较直接,苏轼则十分委婉,借旁边而言其他。
2、李白重景、苏轼重情
前面提到,李白在写庐山景致高下足了功夫,选用气势非凡的意象,勾勒出了如诗如画的瑶池,这也与他个人的风格相同等,写景就纯挚的写景,对大好河山的赞颂,对大自然的赞颂。这一点上李白更像一个“直男”,而苏轼却显得更有“城府”。“城府”在今人看来或许是个贬义词,而用在苏轼身上却觉得不到一丝恶意。苏轼长于不雅观察,感悟人生,将情与景融于诗中,这是他的风格,亦是他的特色。正如《定风波》中写道“回顾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场再自然不过的雨,在墨客眼里都能感慨世事无常,人生变幻。
苏轼 剧照
(二)笔法
1、李白一气呵成,苏轼娓娓道来
从艺术手腕来看,李白这首诗,一气呵成,由所见之景生出的无限感慨,前后四句衔接得恰到好处,毫无违和感。阳光照在喷鼻香炉峰上,飞泻的瀑布挂在其间,仿佛银河落入九天,全诗极尽夸年夜,恢弘,却丝毫看不出刻意雕琢的痕迹,李白所选用的字句,都能让人欣然接管,一点不突兀。虽然全诗都在惊叹庐山瀑布之雄浑,但你却读不出“拍马屁”的意味。
苏东坡《题西林壁》四句诗,由远及近,描写庐山的全貌,感情细腻,娓娓道来,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诠释末了一句诗彰显的哲理。这首诗的主题不是庐山之美,而是通过庐山,看到人生中的自己,回顾过往,统统都如梦如幻,自己全然不知,只有局外人才能看清。
李白是句句点题,苏轼用循规蹈矩的办法来引出诗的主旨。
2、《望庐山瀑布》夸年夜浪漫,《题西林壁》意味深长
纵不雅观这两首绝世佳作,各有千秋,李白夸年夜的手腕,后人望其项背,遥不可及,诗的意境在于如画一样平常,极具画面感,读者有身临其境的觉得,在脑海中浮现出庐山瀑布的景象。论笔法技艺,无人能出其右。
苏轼或许知道在笔法上难以超越李白这高超的技艺,以是剑走偏峰,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描写庐山,你写景,我便写情、写理,在这一方面,苏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略占上风。
庐山瀑布
三、两首顶峰之作,亦是时期的象征
1、《望庐山瀑布》写出盛唐之气候
李白身处盛唐,正是诗歌繁荣兴盛的时期,大唐国力壮大,李白诗中亦尽是对大好河山的赞颂,丝毫没有伤感、失落落之意。
一个时期的兴衰繁荣,从文化上便能看出来,若非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诗歌文化又怎会发展如此迅速。在大唐呈现出了好多有名的大墨客,而李白无疑是满天星河中最刺目耀眼的一颗明珠。
李白晚年写的这首《望庐山瀑布》,丝毫没有对芳华流逝,人生苦短的感叹,相反是极度享受当下的生活,可见盛唐之气候有多壮不雅观。
李白这首诗也代表着盛唐期间诗作的顶峰,在咏物方面,没有人能超越李白,只有他独特的夸年夜风格,将诗词之美,推向顶峰。
2、《题西林壁》承前启后,开拓诗词新视野
苏东坡身处北宋,一个崇文的时期,文学气息浓厚,但国力衰微,外忧内患。
苏东坡长于改革与创新,在唐人的根本上,他将诗意与哲理相结合,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冲破古人固定思维,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局势。
《题西林壁》便是最好的例子,承前启后,汲取古人对事物描写的手腕,再加上自身的人生境遇,让诗充满哲理与厚度,引人寻思。
诗歌发展到了苏东坡这里,就不再是纯挚的咏物写景,而是向多元化发展,或言志,或抒怀,或明理。可以说,这是诗歌创作的进步,也是时期的进步。
庐山
结束语:
李白与苏轼这两首诗,虽然都是咏庐山,却大不相同,各有利害。在咏物写景上李白绝对是王者,苏东坡无法企及,但在抒怀明理上,苏东坡确实技高一筹,独具一格。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们不能凭个人喜好去主不雅观臆断事物的利害,正如苏轼《题西林壁》中阐述的道理,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你们以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