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给我的信,收到多时了。由于正在写一篇别的东西,放不下手,迟迟奉答,甚是抱歉。
您要我谈谈这次和国画家们到表面跑了一趟有些什么体会,在国画创作——尤其山水画方面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现在,就个人肤浅的体会,想到哪里就扯到哪里,随便谈谈。
去年玄月,美协江苏分会组织了以江苏国画院为中央的“江苏国画事情团”出省参不雅观、访问,目的是:开眼界,扩胸襟,长见识,客气向兄弟省市学习,从而改造思想,提高业务。一行十三人(六十岁以上的三人:苏州余彤甫,无锡钱松喦,镇江丁士青;五十岁以上的两人:我和苏州张晋。这是我们此行中的“五老”。此外都是青壮年)扶老携幼,军队不算大也不算小。我们的生活圈子大都非常狭窄,尤其我们几老,多数长期范围在“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江南,个别的还是由于此行才第一次渡过长江。
王维《渭城曲》诗意,27.9×40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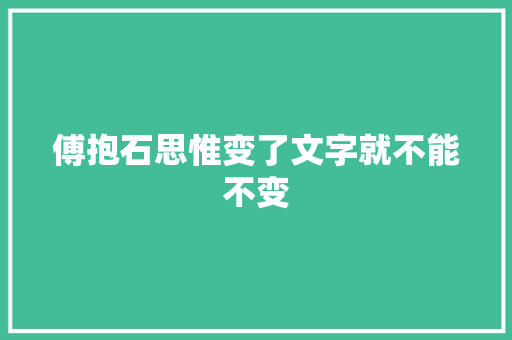
我们是先到郑州的。先后访问了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西岳、成都、乐山、峨嵋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前后三个月,包括来往路程大约旅行了二万三千华里;参不雅观了祖国伟大的工业培植;访问了不少全国有名的公民公社;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韶山毛主席故居,炭子冲刘主席故居,重庆的红岩村落、曾家岩,长沙的净水塘,以及武汉、广州等地的革命遗址;游览了龙门石窟、西岳、峨嵋山。此外便是和各地的兄弟协会、艺术院校举行不雅观摩与漫谈。在这些活动的同时或空余韶光,有条件则勾勾画稿,大家节制,没有规定。
建国十一周年的国庆节,我们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过的。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莫大的幸福。同时又深深地感到在延安只管只有四天,却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诲。凤凰山、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毛主席和中心领导同道的住院,党中心办公的地方,我们都逐一瞻仰过……看到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心领导同道那种非常简朴、非常艰巨的生活,饮水思源,大家莫不肃然起敬。延安您是熟习的,我想见告您一个小插曲:国庆节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阳,照得延安分外俏丽。我和钱老不谋而合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桥,只见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两岸的杨树,虽然已是深秋景象,还是那么绿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峦起伏,雄浑极了,动人极了。钱老欣然说:“若是把延安如实地画出来,人家一定要说我画的是江南了。”一点不错,陕北江南,差不多了。您相信么?这统统统统……包括后来瞻仰过的许多革命遗址,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却。
巴山夜雨,1944年,92×60cm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培植的发展,不但出身了不少新的俏丽的城市(像三门峡市),旧城市的变革也是十分惊人的。这次所走的地方,别的不谈,四川是我曾经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尤其重庆,抗日战役期间,整整八年半,难道还不足“老资格”?一起上,我总喜好向同道们谈四川这,四川那,表示自己“硬是得行”的样子。谁知一到成都,连“祠堂街”也找不到了。这还可以体谅,成都只住过一个短期间。“重庆看我的吧”。哪晓得重庆的变革更大、更彻底,自己出门都要请人带路,别的就不必谈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看到的自然很有限,也很表面,然而对我们特殊是几位年事较长、长期在旧社会混过的人来说,一方面是欢畅惊叹,一方面又是感念万千。
登山图,18.6×51.3cm
伟大祖国的大好形势和美好、幸福的远景,深深地教诲着我们,鼓励着我们。它绝不是苏东坡说的“烟耶云耶远莫知”那样,而是大家从亲眼得见、亲耳所闻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加以肯定的。九分钟出一部拖沓机;一部机床要装三十几个火车皮;一个公社为了全国一盘棋,志愿节约一些,外调了一千多万斤粮食;到处是培植工地,绿荫中还不断送出雄壮的歌声来;还有,过去又脏又闹而现在已是花园般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到晚上就灯烛蔽天,展览、演奏,诸般杂耍,要吞吐好几万劳动人民的广州市文化公园……生活在如此幸福的毛泽东时期,便是我们画山水的,难道还会有人留恋那“古道、夕阳、昏鸦”么?
为什么?现实的教诲,思想的变革。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
乱帆争卷夕阳来,1943年1月,106×57.5cm
就我们此行来看,在西安和成都还不怎么样。到了重庆,据个人浅薄的意见,变革的苗头逐渐露出来了。我对大家是比较熟习的;同行的各位的笔墨,不加任何款识,我也能清楚地指出来。可是在重庆的不雅观摩会上,却有好几幅使我犹豫了。我不好意思直接请教诸老,只悄悄地牵个年轻的同道过来,问:“这是谁的?”“这是丁老的。”原来古人早就说过“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我愉快极了。我们的这种“变”,是气候万千、热火朝天的现实生活的启示和教诲。从业务的提高来看,则不过是万里长征的一个蛙步,间隔形势的哀求还差得太远。
我们一起,不管是火车上、轮船上、旅社里还是古庙里……只要大家凑在一起,就读读报纸、谈谈政管理论,或者聊聊一些有关业务上的问题。没有固定的会议形式,也不作任何的结论,大家随便谈。但谈得最多的自然是有关业务——如何把国画创作提高一步,如何打破自己的水平等等问题。
听瀑图,1945年,109×530.7cm
当我们从西岳脚下玉泉院上山向娑罗坪进发的时候,不久就峰回路转,看到排列在前面高耸云真个西峰,真是壁立千仞,奇峭无伦。忽然后面有人年夜声叫着:“哈哈!
这才办理问题呵!
”那种愉快的感情,的确用笔墨很难形容。本日想来,“办理问题”固然有待于今后不断的努力,而对付长期生活在平畴千里的江南水乡的山水画家,对付长期沉潜在卷轴几案之间的山水画家,一旦踏上了“天下险”的西岳,您能禁得住不惊喜欲狂吗?于是大家的谈锋很快地就集中在明代以画西岳得名的王安道(即王履,他名作《西岳图》现存)身上。您一句,我一句,不经意处倒牵扯到不少如何体会古人和若何表现时期气息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继续与发展精良的绘画传统问题。多数认为王安道的《西岳图》是有生活根据的,一定程度上传达了西岳的气概、面貌,是祖国一位精彩画家。也有的从“皴法”来研究问题,认为西岳最突出的是“荷叶皴”,过去在《芥子园画传》看到的固然完备不是这么一回事,便是王安道的《西岳图》也意多于法,并不若何范例。记得钱老从北峰一下来,来源就说过:“我本日找到真正的‘荷叶皴’了。”我赞许同道们的见地。我们从《西岳图序》里,也清楚地知道它不是无动于衷地仅仅把西岳抄录了下来,而是画了之后很不满意。怎么办呢?于是就把它(西岳)“存乎静室,存乎行路,存乎床枕,存乎饮食,存乎外物,存乎听音,存乎应接之隙,存乎文章之中……”(《西岳图序》),放到全体精神生活里面去,反复洗练,不断揣摩。等到“胸有成竹”执笔再画确当儿,自然而然地就“但知法在西岳,竟不知平日之所谓家数何在!
……”(同上),完成了有名的《西岳图》。我们后来在游峨眉的时候,也是这样“三步一停、五步一搁”,边走边谈,边谈边画。只管减头去尾,不成系统,但都是从亲切的现实感想熏染出发,也是从急迫哀求办理问题的心愿出发。我相信,要不是跑这一趟,呆在家里是无论如何谈不出来的。
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意,20×53.8cm
于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有助于理解传统,从而精确地继续传统;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笔墨技法,不仅仅源自生活并服从一定的主题内容,同时它又是时期的脉搏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反响。我以为,这一点在本日看来哪怕是不很巩固的体会,却清楚地、有力地推动了画家们思想上的尖锐斗争——对自己多年拿手的(习气、节制了的)“看家本钱”开始考虑问题。这是极为名贵,极难堪得的。所谓考虑问题,绝非说“看家本钱”全要不得,笔墨全没用了。决不如此。而是由于时期变了,生活、感情也随着变了,通过新的生活感想熏染,不能不哀求在原有的笔墨技法的根本之上,大胆地赋以新的生命,大胆地探求新的形式技法,使我们的笔墨能够有力地表达对新的时期、新的生活的歌颂与热爱。换句话,便是不能不哀求“变”。
峡江轮船图,1964年,34.1×45.8cm
我们在艺术实践方面,此行也有两次比较深刻的教训,值得一提。去年玄月二十一日,我们到了“三门峡”,就在三、四天之前,黄河的水经由蓄洪变“清”了。古人说“贤人出,黄河清”,几千年来从来不敢梦想的奇迹,本日在党中心和毛主席的精确领导下,在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冲天干劲之下实现了。为害几千年的彭湃澎湃黄水怒号的黄河,变得一平如镜,清澄碧绿,将永久为公民造福了。我们谁不想把“黄河清”画下来呢?哪知道便是这个“清”字把我们难倒了。大家很清楚,找古人的笔墨是不会有办法的。一欠妥心,还随意马虎画成“长江”或是“太湖”呢!
这是一次。后来,由西安乘汽车到延安去,第二天由铜川开车,将要爬上洛川平原的前后,陕北高原那种雄伟而又朴厚的气候,激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除了陪我们去的石鲁、蔡亮几位画家之外,我们全是第一次的瞻礼者。我们既愉快、又紧张,恨不得争分夺秒地把陕北高原的革命圣地的一草一木都要画出来。事实上,大家也画了不少。可是,本日该当若何画黄土高原,又若何画“陕北江南”的延安?和“黄河清”一样,我们至今没有较好的办理,还是今后要深入生活,付出足够的劳动才能逐渐办理的课题。这又是一次。
车行高处风景,1957年,48.6×57.2cm
我们一起上还打仗到这么一些问题。对付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理解,毛主席的提示是多么精确!
以前也多次学习过,可是本日才从心田里领悟到它是真理。因而不同程度地也意识到光靠笔墨,光靠传统,不办理问题。认为必须思想领先,政治挂帅。记得余老在一次谈论会说过一段比较沉重的话。他说:“我过去有三种病:第一是‘思想顾虑’的病,解放以来,党号召国画要反响现实生活,我也下厂下乡,画了一些,以为差不多了。实际,自己思想上并没有彻底解放,过于吃力或者不十分有把握的东西就不太敢于考试测验,万一失落败,岂不贻笑大方。第二是‘笔墨束缚’的病,我搞了四五十年的国画,习气了的一套笔墨技法,像多年相知相亲的老朋友一样,提起笔就来了。因此,只管主题、内容有所不同,而画面的精神、气息,由于受笔墨的约束,却变革不大。第三是‘贪多、谄媚’的病,见什么就画什么,什么都向画上堆,惟恐别人说画的不‘丰富’,不‘全面’,再加上故意无意的在形式、笔墨上做文章,结果还是跳不出过去的水平。”话犹未了,真是满座为之一震。我们几老都以为自己“三病”俱全。既是通病,于是赶紧研究“履历良方”。通过反复谈论,结果同等肯定:只有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特殊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加紧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加强磨炼,才是最有效的治疗。找到了“殊效药”,满座又信心飞腾,为之一喜了。
仰望古城堡,1957年,67×43.9cm
由于我们“五老”全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正处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过去教教书,画画画,为的是糊口,用不着“走万里路”,乃至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开国十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诲之下,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因而越来越感到党对国画奇迹和国画家们无微不至的重视和培养。曾经是织绸工人的丁老在路上就几次再三冲动地说过:“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不是解放,我再活六十年,也绝对不可能像本日这样得到重视,跑这么多的地方……我真感谢党,感谢毛主席。”一点不错,丁老的话正代表了同道们的共同心意。
和平的图们江,1961年,50×57cm
拉拉杂杂地写了不少了,总之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巩固与如何提高的问题。希望您多多提出宝贵的见地,多多帮助我们。
一九六一年仲春六日,南京
(本文原载一九六一年仲春二十六日《公民日报》《新华日报》《文申报请示》等报刊均转载,后收入一九六二年公民日报出版社《文艺评论选集》第一辑。)
傅抱石|(1904-1965),当代中国画家、美术史论家。原名永生、瑞麟。祖籍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1904年10月5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5年9月29日卒于南京。少时家贫,11岁时,傅抱石跟随邻家刻字铺和裱画店的师傅学习刻字、裱画,为他后来的艺术道路铺垫了最初的基石。后由街邻帮助考入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小。1925年著《国画源流概述》;1926年毕业于江西第一师范艺术科,留校任教。1929年著《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3年得徐悲鸿之助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及工艺、雕刻。1934年在东京举办个人画展,颇得好评。翌年7月返国,任教于南京中心大学艺术系。抗日战役期间,在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任秘书。后定居于四川重庆,连续在中心大学执教。1942年9月在重庆举办壬午个人画展。1946年返迁南京。1952年任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1957年任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美协江苏分会主席、江苏书法印章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公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