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刚被贬谪到岭南惠州时已59岁,身体欠佳,可谓是年迈体弱。苏东坡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十分清楚,且谙熟医药,深知一味名叫“地黄”的药物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但是地黄原产于河南焦作(古怀庆府)一带,属于“四大怀药”之一,岭南地区很少见,故而十分苦恼。
他听闻循州兴宁令欧阳叔向在自家的圃中栽种此药,想起自己在龙川做县令的朋友翟东玉与叔向是故交,于是特意写信请翟东玉代自己求一些地黄寄来惠州。后来,他乃至在自家的小圃里也栽种起这味药来,并且为此作诗《地黄》一首,全诗如下:
地黄
地黄饲老马,可使光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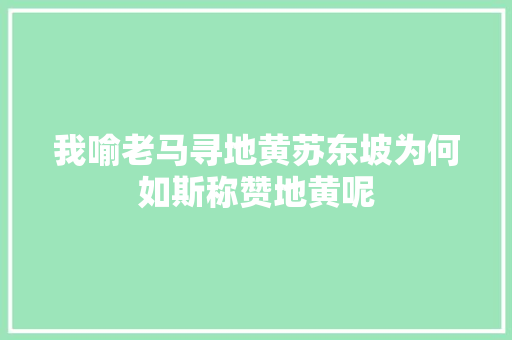
吾闻乐天语,喻马施之身。
我衰正伏枥,垂耳气不振。
移栽附沃壤,蕃茂争新春。
沉水得稚根,重汤养陈薪。
投以东阿清,和以北海醇。
崖蜜助甘冷,山姜发芳辛。
融为寒食饧,咽作瑞露珍。
丹田自宿火,渴肺还生津。
愿饷内热子,一洗胸中尘。
读罢此诗,我们不禁要问,这味地黄究竟是若何的中药,竟得苏东坡如此厚爱,以至于对它念念不忘?
从诗中可以得知,东坡对地黄的偏爱起自于白居易的一首《采地黄者》。晋代医家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记载了韩子治用地黄喂养已经五十岁的老马,此马居然又生了三匹小马驹,一贯活到一百三十岁才去世,后人多效仿。于是灾年便见到穷苦者在野外里辛劳挖取地黄送到富朱紫家喂马,以换取少量的食品。白居易的《采地黄者》便是描述此情此景。
东坡受启示后,便有了食用地黄的动机,他将自己比喻成一匹血气衰微的伏枥老马,希望通过食用地黄,使自己规复康健强健的体魄,如故事中的老马一样平常充满活力。实在,东坡当时的身体状况也比较符合地黄的药用症状。他对自己的描述是“丹田自宿火”,与其年迈而真阴不敷,虚火偏盛有关,常常感到心烦口渴,自觉体内总蕴有一股“热气”。加上他从京城千里迢迢来到岭南,受到岭南独特的湿热蒸郁的景象影响,使得他阴亏火扰,体质状况雪上加霜。
地黄的药用部位为块根,入土为黄色,离土则变黑,汲土中精华而生,因此得名为地黄。据闻,栽种地黄的药田不能年年栽种,要种一茬,休耕八年,否则地力匮乏,药效递减。作为药用,地黄有生熟之分。
生地黄甘寒质润,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对付阴亏血热的病人能够起到左右开弓、标本兼治的浸染,既补益肾阴又清降虚火,十分适宜苏东坡。讲到地黄补益肾阴的浸染,大概大家会遐想到一个专门治疗肾阴不敷的中成药——六味地黄丸,方中发挥紧张治疗浸染的便是地黄。
熟地黄是在生地黄的根本之上经由炮制而得,性味甘温,质地滋腻,能够滋补精血,自古以来便是增强体质、延缓朽迈、治疗一些慢性病及老年病的要药。所谓肾为先天之本,中医里有“久病及肾”的说法,无论阴阳,凡病至极,皆所必至,且人之朽迈的涌现也与肝肾不敷、精血亏虚有关。因此,要延缓朽迈、治疗老年病等,必须主动补益肝肾精血。熟地黄源于生地黄,质地滋腻,性具封藏,善补不消,功专下部,为补益肝肾精血的要药,凡是肝肾亏虚、精血不敷都可用之。
此外,无论是生地黄还是熟地黄都有显著的治疗消渴的浸染,当代研究也证明地黄具有显著的降血糖功效。须要把稳的是,地黄性子黏腻,有碍消化,凡脾虚湿滞、腹满便溏、气滞痰多、脘腹胀痛者慎用,而且多与砂仁、陈皮等理气药同用,以防它太过缓滞的弊处。
选自《药缘文化——中药与文化的交融》
主编:杨柏灿
副主编:祝建龙 李颖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