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刚走出楼门,就听见头顶上方有人喊:“带晌了没有?”是我妈的声音,我朝着窗户回喊了一声:“带啦!
”“晌”是胶东方言,午饭的意思,这个词近些年我早已不用,溘然听见,以为土气中带着一丝默默的亲切。此情此景,很熟习的觉得,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出门被妈妈各种不放心地叮嘱。
吃早饭的时候,妈妈感慨说自己溘然有一种紧迫感,由于她离大舅去世的年事只有9年了——如果她也只能活到71岁的话。4年前妈妈在年度体检中查出肾脏长了肿瘤,确认是癌后终极切除了一个肾脏。关于那次住院,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和妈妈、小姨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欠妥心打碎了要带去医院的陶瓷碗,大家截住了想相互埋怨的话头,沉浸在面对未知的恐怖和焦虑中。后来,当年夜夫遵照流程跟我说手术可能发生的危险时,我脸上的茫然让他以为我大概被吓呆了,便建议换个家属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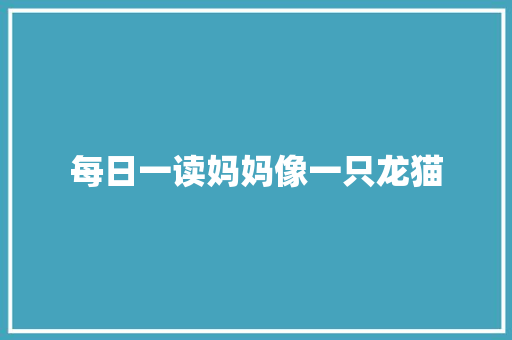
好在统统还算顺利。医院里的那些日子仿佛时空里的黑洞,谁也不愿意多回忆。不过或许是手术后束缚带没有坚持缠,妈妈的刀口处凸出一块肉来,几年后还是如此。妈妈个子高,皮肤很白,近些年来发了胖,肚子上的肉是软的,躺在床上像一只大龙猫。尤其小朋友趴在她怀里撒娇的时候,更像了。宫崎骏的电影《龙猫》里小梅走到树林深处,躺在龙猫洁白的肚皮上睡着了,那一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么大略的电影,却被很多人喜好,或许便是由于它让你感想熏染到了童年的呼唤。
我家小朋友摸着姥姥的肚皮说,姥姥的肚子上有个洞,现在长好了。我也喜好依偎着妈妈,她身上散发着一种让我安心的体喷鼻香,那是属于妈妈的味道,来自迢遥的童年,一贯没有消散过。
我们仨在床上躺着瞎谈天,说了许多重复过千万遍的话。妈妈会提及我小时候她教我的古诗,跟我一起看的童书,我的各种童年趣事。我会背的第一首诗是林升的《题临安邸》,当时未曾理解诗句的含义,只是记得妈妈念“山外青山楼外楼”时的神色和语气,她不算标准的普通话,带着点方言味儿。
我妈并不总是温顺,有时候话说着说着,音量就高起来,让不熟习的人不太习气。我和爸爸倒是习气了她的脾气,而且很早就知道,一个人看上去怒气冲冲的时候,内心很可能是薄弱的。小朋友也会在他写作业的时候,不断分心跟姥姥说:“姥姥你沉着些,再忍忍。”
急脾气的妈妈却有很多朋友。比如,住院期间还特意让我从家里带一个土豆,由于同病房的人打吊瓶手肿了,贴土豆片能消肿;坐了一趟地铁,她还帮助跟妈妈走散的小孩联系事情职员,被一起出行的邻居家小孩当作“年夜大好人好事”写进了日记。我从别人口入耳到这些,心里很为她骄傲。
我没算过我能拥有她多久,也从来不敢去想。不管一个人长到多大年纪,总是须要和惦记妈妈的。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6期)
关注专题 欣赏更多:合集|专栏:逐日聆听 / 逐日一读 文集 - 今日头条
品读年华 | 逐日聆听(音频集)
#【美·听】#
#专题·逐日一读#
#逐日一读·美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