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开封,不仅是爱他的厚重的文化,“一圈城墙围残酷”;头枕淘淘黄河,脚踏一个宋代(余秋雨语),更主要的是我曾在坐落在这里的河南大学学习生活过。我在一首诗里写道:“每一次到开封,我都有难耐得激动,这里有我的母校,这里有老师亲切的脸庞。就连那迎面而来的风沙,也那样使我动情!
”多少次我在母校流连,“静立铁塔不雅观落日,独坐城墙看暮沉。更问潇潇夜雨灯,几次读书到更深?”.
我爱开封,最爱是河大。那宁静的校园,古典的建筑,夕阳下的铁塔,晨光中荡漾的湖水,还有湖畔读书的学子,溜达沉思的教授,每当我忆及这统统的时候,我便想起王文金老师来了。他只教了一段韶光的当代文学。可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受他任教韶光是非决定的。我常常忆起王老师给我们上诗歌时的情景,常常忆起他讲述李洪程的诗《斗天图》的情景。有一短韶光思念的深了,以至晚上难以入眠,心想,何时能再听王老师讲课啊!
大约是1996年5月,阔别近二十年后,我在已任校长的王老师的办公室里,见到了王老师。当他一头银发涌如今我的面前时,我切实其实不敢相认,这哪是二十年前一头乌发、一身中山装、四十多岁的王老师?但我还是从他的眼神中认出了王老师。王老师也认出了我。我解释了来意,希望他给我整理的《云岩寺》一本小册子题个词。他豁达地说:“可以,学生叫我干啥都行!
”说罢,便让人取来了纸笔,写了“伏牛天下名山,云岩天下名刹”。后来这本小册子印出后,白河乡在对外先容云岩寺时常以此书作为宣扬之用。往后无论是出差还是办事,只要到河大,我总要到王老师办公室或家里坐坐。2002年之后,他虽然从校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仍旧从事着学术活动,还带着研究生。记得有一次他请我们用饭,晚饭后他对我说:“你先走吧,我现在精力还行,我要到办公室云校正一篇稿子。”说罢,便匆匆向夜色中的校园走去。
王老师的办公室在河大南门的西边,是一座三层小楼。他在任校永劫就在这座小楼的二层靠东的房间里办公,很普通的一个套间,外间是他接待来访与办公的地方,办公桌对面是一排书架。王老师就坐在办公桌的里面,同我一见如故地谈着话,我在他面前完备没有陌生感,没有丝毫的拘谨。我以崇敬的心情聆听他睿智的话语,每一次发言都有如坐东风之感。他对我讲到对孩子的教诲不要期望过高,不要给他压力,孩子们都有自己的生活道路,相信他们能生存下去。他还谈到他的几个孩子都是靠自己奋斗,自己走的路。每当他谈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默默地谛听,为他的见地所折服。回忆我对女儿的教诲,可能有些期望过高,大概是受了比尔盖茨的影响,他说过,对孩子最大的爱护,是给他创造优秀的学习环境。我常常忆起始终给我以教诲的诚挚的王老师,他那激情亲切的话语,朴拙地对待三十年前的学生的态度,时常使我冲动,有时我想:我是否见王老师显得太随意了,可我一到母校,总还是忍不住去看他。去看他坐在办公桌前,思考着中原文化培植……,窗外,是花木扶疏的校园,一届届学子来了又走了。王老师绐终坚守着他的阵地,播洒着文化,滋润津润着他的学生们。
我爱开封,最爱河大的文化滋润津润。在绿树掩映之中的河大校园外,便是滚滚尘凡的商品社会。可我在这里勾留久了,创造一墙之隔的商品社会由于受河大的文化气息影响,而显得文明、文雅,多了一些书卷气。有一天中午,我在河大西门外的一家小吃店用饭,点了饭之后,见在给顾客结帐之后的老板坐在桌子后面拿起画夹对着前面的一个小女孩画了起来。老板看上去三十多岁,长分头,显得有些斯文。他经营的面馆也便是一间屋子大小,客人也不多,难得有些空闲。一回儿,小女孩母女俩吃完了面,母亲也把稳到店老板在画她女儿,结了帐,便同女儿看店老板的素描,扎着小辫的女儿见自己被画在画夹上,显出一丝羞涩,母亲显得很高兴。她母女显然是来旅游的,向老板道了声谢便掂起行李走了。在繁忙的饭铺里,店老板给顾客画素描这一幕却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去看女儿的时候,时常在河大医学院门诊西边马路旁的一家火锅店吃火锅。这家火锅店因价低味美而很受人欢迎,常常是顾客盈门。大约是24元锅底,若再点几个菜,四口之家,要不了三十无就可热热乎乎地吃一顿。去年秋日的一天晚上,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走进了火锅店,找了个位置坐下后,我被挂在墙上的几幅木板刻字所吸引。见个中的一幅字是这样的:“昨夜西风过秋林,吹得落叶满地金”。字是草书,得仔细辩认方能辨认。听着店外呼呼的秋风,品着这两句诗的意境,我想:这家店老板不是俗人,能在热腾腾的火锅店挂上这副木刻,营造秋的意境,没有一定的文化品位是挂不出的。那一顿饭,我也吃得很故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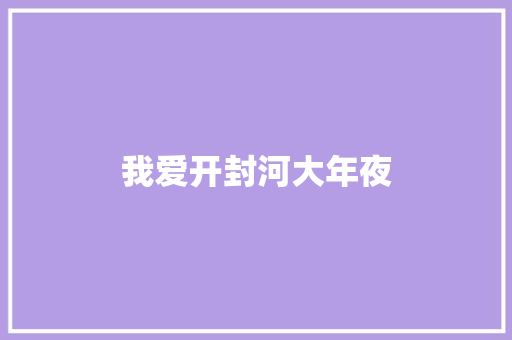
同样故意境的,是我刻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首诗和一阵笛声。诗是我在河大附中院内的宣扬橱窗中看到的。那是一个同学书法作品写的唐代墨客描写梁园的暮春景象:
梁园暮春乱栖鸦,纵目冷落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我是打校院过期有时看到的,却一下记住了。看来好诗是随意马虎记住的。这个学生的作品是用隶体,虽不足老到,但在升学压力下能写的这样也就不易,而他选用这首唐诗更能解释他的文化背景,这个学生不是河大的子第便是开封人。
笛声是我在河大西门外听到的。那是一个夜暮笼罩下的夜晚,中喧华的夜市声中,我挤过小吃摊向河大西门走去,忽然一阵有些淡淡忧伤的笛声传来,我向南面一看,见是在墙角看公用电话的中年人赤着上身坐在破竹上在吹笛。周围是忙忙乱乱的人群,他的公用电话没人光顾,连摆在他身边的杂货摊也无人看一眼,他是为自己的买卖清淡而哀愁,还是原来便是有着悠然情调的人?
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常常在河大西门外徘徊,浑圆的玉轮升起来,撒下清辉笼罩着校园;在朝日初升的清晨,我也曾在校园流连,听鸟声与书声喃喃和鸣。我常想,河大是知识的殿堂,它每天都对开封散发着文明的绿意;河大是知识的大海,微风起时,会溢出一层层浪花,滋润津润干渴的心灵。这便是我爱河大的情由,也是我爱开封的情由。
(2007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