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云:
寒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
酒喷鼻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
江南人把第一次吃青团叫做“尝春”,当东风拂过每一寸乡间野外,那绿色就扑腾扑腾地冒出来了。将最嫩的艾草捣烂为汁,和粉揉团捏壳,封印豆沙、蛋黄等馅料,蒸熟后抹一层油,这出笼后的青团啊,油绿如玉,锃亮一新。四月的江南烟雨朦胧,吃了青团,春天才算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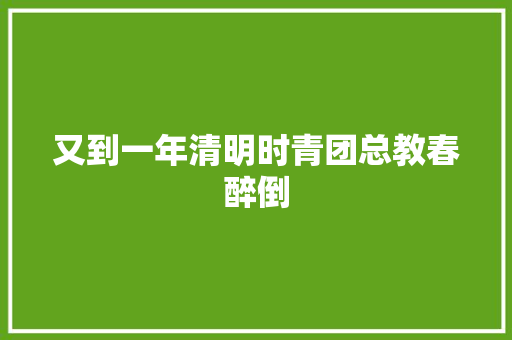
习俗
青团俗称“青圆子”,唯清明前后才有,以是也叫“清明粿”,是江浙沪各地民间清明与寒食节时的一道传统点心。青团和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一样,也有自己的故事。
据考证,“青团”之称大约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相传百五禁烟厨,红藕青团各祭先。”这首《吴门竹枝词》说的便是人们在清明节吃冷食青团,并用红藕、青团敬拜先人。清代《清嘉录》对青团有更明确的阐明:“市上卖青团熟藕,为祀先之品,皆可冷食。”
早期清明团子的盛行与“祓除岁秽”的习俗有关。《吕氏春秋》写道:“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多疫。”为了防治疫病,除了早春的沐浴斋戒,人们还乐意食用喷鼻香草所制的食品,如《荆楚岁时记》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天,取鼠曲菜汁做羹,以蜜和粉,谓之以龙舌拌,以厌时气。”这龙舌拌便是青团的前身。
称谓/形状/馅料
●称谓
不同地区的人们,根据对付青团的喜好为它起好了各种不同的昵称,比如上海宁波叫青团,苏杭叫青团子,南京叫春团或清明团,绍兴则叫清明粿。
●形状/馅料
除各地称谓不同,青团在形状上也有些大同小异。有饼状、饺子状的,而在馅料上,也有甜馅、咸馅的差异。如果有人问,“正宗的青团是怎么做的?”估计能收到100个答案,这些答案都来自长辈的手艺里。
青团有甜馅、咸馅。
甜馅最常见的是豆沙和芝麻白糖。甜馅要加猪油,吃起来才够喷鼻香润。咸馅以春笋、荠菜、马兰头、咸菜、豆干、喷鼻香菇、豆腐、肉丁、油渣等食材为代表排列组合,像咸菜春笋豆干肉丁、马兰头喷鼻香干馅等。
在浙江衢州一带,清明期间食用的是「清明果」,与青团不同,形状为半月形,取的是金元宝之意,分素馅和荤馅,素馅的内里为雪菜,豆腐干,及其他蔬菜。荤馅为土猪肉所制。在杭州,老人收了院子里种的艾草,取其新鲜汁液和面,趁着夜雨频发,摘来春笋春韭,入锅蒸煮,鲜嫩多汁的咸口青团便制霸一方了。
甜馅青团一样平常采取芝麻,豆沙,软糯的外皮与清甜豆沙的结合能让人从今年清明记到明年。作为主流派系的海派、客家、江浙,对付自己家的青团总是能拍着胸脯担保,“我们是最正宗的。”
福州的“菠菠粿”,是用菠菜压榨成汁后混入粿皮制作而成的,造型一样平常以饼形为多,内陷多用枣泥、豆沙等制作,也有用萝卜丝、芝麻、花生为馅的,同样也喷鼻香甜适口。
江西的“清明粑”,馅料范围则更为广泛,榨菜、芽菜、笋干、蒜苗、腊肉等殽杂在一起,调味更多了一分辣味,如果不包在这团子里,恐怕都可以用来炒一份菜饭了吧。
着色
青团的绿,来自江南的艾草。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写到:“捣青草为汁,和粉作团,色如碧玉。”艾草生于早春山野,到野地里一蓬蓬刈下来,细细切碎,用葛布滤出青绿的草汁来,和上筛得均匀的糯米粉,便揉出一团春天最浓郁透彻的喷鼻香。
艾,俗称艾草,艾蒿,艾叶,是田间地头常见的一种多年生野草。全体植株具有浓郁的气味,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爱之如命。从清明到端午,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惊蛰过后,草木兴盛,清明前后的艾草最为鲜嫩,采摘艾草叶,榨成浆,便是制作青团的天然染色剂。而到了端午节,家家户户则会悬挂艾草于门上,以辟邪去秽招纳百福。在日常生活中,艾草常日还被用于喷鼻香薰、针灸、驱蚊,有驱寒温身的功效。
利用艾草制作青团,颜色深绿,带有淡淡中药味的艾喷鼻香。处理时加碱,防止叶子变黄也能更快煮烂。石灰水和小苏打都是碱,起一样的浸染。利用石灰水要避免混入石灰颗粒,现在更提倡利用小苏打。
鼠曲草/麦草汁/菠菜汁/抹茶粉。
同属野菜的鼠曲草,用它制作青团,颜色会浅一些,模糊的喷鼻香气没有中药味。颜色碧绿的青团,多是用麦草制作。
如果自己做青汁会比较麻烦,市情上也有更省事的青汁售卖。与艾草的喷鼻香味不同,是更为清新直白的青草喷鼻香。苏州人更常用麦草制作,有感怀大禹平息太湖水患使得附近好种麦的说法。
现在市情上也有用菠菜汁、抹茶粉制作的青团,喷鼻香味自然是不同,紧张取个色。
思念
吃一口清明团子,品一口故乡情怯。
宋徽宗在北虏期间,清明时见到北方野间成长的茸母(鼠曲草:青团用料),让他想起汴京的茸母,生起无限思乡之情,吟诗一首:“茸母初生认禁烟,无家对景倍悲惨。帝城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泪涟。”国势颓败,一国之君沉沦腐化异域,为臣子为仆众。一样的茸母,做出来的青团却是不一样的味道。
这种对付故乡滋味的无力与思念之情,阔别故土流落在外的旅人也有所体会。每逢清明倍思亲,望得见的故土,望不尽的哀思。承载了诸多典故与诗意的青团,在每年清明上市,身在异域的游子会忍不住购买一二以解馋欲,但终极的味道都不如童年影象里外婆亲手制作的那一枚。
青团的风格始终在改变,谁也说不上来正宗的青团应该如何,它不像嘉兴粽子,宁波汤圆,能被冠以地区之名。但是潜意识里,每个流落在外的人,只认故乡的金字招牌。
以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保存办法,一年四季都可以有青团供应,但是人们更乐意在四月斜雨中去品尝。像是三月“咬春”,四月立柳,端午熏艾。食品与节日之间产生美好的联系,能让青团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沉浮高下,却从未消逝。
更多内容请关注"大众年夜众号:糖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