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不知远郡何时到,犹喜百口此去同。
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存一舟中。
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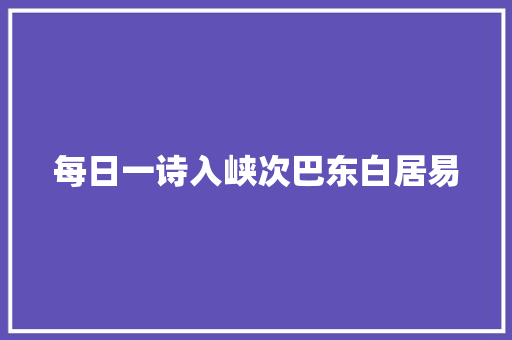
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
这首诗作于元和十四年(819年)三月。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案,上书言事,得罪执政,被贬为江州司马,不久又移官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墨客由江州履新忠州刺史,途经三峡宿于巴东时作。
忠州在当时是偏僻的山区,生产掉队,赋役繁重,公民生活相称困难。这次改受,表面看来是升迁,但忠州偏在远郡,实际上和流放没有多大差别。天涯沉沦腐化之感,苦闷忧伤之情并未完备肃清。以是诗一开头就满腹惆怅,心坎不安地低吟出“不知远郡何时到”。这象口语一样的淡淡一句,不知包含了墨客多少忧伤的感情,细玩之,大有长路漫漫,命运何托,是祸是福,出息未卜的味道。这平平的起句,给后面开拓了广阔的意境。
但刺史的上任,和贬为司马的出行毕竟不同。从年底接诏,到次年三月动身,经由三个来月的准备,能够携同百口,特殊是又有既是爱弟,又是文友的白行简与之同行,不乏明日亲之乐趣,又可会文于舟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慰籍。以是接下去,一扫统统忧伤的情调,提出“犹喜百口此同去”,宽慰之情,溢于言表。异峰突起,波澜顿生,如长风之出谷,似大海之扬波,泪泪滔滔,一泻千里,感情的大门一经打开,再也无法收拢。
“万里王程三峡外,百年生存一舟中”。“万里”极言其远,并非实指,万里迢迢的行程,现在已经到了三峡附近,百口的生命财产尽在舟中,这解释作者这次上任是充满喜悦心情的,是下决心要到忠州作出一番奇迹的,从“百年生存一舟中”可以看出大有“破釜沉舟”的气势,想在忠州大干一场,为忠州公民作一些力所能力的好事。
“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此句直用杜甫“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只改动了个中的两个字,意思并未改变。三峡柔美的景致,宜人的景象,已使人明显地有所领略,江风习习,春雨沙沙,一叶扁舟,出入江上,如置身缥缈的瑶池,似荡漾迷茫的天涯,怅惘忧伤的感情早已抛之九霄云外,轻松喜悦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两片红旗数声鼓,使君髅牒上已东”。船上红旗飘扬,鼓声阵阵,一派山摇地动的气势,急速使人想到,这决不是一样平常平民百姓所能办得到的,也决不是被贬为江州司马时能够享受的报酬。“使君艛艓上巴东”既交代了太守出行的浩大场面,又表达了刚刚摆脱遭贬时屈辱无聊处境的宽慰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入峡次巴东”的题意,迎刃而解,情景交融,天衣无缝。
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四句叙事,交代百口携行是奉王命出任忠州刺史,现已行程过半,到了三峡之外;后四句写景兼抒怀,写出三峡柔美的风光和对太守出行那种浩大场面的喜悦。三峡向来是骚人墨客不断歌颂的地方,墨客途经此地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但这首诗并没有着意去写三峡的险和美,只选取了“沾花雨”和“逆浪风”,这些并非三峡的范例景致,作者之以是选取“雨”和“风”,特殊是“逆浪”,看来是有所寓意的,他知道忠州是偏远贫庸的地方,是准备迎着风浪客岁夜干一番奇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