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作者:洞见·江徐
英国作家毛姆喜好绘画艺术,尤其崇拜印象派画家高更。
当他前往高重生涯过的塔希提岛旅行,亲见画作中的风景,深受震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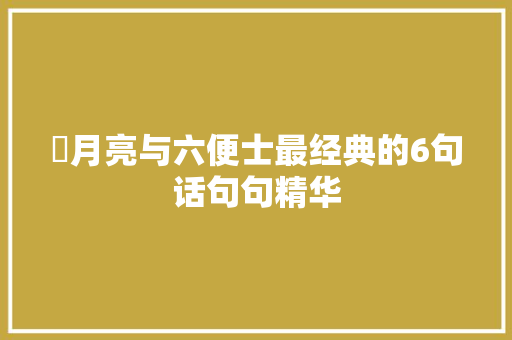
回来后,便以高更为原型,创作出《玉轮与六便士》。
伍尔夫曾评价:“读《玉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
毛姆被誉为故事圣手,不仅善于处理回环弯曲的情节,更善于用精准的笔触,描摹出世情万物,人间百态。
书中这6句话,令人深受启示,回味无穷。
为修炼自己的灵魂,
一个人每天都要做两件他不喜好做的事。
小说中的“我”是一名作家,对生活信奉苦行主义。
为了提高写作能力,“我”每周都要逼自己阅读《泰晤士报》上的文学周刊。只管这件事,对“我”来说很痛楚,就像是进行“严厉的身体折磨”。
这样一个过程,虽然很痛楚,但是对“我”的写作和生活,却大有裨益。
因此“我”把他视为一种有益身心的修炼,每周坚持,从未间断。
书中有句话说得很好:
为修炼自己的灵魂,一个人每天都要做两件他不喜好做的事。
与生俱来的天性,导致我们方向于选择轻松自由的生活,但想要变得更好,必须主动去直面那些令我们痛楚的事情。
做天然喜好的事,是为享乐,做不喜好却有利自我发展的事,是为修炼。
凡是能让你变好的事情,过程都会有疼痛。
真正识破这个天下的人,都是在用苦难修行。
卑鄙与伟大、毒辣与善良、仇恨与热爱,
是可以互不排斥地并存在同一颗心里的。
毛姆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人性只做描述,不做评判。
从某个角度来说,小说主人公史特利克兰是一个渣男、伪君子、自私自利的卑鄙小人。
为追求艺术空想,他带走全部积蓄离家出走,对妻子不管不顾。
对雪中送炭的朋友,他不睬解知恩图报,反而恶语相加。
出于情欲,他勾引朋友的妻子,得到知足后将其抛弃。
当他听闻那个女人仰药身亡,非但没有丝毫愧疚,还说统统都是她咎由自取。
在这一方面,他是个冷漠的忘八。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天才。
为了画出心中的绝美景致,他放下统统,对金钱视若无睹,对名利不屑一顾,超然物外,完备沉浸在精神天下。
他对外界各类熟视无睹,却对艺术保持高度激情亲切,与绝对的诚挚。
屡遭挫败时,他从不气馁,也从未绝望。
面对这样一个个性繁芜的人,人们谩骂他的低劣无耻,又想赞颂他的无畏无惧。
张爱玲曾说:“人性是最有趣的书,生平一世都读不完。”
小时候,我们用年夜大好人坏人这样大略的标准看待天下。
终年夜后创造,年夜大好人实在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坏人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懂得人性的繁芜,我们就不会用非黑即白,大略的二元对立,去看待身边的人;
接管了万物的两面性,我们的心才会越来越原谅、视野才会越来越宽阔。
文明社会中的人,把短匆匆的生命
都摧残浪费蹂躏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不值。
史特利克兰太太是个热衷应酬的家庭主妇。
她常常举办宴会,约请文艺界大佬参加,大家觥筹交错,迎来送往,看起来一派高雅。
一次有时的机会,身为作家的“我”受邀出席晚宴。
在那里,“我”坐观成败了众人见面时的冷漠、吹捧时的虚伪、告别时的如负重释。
主人劳心操心地准备,来宾不嫌麻烦地赴约。
全体过程,大家都在戴着面具敷衍,完成一场礼尚往来的社走运动,很假,很累。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也是如此,费尽心思渴望在社交场合扩展人脉。
但每每宴席散后,那些所谓的人脉,变成了朋友圈里一条条不熟习的新动态。
没有建立在等价交流上的人脉关系,只是空中楼阁。
人生苦短,与其把韶光耗费于无聊应酬,不如在独处中积蓄能量。
《请停滞无效社交》中的一句话,说得到位:
结识很厉害的人的方法很大略,那便是让自己成为很厉害的人。
当一个人掉进水里,
他拍浮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
反正他得挣扎出去,不然就得淹去世。
史特利克兰离家出走后,“我”受他妻子委托,去巴黎讨要说法。
但见面往后,史特利克兰只是一贯在重复一句话:
“我必须画画。我必须画画。我必须画画。”
那情景就像是溺水,而画画,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因此,他已经顾不了家人的感想熏染,也无暇再去公司上班,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画画。
对他来说,画画成了一件不由自主的事。
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曾埋有梦想的种子,但有些种子被生活的噜苏践踏,永久无法生根萌芽。
但有些民气中的种子一贯在悄悄成长,对他们而言,那种子是海岸的灯塔,更是救命的稻草。
当种子破土而出的一瞬间,他们将用全部热心,去灌溉它长成参天算夜树。
美国的摩西奶奶本是一名家庭主妇,平时卖力操持家务,打点农庄,日子过得平淡宁静。
然而到了古稀之年,她却放下统统,毅然决定学画画,八十岁的时候,她在纽约举办个人画展。
她说:人生永久没有太晚的开始。
如果你心中有一份梦想,以为非做不可,不做就像掉入河里的人,不挣扎就会淹去世。
那么,不要由于环境犹豫未定,毕竟人生如驹奔隙,骎骎而过。
一样平常人都不是他们想要做的那种人,
而是他们不得不做的那种人。
希腊德菲尔神庙的石柱上刻有一句铭文:认识你自己。
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却少有人交出完美答卷。
史特利克兰从小就想当一名画家,但是在父亲训导下,他成了一个买卖人。
终年夜后,他按照社会期待,循规蹈矩地生活,成为别人眼中的好丈夫 、好父亲、老实的证券经纪人、品行端正的社会成员。
但是有一天,史特利克兰溘然意识到,自己一贯活在别人的期待中,从未真正做过自己。
于是他决定撕掉身上所有标签,经由多年的流落,终极来到塔希提岛。
在这里,他过上了为所欲为的小日子,做回艺术之美的朝圣者。
大多数人,从出生到去世亡,始终遵照父母和社会规定的路线,统统按部就班。
大概在某个领域卓有造诣,生活体面,奇迹辉煌。
但辛辛劳苦一辈子,到头来,活成了父母的续集、子女的前传、朋友的外篇,唯独没有真实的自己。
回顾往昔,内心难免产生挥之不去的遗憾与失落落。
但生命只有这一遭,与其遵照他人安排,不如屈服内心召唤。
为自己,年夜胆一次。
人生只有一种办法,
便是以自己喜好办法过生平。
《玉轮与六便士》中有一段话,发人深省: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好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挥霍自己吗?
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年夜夫,年薪一万镑,娶一位俏丽的妻子,便是成功吗?
我想,这统统都取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他认为对社会应尽什么责任,对自己有什么哀求。
既然社会上的人参差不齐,生活也不该千篇一律。
崇尚自然,便归园田居;习气了稳定,就安于朝九晚五的重复;想搏出一番天地,就去承受创业的压力。
生活办法没有好坏之分,自己喜好的,才能问心无悔。
书里讲到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年轻人,医学院学医,才华出众。
大家都认定,等着他的是锦绣出路与荣华富贵。
就职前,亚伯拉罕想旅行一趟。
当他到达亚历山大港,望着第一次到来却倍感亲切的城市,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喜悦,仿佛回到了家。
由于“感想熏染到一种神示”,在内心强大力量的匆匆使下,亚伯拉罕决定留下来。
他在政府部门找到一份事情,职位低微,收入浅薄。
亲友对此无法理解,都认为他疯了。但心灵的知足感,也只有亚伯拉罕自己清楚。
对当初的决议,他从未后悔,并且想在此度过余生。
这位年轻人的取舍,验证了尼采的一句名言: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如果心神往之,就义无反顾地实践。
如果乐在个中,就心安理得地追求。
人生最大的成功,因此自己喜好的办法度过生平。
▽
高晓松在一次节目中说道:
“每个心里永久有两样东西,就像《玉轮和六便士》,六便士当然是人们须要的,但你弯腰去捡六便士的时候,别忘了举头看看天上那个玉轮。”
现实和空想,本是人生的一体两面,锅里有饭,心中有梦,忙时策马奔驰风风火火,闲时修篱栽竹清寂静静,才算花好月圆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