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出自《苏文忠公函集》,原文里面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诗句制定条约论,这里只将与本文有关的段落进行翻译。
苏轼这段话的意思是,许多诗歌,须要读者有深切的人生履历和生活体会之后,才能懂得个中的境味。但是普通的墨客和超级巨星般的墨客,在才华、笔力、技巧以及境界这几个方面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晚唐墨客司空图这两句,“棋声花外静,幡影石坛高”,表现了深山寺院中极其宁静的午后,没有寺僧的踪影,只能听到从花圃那边传来的棋声。的确是极宁静的境界,但除此之外便没有更深层次的韵味了,你不知道墨客此刻是若何的感情状态,也不知该用若何的思想感情来解读它(彷佛晚唐苦吟派墨客都挺善于写这类不见情绪但词句工巧的诗歌的)。而后面引用的杜甫这两句,“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则有不同,我们且来看一看这首杜诗究竟高明在那些地方。
倦夜
唐代 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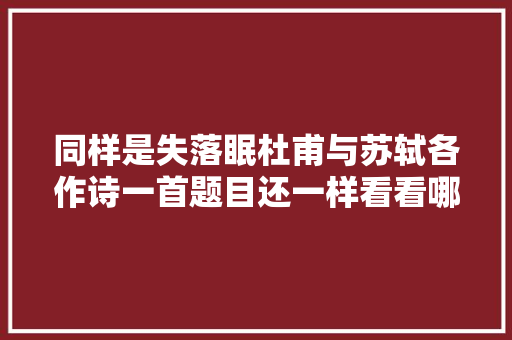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
重露成丝毫,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兵戈里,空悲清夜徂。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初秋,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乱彷佛开启了大唐王朝的浊世序幕一样,从那往后,叛乱和盘据一场接着一场,此起彼伏,就连原来归顺大唐王朝的友好邻邦们也开始不断侵扰,这不,西南的吐蕃看着江河日下的大唐也不禁蠢蠢欲动,终极还是操戈相向。《资治通鉴》记载,“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疆,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开屯田,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胡虏尽蚕河西之地;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这即是说,成都平原以北和以西之地,已尽归胡虏之手,而成都这个可供大唐天子避难之所也险些成为战役前哨。杜甫这首《倦夜》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成。
前四句写初秋夜晚的失落眠过程,从室内到室外,从子夜到清晨,墨客因心中有所郁结而辗转难眠,人是疲倦的,精神是紧张的,这种失落眠的夜晚就叫“倦夜”。再加上颈联两句,“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前六句就将墨客永夜漫漫、夜不能寐的过程都给写出来了。这六句有两个特点,一是无一字与失落眠有关却处处是失落眠时候的所见所感;二是此六句全为客不雅观描写,但却处处指向着那个看到听到感想熏染到这统统的亲历者——墨客自己,由此这六句三十个字也就字字都熔铸着墨客的情绪了。试想,若墨客此刻没有敏感而焦虑的心情,他怎能在疲倦的初秋之夜感想熏染到竹席的寒凉,他怎能为竹叶上露珠的滴答声所扰,他又如何深切地不雅观察到萤火虫的自照与鸥鸟的相呼呢。有一种表明将“水宿鸟相呼”句中的“呼”字阐明为“打呼噜的呼”,说墨客实在难以入眠,于是移步院外,草堂的深夜实在太安静了,墨客竟然都听到了鸥鸟的呼声,大自然中生物的安心、自适和高枕而卧,更加衬托出墨客内心的焦虑,也更加衬托出这个失落眠之夜的宁静,两相对照之下,诗中所包含的情绪也就为读者所深刻感知了。(我以为这个解读切实其实神了,若是解读为鸥鸟呼唤差错则诗意减去一半)
末了两句“万事兵戈里,空悲清夜徂”(徂是消散的意思),点明全诗的精神内核,墨客始终不忘忧国忧民,以一匹夫之身,书尽家国天下的忧虑。实在我以前读到这类诗的时候都认为忧国忧民不过是诗歌的一种题材而已,但这段韶光实实在在看到了大时期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生离去世别,便对这些忧国忧民有了更深切的理解。的确,就犹如那句话中说的那样,时期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便是一座山。
读过了杜甫的深厚,我们再来看一看苏轼用同样一个题目所作的一首诗,看看他又是若何的心情呢。
倦夜
北宋 苏轼
倦枕厌永夜,小窗终未明。
孤村落一犬吠,残月几人行。
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
荒园有络纬,虚织竟何成。
写这首诗时的东坡身在儋州(今海南省),已过耳顺之年,这也是他末了的一个贬谪之地。漫漫永夜,夜不能寐,由此而想到他这孤旅般的生平,心中也是有所郁结,同杜甫那首一样,东坡也是失落眠了一整夜。
先将诗句略作翻译:只有失落眠的时候才懊恼夜的漫长,一直地望向小窗处,却始终不见黎明的到来。不知已是几更天了,村落庄那头传来了犬吠,或许是有几位行人在匆匆赶路吧,他们定当是为了生活在奔波。看看自己已经到了鬓衰之年,却还在人生的旅途中波折不断,想到这里不禁辗转反侧。这荒凉的院子里有蟋蟀的叫声,它们整夜里“吱呀吱,吱呀吱(谐音织呀织,织呀织)”地叫个一直,但织巾又几时能成呢?(蟋蟀,又称络纬、纺织娘,苏轼这里用字面意思反衬自己繁忙生平而无所成)
可以看出,前两句表现了墨客辗转难眠时的焦虑;次二句用犬吠遐想到行人,又反衬出自己的孤独寂寞;五、六两句感慨自己人生孤旅的惆怅;七、八两句抒发民气抱负不能实现的无奈。人生的孤旅,贬谪时的孤独寂寞,就在这个失落眠的夜里,化作了一声声“吱呀吱,吱呀吱”!
清代纪晓岚评价这首诗道:结故意致,遂令通体俱有归宿。若非此结,责成空凋。
清代文人查慎行这样评价道:通首俱得少陵神味。
就笔力、韵味、境界和思想感情来说,苏轼这首比司空图那两句要高明许多,其才力堪与杜甫一较高下,只是就这首来说,个中暴露的肺腑比起杜诗还是稍显气短,一家之言,一家之言!